特朗普的脸,我们的脸
作者:云也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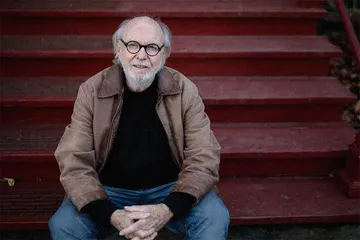 “入主白宫”,这四个字描述的景象基本上已褪尽了光环。年轻些的人似乎没有动力去竞逐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位置,而一眼看去,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政治大事值得一位美国总统兴奋起来,去促进它的解决,同时谋求个人的留名青史。新一轮的总统竞选,大概率仍然会在特朗普和乔·拜登二人之间展开,我想,明智而内心无偏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好事情。
“入主白宫”,这四个字描述的景象基本上已褪尽了光环。年轻些的人似乎没有动力去竞逐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位置,而一眼看去,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政治大事值得一位美国总统兴奋起来,去促进它的解决,同时谋求个人的留名青史。新一轮的总统竞选,大概率仍然会在特朗普和乔·拜登二人之间展开,我想,明智而内心无偏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好事情。政治漫画关注各国元首,而美国总统的漫画尤其多,因为他们权力大,曝光率高,做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漫画家把小布什画成手握火箭弹的样子,克林顿则捂着下体,奥巴马等人也都各有各的主要“作为”。人物的某些特征往往被放大,如此彻底瓦解了这个职位的严肃性。
然而有一任是例外:特朗普,他免于漫画家的蹂躏。特朗普的漫画当然很多,稍微一搜索就知道,可是仔细看来,不论是在“飞机头”上做文章,还是在夸大其面门的通红,漫画对特朗普的杀伤力都不如对奥巴马、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等人的杀伤力那么强。——这是W. J. T.米切尔的观点。他是一位研究图像学的学者,他说漫画家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上台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挫,他们用得得心应手的技艺,在特朗普这个对象上失效了。
“特朗普的特性”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政治漫画家发现,自己竭尽所能也“很难超越或夸大它”。正如我们常说的“现实比小说更像小说”,特朗普是“比漫画更像漫画”,根本不劳漫画家(以及政论家、时评人等)动手,他从不自称正人君子,于是也不需要漫画家来揭露他的道貌岸然。同样,脱口秀节目本来是集中嘲讽政坛人物的舞台,可是模仿特朗普的脱口秀却不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演员模仿得越像,观众越不觉得好笑,仿佛特朗普比他本人更像一个脱口秀演员。 米切尔教授的这本小书,书名叫《元图像》,书中最有趣的一处,也是直接触及书名的一处,就讲到了特朗普的脸。米切尔点破了一个人们通常不愿承认的事实:一向拥有美名的美国民主,其存续的基础是很无聊、让人厌倦的——“只有政治和法律等乏味的制度才能拯救民主”——于是依附它、参与它的人,和揭露它、讽刺它、冷落它的人,都是以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特朗普的出现,宣告了这套机制的一次沉重的挫败,不管失败是源于本身运作失灵还是源于被劫持。
米切尔教授的这本小书,书名叫《元图像》,书中最有趣的一处,也是直接触及书名的一处,就讲到了特朗普的脸。米切尔点破了一个人们通常不愿承认的事实:一向拥有美名的美国民主,其存续的基础是很无聊、让人厌倦的——“只有政治和法律等乏味的制度才能拯救民主”——于是依附它、参与它的人,和揭露它、讽刺它、冷落它的人,都是以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特朗普的出现,宣告了这套机制的一次沉重的挫败,不管失败是源于本身运作失灵还是源于被劫持。
古往今来,凡是领袖人物,国王、皇帝、首相、总统,不管是不是名垂青史,都是被人关注的,而这种关注多少也都意味着被仰慕。米切尔说,美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诡异时刻,一个没有任何庄重感而又具有危险性的人,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不过米切尔无意讨论“民主的未来”之类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图像。在他看来,特朗普对民主的有效破坏,除了其尽人皆知的“大放厥词”的习惯、其对于保守人群的无底线的煽动等之外,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是用他的那张脸,那张不需要有意扭曲、天然就如一幅漫画的脸。
脸正是“元图像”——在书中,米切尔小心地提出这个极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元”,意味着其他图像因它而生,为它而来,人们的关注、视线和内心的安与不安,都围绕着脸。最简单的例子:给你一支“随便画画”的笔和纸,你会画什么?多半会画出一张脸,最起码是三四根线组成的一个表情。我们走过一座建筑,注意力一定会首先被“门脸”吸引过去(英文和法文的“门脸”——façade——即“建筑外立面”,同样是源于face的一个词)。人类只要形成了基本的认知,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各种事物上寻找它的脸:花的花冠、树的树冠、房屋的门窗、桌子的“台面”……T台走秀的模特永远是一张没表情的冷脸,这是不是说明了,我们永远会不由自主地先去看脸,哪怕明明知道这个人是来展示身上的服装的?
脸必须是裸露的,否则会让人感到怪异,难以信任(所以一个戴口罩被接受为正常的年代一定是和之前有所断裂的),但裸露本身又埋下了冒犯的可能。蒙在脸上的面纱,既是保护又是引诱;被蒙上的脸让人想揭破它,因为不想被它偷窥,而裸露的脸则让陌生人不自觉地回避,不愿同它上面的双眼相遇。再说一个更有群众基础的例子:你打开一个视频,蹦跳的粗体字讲“某人在某地做了什么事情”,而图像里的人脸却往往被模糊掉。打着“保护隐私”的名义,这种视频引导观者产生“这事见不得人”的想法。观众也许会渐渐明白,此类视频很可能是虚假的,可是类似的图像仍然在大量生产出来,占满人们那些用来浪费的时间。
社交媒体的发达无限突出了脸在图像世界里君临一切的位置。谁都知道图像中的脸是加工过的,也都会本着一点点的虚无主义,去想象去掉妆容和美颜之后的样子,可是真伪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露脸。
特朗普那张从来直面一切人的脸,让一些人感到强烈的不适,强烈的不可接受,另一些人则疯狂地赞美他的“直率”“不虚伪”“真性情”。按照惯例,美国总统,这种公众人物中的公众人物,是断不可以任凭自己的好恶在公共场合流露的,然而这位“推特总统”仅凭其脸和表情,就可以(至少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赢得他所需要的那部分民众的(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
米切尔对元图像的分析,对于急切地想把握当下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入口。这本书并非每一章都易读,关于《愚人船》和瓦尔堡绘画的部分甚至让人感到文化上的生僻,可是我感到,他的叙述正如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那样,有很大的隐喻意味,他展示的不是探究的结果,而是过程——甚至可以说是探究的决心。《一九八四》再度成为被倚赖的、关于未来想象的可靠文本,米切尔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要一幅未来的图景,就想象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的脸上。”
在中文的常用语中有个有趣的现象:“面”和“边”用于描述位置时往往可以互相替代。“他在我的右边”“队伍的前边”“东边”“上边”“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这些表述中的“边”都可以换成“面”。或许区别只是在于,人们在说“太阳在东面”的时候会转身面向太阳,而说“太阳在东边”时则不会。然而有一个词是不能替换的:“对面”不能改为“对边”,因为只要是二人(物)相对,则必为面对面,没有第二种可能。
“面对面”是如今最大的奢侈品,因为图像和图像中的各种脸太多,它们都属于一般所说的“看脸的时代”中的“脸”,一个个真人的注意力被它们抽干捞净,然后带着空空如也的眼神回到人群之中。所以,米切尔和他的《元图像》,做了一个思想者最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