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王”与他的时代
作者:陈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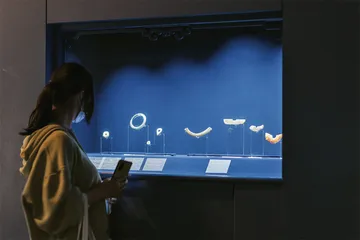 张家港博物馆的二楼,与东山村遗址发掘的其他高等级墓葬分开陈列、单独展示的,是被考古学家严文明称作“崧泽王”的大墓:M90。这座大墓,不仅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9座崧泽时期大型墓葬里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崧泽文化中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
张家港博物馆的二楼,与东山村遗址发掘的其他高等级墓葬分开陈列、单独展示的,是被考古学家严文明称作“崧泽王”的大墓:M90。这座大墓,不仅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9座崧泽时期大型墓葬里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崧泽文化中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通过展览现场一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墓葬主人仅剩头骨尚存,下葬时四个角落里堆放的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器物已被挤压成碎片。作为配饰使用的璜、镯、玦、管等19件玉器组合,依稀可辨曾按照某种佩戴方式安置在墓主人身上。尽管有机物早已腐朽,但可推想,他可能曾经头戴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着玉璜,耳朵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上还戴着玉镯。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散落在墓主人四周、经过精细打磨的5件石钺,以及西北角落的一件大石锛。 M90大墓里出土的这5件石钺,整体都近似圆角方形或梯形,磨制光滑,刃部未见使用痕迹,中间均有圆形穿孔,显然不具备任何实用功能,除材料并非良渚文化中常见的软玉外,其形制已经与良渚文化的玉钺极为类似。并且,一件石钺所在的土面上还有数道朱砂痕迹,可推测原本这件石钺的圆孔两侧还曾绘制有图案。
M90大墓里出土的这5件石钺,整体都近似圆角方形或梯形,磨制光滑,刃部未见使用痕迹,中间均有圆形穿孔,显然不具备任何实用功能,除材料并非良渚文化中常见的软玉外,其形制已经与良渚文化的玉钺极为类似。并且,一件石钺所在的土面上还有数道朱砂痕迹,可推测原本这件石钺的圆孔两侧还曾绘制有图案。
良渚文化时期,玉钺与玉琮、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是权贵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将玉钺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则最早开始于崧泽文化时期的石钺。东山村遗址发掘的高等级墓葬显示,崧泽文化时期氏族里的权势成员,不仅使用丰富的日用陶器、玉器随葬,还拥有象征军权、王权的石钺。这些发现,将以石钺、石锛和石凿为代表的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的出现时间,往前至少推进了300年。
按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若非族群里领袖式的高贵人物,不可能拥有如此排场。此外,墓主人的下颌及颈部周围发现了较多石英砂粒。石英砂又常被称作“解玉砂”,是对各种玉石材料进行磨削的工具。他的头部右侧上方还出土了一件铁质含量较高、刃部有疤痕的石锥,身边搁置着一个打磨用的砺石。考古学者们由此推测,这是一套琢制玉器的工具,表明“崧泽王”拥有治玉权,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东山村遗址位于张家港博物馆西北部19公里处,坐落在香山由西向东延伸的斜坡上,地势较高,紧邻长江。这里曾是金港镇乡政府所在地。2009年撤乡并镇后,被废弃的乡政府旧址上就只剩下几座建筑,虽然外立面还贴着红色瓷砖,但墙脚生出的青苔、探出窗外的草木,都在显示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逐渐抹去的。
东山村遗址位于张家港博物馆西北部19公里处,坐落在香山由西向东延伸的斜坡上,地势较高,紧邻长江。这里曾是金港镇乡政府所在地。2009年撤乡并镇后,被废弃的乡政府旧址上就只剩下几座建筑,虽然外立面还贴着红色瓷砖,但墙脚生出的青苔、探出窗外的草木,都在显示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逐渐抹去的。
考古学家的工作正是重新发掘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林留根还记得,当时张家港市的宣传部长找上门来,希望考古所能够在当地做些工作,挖掘更多历史文化内容。然而在对张家港的几个遗址进行调查后,林留根发现大多数遗址都在城市建设中被破坏掉了,只有东山村遗址,“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开展些工作”。
1998年金港镇进行乡政府建设时,苏州博物馆曾在东山村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发现的主要都是些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因此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处马家浜文化的早期遗址。由于出土的随葬品与草鞋山等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太一样,当时给它命名为“马家浜文化东山村类型”。
等到金港镇撤乡并镇时,东山村遗址有了进一步发掘的条件。此时乡政府建筑还未被完全废弃,一些工作人员仍在这里上班,遗址上满是房屋,食堂、篮球场、停车场、宿舍楼、办公楼……几乎“没地方下脚”。负责现场工作的领队是当时考古所的副所长周润垦,他带队花了好几天在遗址四周探了情况,观察哪些地方还遗留有文化层。篮球场所在的位置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底下有文化层,地上没有地面建筑,砸掉地表便可进行发掘。
进行半年多的发掘工作后,一小片墓葬进入大家的视野。这片墓葬并不属于马家浜文化,随葬的陶鼎、陶豆以及打磨光滑的石器均显示,这是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遗存。尽管由于建设施工,遗址大部分已遭破坏,只剩下一点点痕迹,但仍可以看出,这片墓葬排列比较有秩序,并且还算完整,多数陪葬有几件或十几件随葬品。“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不多,比较好的有上海崧泽遗址、嘉兴南河浜遗址等,所以这本身是个很重要的发现,远超我们最初觉得只是挖点马家浜文化遗存的预期。”林留根说。 不过,看着这些长约一米、宽几十厘米,排列似乎井然有序的墓葬,他忍不住想:这个墓葬群的规模可不可能其实更大?墓葬区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这些远古先民的居住区又在哪里呢?
不过,看着这些长约一米、宽几十厘米,排列似乎井然有序的墓葬,他忍不住想:这个墓葬群的规模可不可能其实更大?墓葬区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这些远古先民的居住区又在哪里呢?
林留根等人在接手东山村遗址的考古工作时,其实带着一种聚落考古的观念,也就是除了挖出东西,更重要的是得了解聚落的生存、发展和兴衰,以及聚落周边的环境,揭示出聚落自己独特的生命史。按照这种思路,当他们发现了篮球场底下的墓葬区后,紧接着便开始试图寻找居住区、生产区、手工艺作坊区等。不久后,他们在篮球场西面的高处又开了几个探方,发现了一片有红烧土的文化层堆积。
这片文化层位于乡政府大院的一条马路上,马路修得很宽阔,可以停放车辆,两旁绿化也很好。他们这次是敲开了马路往下挖,地层表面大面积的红烧土显示,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先民利用木骨泥墙的建筑方式,再经过火烧加固后的房屋,坍塌后形成堆积现象。经过清理后,房屋柱洞明显,是一个方形房子加一个圆形房子的配套组合,每座房屋面积约在85~95平方米。
“根据当时我的经验,这么大的房子在崧泽文化考古工作里都是没有见过的。”林留根解释说,“马家浜文化也有圆形的房屋,但面积没有这么大,而且东山村遗址的房屋是一个很大的方形建筑,外面搭配一个小点的圆形建筑。圆形建筑可能类似于附属建筑,相当于厨房、仓储,与方形建筑结合使用,而方形建筑里可能还有空间区域的分割,整个房屋等级规模明显比较高。”
他开始考虑这片建筑遗址与此前发掘的小墓葬群之间的关系,“小墓里埋葬的人绝对不可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放眼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这几乎是新石器时代最好的房屋了,无论凌家滩还是良渚,都没有发现多少大房屋,发现房子最多的就是苏州吴江的龙南遗址,但都比较小。”
这些大型房屋的出现,更让林留根感到东山村聚落十分不寻常,他判断周围可能还存在更高等级的墓葬。按图索骥,考古队又将调查范围继续往外围扩大,但由于遗址的南面已经建起了不少别墅,一线的工作人员虽探清楚了情况,却没办法进行发掘。
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西边山上的香樟林。此前,考虑到若是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需要赔偿大笔青苗补偿费,成本过高,所以他们一直没纳入计划,但眼下这里成为考古队员们最有可能继续下去的现场。最终,在张家港市政府的积极配合下,这片香樟林被移植到别处。
最初,铲开土层逐渐露出的红烧土让林留根以为这里可能也是一片居住区。不过很快,接下来显露的就是后来被誉为“崧泽王”的大墓M90。
“它的墓坑达到了三四平方米,而马家浜的墓坑只有一点点大,良渚反山、瑶山的大墓,尽管出土的玉器比它多,但墓坑也没它大。”墓坑里密集陈设的随葬品也让林留根十分兴奋,他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重要发现。 顺着M90大墓,考古队很快又在附近依次找到了92、95等10个大墓。这些墓葬排列很有规律,互相之间没有打破关系,清理后里面的陪葬品都很丰富,除大量陶器、石器外,还共计出土了121件玉器。林留根内心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崧泽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但又不敢妄下判断,因为此前考古学界认为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作为良渚文化的前身,虽然也存在社会分化现象,但总体延续了马家浜文化比较平等的社会面貌。
顺着M90大墓,考古队很快又在附近依次找到了92、95等10个大墓。这些墓葬排列很有规律,互相之间没有打破关系,清理后里面的陪葬品都很丰富,除大量陶器、石器外,还共计出土了121件玉器。林留根内心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崧泽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但又不敢妄下判断,因为此前考古学界认为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作为良渚文化的前身,虽然也存在社会分化现象,但总体延续了马家浜文化比较平等的社会面貌。
2009年秋天正值浙江省考古所成立30周年,张培忠、黄景略和严文明等考古学家都齐聚杭州。作为江苏的代表,林留根也来到会场,他趁机邀请这3位著名学者与会后前往东山村遗址现场参观。张家港市政府派来了一辆商务车,载着他们一路颠簸至东山村遗址。
细雨蒙蒙,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行人决定先上考古工地。现场的地面微微有些潮湿,已经提前收拾干净的10座大墓清晰排列在遗址现场,几位老先生站在探方上安静又认真地端详起来,林留根觉得可以用“鸦雀无声”来形容。隔了半晌,张培忠提起拐杖,往探方上轻轻一敲,感慨了句“这还了得”。严文明和黄景略则久久沉默不语。
为了避免玉器露天陈列会被盗走,考古队早已将这批墓葬中发现的小件玉器都拿回了标本室收藏。考察完工地后,专家们立刻直奔标本室,仔细地查看起了这批玉器,过了许久看完,这才返回到张家港博物馆休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见几位大先生到来,送上了提前准备的笔墨纸砚求字,一向谨慎的严文明竟欣然应许,提笔写了三个大字:“崧泽王”。
“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我渐渐了解到,当严先生落笔写下‘王’字时,他心里其实有个长江下游古国文明的概念。苏秉琦、严文明先生认为良渚是一个早期古国文明,他们一直在探索这种文明到底从何而来,因为它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发展出来的。”林留根很是感慨道。 实际近年来,考古学家李伯谦指出,东山村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了苏秉琦所说的“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认为的距今5500年到4500年,提前至距今6000年,中国古代社会在更早时间里,发生了由相较的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
实际近年来,考古学家李伯谦指出,东山村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了苏秉琦所说的“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认为的距今5500年到4500年,提前至距今6000年,中国古代社会在更早时间里,发生了由相较的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
“东山村大墓区是从崧泽早期到崧泽中期,延续了好几百年好几代人的墓葬群,类似于这个古国的王陵。这几个高等级墓葬的主人,便是这个古国的国王,基本上每个墓葬里都发现了钺形器,95号墓里出土了一把玉钺,其他墓葬里均出土了石钺,它们都是权力的象征。”林留根表示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对于长江下游的文明发展进程而言,崧泽文化处在一个关键的变革阶段,“它在距今大约5800年前就发生了社会分化,这是有基础的。实际良渚所在的钱塘江区域,不如太湖西部沿江地带出现社会分化那么早或者那么明显。因为要出现社会分化,既需要内部因素,也需要外部因素。太湖西部沿江地带因为先天矿石资源的优势,玉石器工业更为发达,这些玉石器既是产品也是商品,慢慢就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
良渚文化里像反山、瑶山这类墓葬都位于高出地面人造的祭台上,浙江嘉兴的南河浜遗址也曾发现过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的祭台。那么,东山村遗址是否也有类似的祭台呢?时间序列上比良渚更早的崧泽文化,到底给良渚文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它的这套文明因素是如何被良渚所继承的?
带着这种思考,林留根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变成了寻找祭台,结果却没有找到。但考古队对整个东山村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勘探,发现这个遗址的面积大概在25万到30万平方米之间,整体略呈圆形,其北部紧邻长江,南边靠近河道。在已经发掘的2000多平方米内,崧泽文化时期的27座平民墓均位于东区,而9座同时期的大墓都在西区。
直到2017年,在针对常州青城墩遗址的考古发掘里,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唯一的高台式贵族专用墓地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并且,该遗址双重环壕的聚落格局也极为少见。此外,青城墩遗址71号墓里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玉龙,它在下葬时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这条玉龙直径只有1.2厘米,被设计成一个蜷曲的玉环,需要借助放大镜才可以看清它浑圆且突出的眼睛、向上弯曲翘起的吻部和紧贴在颈背的双角。不论龙纹还是玉器,都与先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表明,该遗址是江南地区一处难得的较高等级的史前聚落中心,而71号墓的主人应该属于这个族群的权力阶层。
作为长江下游的两个史前玉器中心,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至今成谜。从两地的用玉习俗或玉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它们必然存在着一定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凌家滩玉资源或者玉工的衰退,造成了玉工的迁徙,令良渚文化最终得以崛起。但究竟它们之间是如何转变的,则缺乏更多的证据。
与通常认为文明发展往往遵循从神权到王权再到帝权的途径不同,崧泽文化在发展到良渚文化的过程中,由军权、王权的道路开始走上军权、王权与神权相结合而突出神权的道路。东山村遗址的玉器较多,还出土了一些异形玉器,这都在良渚文化时期得到了更多发展,形成以琮、璧、钺为中心,用以区别阶层、标识身份、反映等级的玉礼器系统。
这种发展路径,“一方面有效地巩固了良渚上层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走上了以神权为主体的发展道路,导致统治脱离了现实,最终覆灭。而中原地区走向了以王权为主体的道路,王权更加务实,逐渐崛起”。林留根说。大崧泽文化圈
崧泽文化是以上海市青浦区的崧泽遗址命名的,虽然现在有的考古资料显示这里只是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普通聚落,但它为认识距今5800年至5300年间长江下游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在2004年曾参与过一次现场考古发掘,他们发现了多座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并且首次发现上海地区带有人类骨骸遗存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这具人类骨骸也被称为“上海第一人”。
了解到我们是为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器而来,陈杰将我们带到了上博的玉器展厅,指着展览最开始位置的一个小小展柜说,崧泽文化里玉器并不突出,偌大的玉器展厅里,只有这里面的几件装饰性用玉属于崧泽文化时期。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用玉特征。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用玉的传统形成很早,最早可以溯源到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以及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用玉更加普遍。作为上承马家浜、下启良渚的崧泽文化,却“由于现在崧泽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发现很少,还没办法将当时的用玉图景加以清晰描绘”。陈杰介绍,“但崧泽时期应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用玉体系。首先比如装饰性用玉,从原来头部、耳部的装饰,已经开始往胸部、腕部乃至全身扩展,胸前会佩戴玉璜,手腕上戴玉镯等。这种组配式的装饰体系在崧泽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其次这时期也开始形成了一些礼制性的器物,不少崧泽文化的遗址里一些身份较高的墓葬中都发现了玉质的斧、钺等器物,这类器物本身没有开刃,材质也不具备实用价值,应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另外还有类遗物,目前发现不是很多,如桐乡普安桥遗址发现的玉龙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精神信仰,再如东山村遗址的那件小型钺形玉器,它可能是某种装饰品,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虽然馆里观众熙熙攘攘,但他们几乎都是冲着“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而来,没人注意到中庭高高悬挂的一幅海报,上面预告着博物馆接下来的6月即将开幕的“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陈杰强调他们特别在展览标题中加入了公众不太了解的“崧泽”,因为实际上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虽然馆里观众熙熙攘攘,但他们几乎都是冲着“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而来,没人注意到中庭高高悬挂的一幅海报,上面预告着博物馆接下来的6月即将开幕的“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陈杰强调他们特别在展览标题中加入了公众不太了解的“崧泽”,因为实际上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有专家认为崧泽文化已经达到了‘古国时代’初期,跨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虽然它没有良渚文化体现得那么明显,但当时社会的分化、技术的水平,已经和一般平等社会不一样了。从这点上,我觉得崧泽文化对研究长江下游早期文明意义非常重要。”陈杰所指的崧泽文化即包括了分布在太湖流域的狭义的崧泽文化也包括了皖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不同聚落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文化面貌趋同,生活方式相似,因此被专家们认为同属于大崧泽文化圈。
“以东山村遗址和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大崧泽文化圈。这些遗址都明显反映出了聚落的分化,阶层的分化,是新社会阶段的体现。要理解整个大崧泽文化圈,凌家滩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陈杰说。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凌家滩遗址的年代在距今5600~5300年左右,相当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而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大型墓葬则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早中期。从考古学判断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据陶器上看,凌家滩遗址与崧泽文化联系紧密,但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器又如此独树一帜,或许太湖地区还有崧泽文化晚期重要聚落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过程里,其背后代表的长江流域湿地稻作农业是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范本。世界的饮食体系里,多数是以旱作农业小麦为主,而长江中下游在很早便开始了以湿地稻作农业为主的实践。这些稻作农业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典型的有浙江省浦江县的上山遗址、杭州市萧山区的跨湖桥遗址。但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人类生产的补充,还没有发展成主要的食物来源。进入崧泽文化时期后,稻作农业才逐渐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重要。
因此,崧泽文化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一套套规范性器物组合,形成耕地时有石犁,收割时有石镰、石刀等完整的石器使用体系,并被良渚文化继承了下来。这些器物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崧泽晚期的遗址数量迅速增加,说明当时的人口迅速增加,也开垦了更多新的土地。
陈杰说,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凌家滩遗址的年代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相当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而东山村遗址的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早中期,或许太湖地区还有崧泽文化晚期重要聚落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那么,究竟良渚文化是如何从崧泽文化里的军权、王权的道路,走上了以神权为主的道路呢?陈杰认为根据玉器的发现,这可能与信仰体系上的变化有关。崧泽文化的玉器造型非常丰富,有虎、鹰、龙等。而良渚文化逐渐形成了以神人兽面纹为特点的重要信仰符号,并在1000多年历史里贯穿始终。“这或许是一种祖先崇拜。从崧泽文化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们许多仍取之自然,崇尚自然,有许多动物造型的遗物,它的信仰呈现多元的形式。世界各地的人类信仰都是从多神信仰逐渐转变为一神信仰的。统一信仰的形成或许促进了良渚社会的统一和增强了社会组织能力,从而铸就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高峰。”
在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修建人工池塘时发现的一口六朝古井,恰好位于遗址的居住区和小墓区之间。早已被大棚围起的东山村遗址发掘现场,绿荫环绕下的六朝古井,以及荒废的红砖墙现代建筑、无人问津的残余篮球场……令历史在这里交织叠加,具有了可视的厚度。崧泽文化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它们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发掘,但这些想象已构成了我们对这处平常山麓的向往。
(感谢张家港博物馆田笛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