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而炽热的“游牧人生”
作者:胡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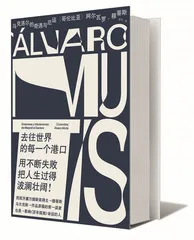 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见到流浪的人、漫游的人,却难得见到马克洛尔这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属于大海的人”。
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见到流浪的人、漫游的人,却难得见到马克洛尔这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属于大海的人”。马克洛尔是哥伦比亚诗人穆蒂斯的长篇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的主人公。这个人物最初是穆蒂斯在诗歌中创作的,一个瞭望员,一个缠绕着“离经叛道的梦境维度和他纠结而炽热的存在”,过着一种“混乱的流浪生活”。
20世纪不再是一个流浪者、漫游者的时代,而是漂泊者的世纪。在里尔克、卡夫卡、艾略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罗伯特·瓦尔泽、佩索阿、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的作品里,人类遗失了自己的道路,忘却了或者说抹除了目的地,因而漂泊于内心的和回忆的风景。在穆蒂斯的小说里,我们遇到了马克洛尔,他渴望流浪,享受漫游,却并不对人和风景感到震惊。他要同时在现实和内心空间里漂泊。他永远在抵达不同的地方,遇见别样的人。他满怀激情地走向海洋和港口,却不执着于目的,更不规划未来。漂泊的生活是无序的,不再怀念家园,不再期待救赎。
虽然总是沉浸在对梦境、过去的回忆中,马克洛尔却又是一个钟情于现实世界的人。他钟情于遭遇到的人(尤其是女人),钟情于经历过的港口和大海。他期待“奇遇”,心系漂泊,在漂泊中耗费自己的生命——无目的地,无原则地耗费。他之所以选择大海,是要在我们的世界上寻找一个没有记忆和历史负担的牧场,让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成为遭遇的瞬间、恍惚的瞬间、放纵的瞬间。现实世界的瞭望员要为船只测定远方的路程,避开即将出现的“厄运”。然而瞭望员马克洛尔,既不测定路程,也无心避开自己的厄运,甚至不惧怕厄运。他要在旅程中观看、体验、爱上整个世界。
马克洛尔的生命,永远在开始。他是一位在全世界漂泊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对他来说,港口只是短暂的过渡。而他的朋友、他的女人只是他无数梦幻的间歇和裂隙。他的人生不能停顿和止息,他在日记里写过:“告别漂泊时,我总能感到轻微的焦虑和模糊的恐慌,不知在踏上土地的那一刻,会有怎样的未知降临在我头上。”因此,受伤后滞留在“阿尔米兰特”休息站时,马克洛尔极为痛苦——痛苦于漂泊的结束,浪游的停息。他的人生必须拥有无数的“起伏和意外”。甚至,他的朋友和恋人的生命也是如此:阿卜杜尔·巴舒尔死于坠机,伊洛娜和拉丽萨死于废弃的船里的燃气罐发生泄露爆炸。
马克洛尔的生命一直在旅途中,因此行李中只有必需品。但他总是随身带着书。他集中阅读法语作品和译本,特别是历史书籍和名人回忆,如《红衣主教莱兹回忆录》、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约根森的《圣方济各生平》等等。他阅读时喜欢沉浸在外语中,就像他的人生——总是在越界。他的阅读和他的人生步调是一致的。他暂时离开大海时,就去开酒吧和妓院,做旗语生活,进行荒原之旅,走私军火,山中淘金,做船舶修配厂看守、咖啡馆侍应、夜班值班人、医务室清洁工,甚至乞讨。他所谓的“关于人的事情”,不可能是传统的爱、伦理和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只是存在、虚无和时间,而可能就是漂泊本身——悬置了时间后,在空间里的漂泊。用马克洛尔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探索一个对他来说“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世界,构成了对日常、愚蠢和平庸的挑战,孕育着真正的生命。
最关键的是,马克洛尔对陌生的世界——大海和陆地的探索并非出于强迫,哪怕是自我强迫。这一切源于他身上充盈着的“炽热”存在。他要“用他在路上遇到的一切事物让每一个此时此刻都更有价值”。因此,他的一切经历,包括奇遇和厄运,都让他心心念念,刻骨铭心。
他挂念着一切遭遇过的人,同情所有和他一样永远在漂泊、即将去漂泊的人。他的特立独行造就了孤独,因此他要在出发、行走、遭遇中,通过走向他人而遏制孤独。他的人生在揭示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的当代世界正在向绝对的陌生关上大门。超量的信息和速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重复、均质、乏味、透明、循环。看似新奇而陌生的商品永恒地变化着,但从不产生绝对的差异和陌生。重复和循环让我们走向倦怠。
马克洛尔是不是一个虚无的人?他一味地出发、行走、遭遇、探索,其生命的价值何在?他活在可能性中,因此,也活在虚无中?在这一点上,穆蒂斯的这部小说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之间截然不同。马克洛尔并不是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也不具备“垮掉一代”的颓废精神,虽然他和“垮掉一代”共享了失败的情感。对萨尔、狄安、玛丽露而言,“在路上”,是一次短暂的偏离正轨的旅行。但是,在马克洛尔这里,漂泊不是临时的姿态和立场,而是内在于生命的需要,是终其一生的命运。他只能漂泊,在海上漂泊。大海并不是确定的道路。
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特别是在最后一部《海陆三部曲》中,马克洛尔的人生出现了“本质的改变”。漂泊的激情在冷却,“已经不再有从前统治他游浪人生的那种不求回报的固执挑战意味”。如今,他已是一个站在“暮年的门槛前”的人,因此,生命处在奇异的临界点上——在“炽热”之外,又多出了种种“纠结”。在他身上,一边是激情,一边是对命运的顺从,而衰老是他最终的厄运。人人都要衰老,对于马克洛尔而言,衰老是极为残忍的。因为,在衰老中,他的激情覆灭了。更残忍的是,他一无所得。但这正是他的漂泊的意义。他并不想要在漂泊中抵达一个目的、一个价值体系。对于他,生命正是用来耗费的。
在小说接近结尾的时候,马克洛尔吐露了心声:“马约卡岛是我的软肋,古老的根把我和这片土地连在了一起。”一个属于大海的漂泊者,最终回归了一个地中海岛屿——不过,我们知道,他并不执着于居住,他的房子破败如废墟。在这里,他答应照顾巴舒尔的儿子贾米尔。在这样一种短暂的准父子关系里,他内心“燃起了一种热切的同情和绝对的喜爱”,并且将这种情感指认为“全然陌生的东西”,是“藏在他无法避免的长久征途的迷宫中的考验”。他对伦理情感的回归,依然是在漂泊的维度上完成的。
有必要比较一下马克洛尔和他大半生的朋友与同谋阿卜杜尔·巴舒尔。他们的友谊太深厚了。马克洛尔愿意暂时照顾贾米尔,正是因为能够在贾米尔身上看到巴舒尔的形象。巴舒尔几乎就是另一个马克洛尔。当然,他们的个性又是那么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与马克洛尔谜一般的出身不一样,小说明确告诉我们,巴舒尔是黎巴嫩人。巴舒尔的人生和梦想之间是错位的,他“用全部人生来做航船的梦,拥有过的所有船只却从未令他实现梦想”;而马克洛尔并不具有明确的梦想,只是一直在行动实践着梦想。巴舒尔相信一切可能性;而马克洛尔认为失败是一切事情的归宿——“在那么多流浪和失败中任意漂流”。巴舒尔不断坠入爱河,每一次恋爱都如初恋般充满热情;马克洛尔和女人交往时则从不承诺,也不因抛弃对方而感到罪过。如果说,巴舒尔的人生更加积极,遇事便会反抗,那么,马克洛尔的人生则更加消极,很少与人对质。他“更希望由流转的人生与命运来给他人相应的教训和惩戒”。
这样的对比中,我们更能感受到马克洛尔的与众不同。在“炽热”的存在中,他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冷漠”。他冷漠于伦理的负担和道德的束缚。他对大海和陆地充满无限的热情,但对人(尤其是女人)表现出巨大的“冷漠”。他渴望与不同的人相遇,渴望爱,但不轻易做出承诺,也羞于表达好感。他满怀激情地走向大海、港口和女人,却会被记忆之重压垮——他写了大量言辞华美、句法绵长的日记,诉说“他的不幸、回忆、思考、梦境和幻想”,但他并未成为普鲁斯特。因为他相信“遗忘和冷漠一定会抹除我们原先以为不可更替的情感”。在马克洛尔这里,冷漠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超然。
马克洛尔,那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马克洛尔,代替我们每一个人,一直超然地、自由地漂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