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活字之毁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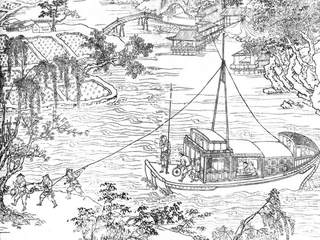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佩文韵府》告成,康熙心情愉悦,在所撰序言中写道:“从来著一大书,非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今数年以来,所成大部书凡十有余种。”此言不虚,却应区别个人著述与朝廷修书的差异,也包括一些由个人编著改为朝廷主导的项目,包括选项的难易程度、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都会影响到进度和最后结果。比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不到五年就纂成初稿,而修订和制版印刷竟用了15年,出版时连他的名字也没了。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佩文韵府》告成,康熙心情愉悦,在所撰序言中写道:“从来著一大书,非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今数年以来,所成大部书凡十有余种。”此言不虚,却应区别个人著述与朝廷修书的差异,也包括一些由个人编著改为朝廷主导的项目,包括选项的难易程度、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都会影响到进度和最后结果。比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不到五年就纂成初稿,而修订和制版印刷竟用了15年,出版时连他的名字也没了。由此也就扯出铜活字的一段公案。
《古今图书集成》的规模太大,雇人写版刊刻将旷日持久,板片的需求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印完后的贮存也会成为大麻烦,主事者决定以铜活字排印,以故该馆又被称作“铜字馆”。自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相继出现木活字、铅活字、铜活字,明代中叶无锡的华氏、安氏两家书作坊,即以使用铜活字著称,所刻有《锦绣万花谷》《百川学海》等书。清代江苏、福建等地仍流行铜活字版,其技术已臻完善。《清会典事例》明文记载武英殿有铜字库,设置一名管事(库掌),两名管理人员(拜唐阿),“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但语焉不详,很多事情长期误传。兹引据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稍加梳理——
一、设置。武英殿铜字库是何时批准设置的?换言之,铜活字是何时进入武英殿的?未见确切记载,在康熙前期和中期,也未见有铜活字出版物流传。在清代文献中,古今图书集成馆又被称作铜字馆,所以也可将康熙五十五年开设集成馆作为一个节点,或曰亮点。此前即便已有了一些铜字,应非机构设置,数量亦相差甚多。
二、制作。铜活字的制作有铸造和镌刻两种:铸造是以硬木刻字,翻成砂模,注入铜液铸成;镌刻则先浇筑出不同规格的铜子,再由匠人在上面刻字。史籍记载“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故宫专家翁连溪经过细心比勘,认为清代内府铜活字皆是刻制的,“字体规整,墨色鲜丽,笔锋尖锐,如刀刻所出的效果”,相比之下,铸字就显得“笔画迟钝,立体感差”,这是行家之论。
在铜上刻字当然不易,可也难不住专门的匠人。翁连溪曾算过一笔账:“如按每人每月工银两钱计算,刻铜字人每天要刻5个铜活字,按每月30天算共刻字150个,25万铜活字由50人镌刻,要用近3年的时间。这以当时清内府的财力、人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他说的时段应在康熙五十五到五十八年,此后《古今图书集成》已开始印刷,时间上亦相合。而问题在于刻字量,铜字馆所存活字远远大于25万个,看来情况要复杂得多。
三、数量。关于武英殿铜活字的数量,说法有25万、30万、100万等多种,项旋从内务府档案中查的实数,为101.5万多,精确到个位,从而一锤定音。而也附带引出一个疑问,需要那么多吗?翁文提到的25万个铜活字,应是参照了后来武英殿聚珍馆木活字之数。而聚珍版图书品种有限,集成达一万卷、40多万页,需求量自会大得多,100多万个铜活字的总数,应是经过详细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铜活字的刻制,如果翁文所称每天刻五字大致靠谱,对刻工的需求多一倍也不止,怎么办?我想大约会以发样订购的方式,北京有此类作坊,江浙也会有,将书版所用大小字样发给照刻即可。至于武英殿设刻铜字人,应用以缺字时补刻为主。
四、使用。推测在集成馆正式设立之前,已决定采用铜活字印刷,采购铜材,铸造铜子,选择作坊分包刻字等项已然开始。其使用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盛字箱格、木槽板,要有拣字熟手、校对、打样、复核,而且也不可能只有一组人马。书缺有间,则往事必然如烟,具体之操作,今人也只可推想了。
五、销毁。这一套来之不易、价值高昂且对内府出版做过大贡献的武英殿铜活字,于乾隆九年竟然奉旨销毁。弘历《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毁铜惜悔彼,刊木此惭予”二句,小字夹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为非计。且使铜字尚存,则令之印书,不更事半功倍乎?深为惜之!”此时已是三十九年五月,忽忽30年过去,要兴办《四库全书》了,乾隆才对当年之举深切追悔。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说铜字被改铸成铜钱,错。乾隆九年冬原雍亲王府改为喇嘛庙,应管理武英殿事务的和亲王弘昼之请,用铜活字铸了雍和宫正殿的三尊高约两米的大佛。
武英殿铜活字的销毁,当年还引发了一桩贪腐案,牵涉人员也不少。据乾隆十八年六月内务府慎刑司呈奏:
查武英殿奏销档内,有雍正十一年奏明,贮库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后经乾隆九年奏交铸炉处时,永忠、郑三格只将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奏交铸炉处,其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并未入奏……
永忠为大清宗室,授辅国将军,时任内务府员外郎,被审讯时供称:具体管铜字作的是原任员外郎郑三格,经他查明铜字有101.5万余个,另有从太监何玉柱抄出的无字铜子18.8万多。郑三格说这些铜字收藏日久,难免有遗失,建议将何家抄出的留下,以备补救。永忠听了他的话,只将铜字馆所存奏明和亲王,交铸炉处收讫。后见大小铜子仍有18万多,遗失的不多,“不敢将留下的缘故回禀和亲王,是以称说是早年抄家的遗漏未载,王爷可以留用。和亲王说既是余出来的,你们送往府里来罢。将18万余个铜子我同姚文彬送了一次,同郑三格送了一次,两次送完了”。
武英殿铜字库库掌崔毓奇供称:“乾隆九年冬月据员外郎永忠、监造郑三格叫我速查铜字数目,要交造佛处。即照档查明,向永忠、郑三格报明。永忠、郑三格恐数目有差,郑三格要了档子去,照数查看,数目不少。永忠、郑三格派我送到经史馆,永忠、郑三格亲收。”他还提到曾有一本铜字档,遵照永忠的指示交给内务府档案房的笔帖式常宁。接下来审讯常宁,则交代是有过此事,自己收下后即归档保存,“后监造郑三格亲身到档子房来,将档子要去,我后来向他要过几次,他因循着并未曾给回与我,后年久了我也就忘记了。”
18.8万多枚备刻铜子,可不是个小数,永忠等人用以巴结和亲王弘昼,弘昼也就大大咧咧地收下了,据说是铸了些缸、罐啥的。那是个有名的荒唐王爷,跟哥哥弘历也曾当面叫板,案件追查到此,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