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文化“杂交”
作者:维舟 在欧洲流行乐坛上,黑人音乐向来是最不可小觑的存在之一。然而,如果仔细想想,所谓“黑人音乐”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称呼,至少它不像爵士乐、摇滚乐那样是按音乐门类来分的,世上可也没什么“白种人音乐”这种说法,那为何唯独黑人在流行音乐领域的表现如此突出,以至于出现这样特定的称呼?当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归结为这一族群某种神秘的“天赋”,就好像以为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一样,但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
在欧洲流行乐坛上,黑人音乐向来是最不可小觑的存在之一。然而,如果仔细想想,所谓“黑人音乐”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称呼,至少它不像爵士乐、摇滚乐那样是按音乐门类来分的,世上可也没什么“白种人音乐”这种说法,那为何唯独黑人在流行音乐领域的表现如此突出,以至于出现这样特定的称呼?当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归结为这一族群某种神秘的“天赋”,就好像以为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一样,但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在此,最为吊诡的一点是:这种被看作黑人文化“本质”的东西,仿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性,其实却是在多元碰撞的现代化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如今那种“典型”的黑人音乐,其中的很多元素并不一开始是黑人的,实际上,在两三百年前可能根本就没有“黑人音乐”这种东西——这乍看起来是与其身份紧密相连的传统,但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如果它是传统,那也是不断变动的传统。
这当然与欧美黑人的特殊历史遭际有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五百年里,没有哪个种族像黑人这样,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流散、漂泊,并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挣扎着活下来。如果说现代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无家可归的,那么黑人的经历则尤为漫长痛苦,毕竟他们不仅被从自身原有的传统和文化中连根拔起,而且还要作为最底层的群体,接受陌生的语言、礼仪和文化,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呈现出混乱、无序又鲜活的构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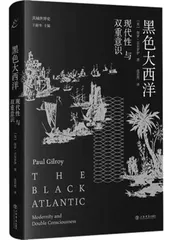 《黑色大西洋》
《黑色大西洋》
所谓“黑色大西洋”,就是基于这一经历,认为以非洲裔美国人的流行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杂交性和混合性的,从而否定对“种族”纯洁性的迷恋,那种危险的执念不仅带来纷争,也是对历史的误解。英国学者保罗·吉尔罗伊之所以提炼出这一概念,还不仅仅是为了黑人身份认同本身,因为就像他在前言里强调的,“黑色大西洋的历史带给我们一系列有关身份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的教益,它们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在重新生成中”。
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曾指出,黑人内化于美国人身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双重意识”:“一个人总是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种灵魂、两种思维、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战;两种交战的理念同在一个黑色的身体中,凭其顽强的力量才不至于被撕裂。”这当然是为了指明美国黑人时时刻刻处于撕裂的艰难处境,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只拥抱某种同一性,而必须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模式中自处。
按照族群绝对主义的观点,这种混杂性是“一连串的污染和不纯”:对美国黑人来说,除了肤色,没有什么生来就是他们的,不管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了在陌生的新大陆上生存下去,都无法真正排斥任何文化元素。虽然种族通婚长期遭到严厉禁止,但在文化上,黑人不得不持续经历彻底的重塑过程,这反而给黑人音乐带来了活力和复杂性。
那么,为什么是音乐?这当然是因为音乐并不会直接冲击奴隶制的等级秩序,作为一份自由象征性替代品的吝啬礼物,得到了容许,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艺术表达也成为了奴隶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方式,换句话说,“音乐应该享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它能直接表达奴隶的意愿”。重要的是,这不仅证明了黑人和所有人类一样富有创造性,超越了物质生活的简单需求,工作也并非只有奴役、悲惨和服从,而且这种艺术表达还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为之划定的边界——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跨国的文化现象。
从19世纪中叶起,音乐常常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特性的象征出现,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然而黑人文化却没有这回事:它原本就是在大西洋两岸的流动中产生的混杂文化,黑人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不同的黑人群体之间恐怕就像中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像雷鬼乐虽然常被视为一种黑人独有的、来自牙买加的风格,但它的源头本身就是混杂的产物;同样的,嘻哈文化产生于美国黑人通俗文化和加勒比流行文化的混合。
看似奇怪的是,像英国这样的殖民势力,却又可能反过来成为黑色大西洋政治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就是说,黑人文化并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是在某个边界清晰的地理单元内封闭自足的,而是可以利用任何跨国的流动性,并与之共生。这里有一种“开放的黑人性”,与那种狭隘的民族身份认同截然不同,而是始终在流动中变化、融合、萌生出全新的可能,用本书的话说,“音乐在黑色大西洋中的传播和演变,摧毁了把非洲、本真性、纯洁性和根源与美洲、混杂性、克里奥尔化和无根性对立的二元结构”。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不仅是因为这扭转了对黑人文化的评价,为黑人的自我身份打开了新的视角,还因为一种开放性的理念。传统的种族主义突出种族纯洁性,敌视流动、混杂,尤其贬低和恐惧混血,然而,后现代性则相反,歌颂文化混杂。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早在1998年就指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趋势,就是一种对“交叉、杂交和混杂”的赞美,而原先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那些事物(诸如种族、等级)则都被纷纷解构为“虚构的存在”,鲜明、严格的文化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殖民历史上,那些不同文化遭遇的“接触地带”都是充满张力、冲突和活力的地带,由此才可能通过文化交流创造出新的可能。“黑色大西洋”正是反对那种以纯洁性的概念来作为种族团结的基础,因为如果黑人文化的活力正是来自开放性,是多元化促进了文化混杂,那么自我封闭之下形成的黑人特殊性,到头来极有可能会是文化衰败的开端。
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认为,现代世界其实人为地割裂了现实生活的整体性,“世界大同”从未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的张力也从未消除,只是制造了更多的“杂交体”——例如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化就是“中西合璧”。问题是,为了抵抗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又仍有必要坚持本土文化的差异性,否则最终出现的可能就是大量地方性文化的消亡。如何既保持自我,又能在文化混杂中创造出新的可能,这可能是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 黑色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