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翦而华夏兴
作者:叶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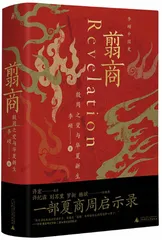 小时候第一本我从头到尾看完的书是《战国故事》,里面的很多故事中都有一个智者,向一位君王讲述一个故事,从而说明一个道理,而这位君王也很通情达理,能够听从智者的劝谏。相信很多人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都会有与我类似的感受:那是一个遵循礼义的世界,就连打仗也要讲理、讲德,不可半渡而击。不懂礼的王,要么是蛮夷,要么是暴君——就像始皇嬴政,建立了大秦帝国仍要被世人唾骂,短短二世便被终结。
小时候第一本我从头到尾看完的书是《战国故事》,里面的很多故事中都有一个智者,向一位君王讲述一个故事,从而说明一个道理,而这位君王也很通情达理,能够听从智者的劝谏。相信很多人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都会有与我类似的感受:那是一个遵循礼义的世界,就连打仗也要讲理、讲德,不可半渡而击。不懂礼的王,要么是蛮夷,要么是暴君——就像始皇嬴政,建立了大秦帝国仍要被世人唾骂,短短二世便被终结。华夏文明,礼仪之邦。我们似乎天生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翦商》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华夏旧文明的历史,在那个“礼”字当先的春秋出现之前的历史,一段曾经被历史刻意遗忘的历史。虽然这些历史并不是什么新鲜出炉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此密集、如此连贯、如此缜密地呈现,仍然是撼人心魄的,甚至令一些人难以接受。
从更宏大的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讲,所有文明都是从野蛮中成长起来的,华夏文明亦不能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质是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的,那便是同类之间的杀戮。无论是非洲东部稀树草原上的人类共同祖先之间,还是先后走出非洲形成的不同人属物种之间,抑或是新大陆上新旧文明的碰撞、在热核反应中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至今日仍在响彻的枪声,无不赤裸裸地宣扬着我们同类相残的本性。
然而还有一种将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地球生命的特质,那就是同类之间有意识、有组织的合作。人类凭借瘦小的身躯和简陋的武器就能将巨型陆生动物赶尽杀绝,靠的正是合作。人类的语言是为了更高效的沟通与合作;人类在孩童时代就明白用手指指向某物的动作含义,是为了在悄无声息间完成合作;人类创造了地球上此前从未有过的音乐与舞蹈,在“嗨”的过程中达到精神与意志的同步,从而更好地合作;人类还创造了宗教,并在杀戮纷争的时代发现宗教可以用于团结人群,促进不同背景的人们无条件地合作。
人祭正是在同类杀戮与同类合作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统一性。《翦商》从早在夏商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原始文明讲起。它们如同地球上任何其他的原始文明一样,会杀死战俘,以战之名献祭。在南美的亚马孙雨林中,以及在赤道几内亚等隔绝封闭的岛屿上,由于缺少大型陆生动物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所以部落文明一直将杀死并吃掉战俘的习俗保留到了现代。
然而对于我们的先祖而言,杀俘不是为了解口腹之欲。杀俘是战斗动作的惯性延续,是对仇恨的消解,也是对仇恨的张扬。同时,杀俘又是为了团结族人,同仇敌忾,为即将开始的新战斗做好准备。
当部落联合为国家,杀俘依旧,同时又出现了人祭。特别是到商朝兴盛以后,人祭之风也达到了疯狂的巅峰。国家要以人祭天地、祭鬼神;王侯公卿要以人祭祖先、祭高堂;就连各行各业也要以人祭祀,保佑技术上不可控环节的稳定产出。干将、莫邪投身熔炉,显然不仅仅只是大胆的想象,倒更像是日常标准流程的艺术化。
商代的人祭,其实在当时的背景来看,是对生产力的极大浪费。《翦商》也提到,人祭是通过牺牲现实利益,来换取王权与神权的合一与稳固。但是,商朝当时的青铜器冶金术与其他领域各种生产技术都处在相当高的水平,商人无论在农业上,还是在战场上,都能“以一当十”,这或许才令他们有了条件,去选择血腥的人祭来巩固王权。事实上,人祭虽然自夏至商初都存在,但直到商中期才变得越来越普遍,似乎也与商朝的国力日渐强大有一定的关系。
《翦商》详细梳理了周朝的兴起,以及其伐纣翦商的历史进程,并举证了人祭制度在周朝的彻底消失。至于其中的原因,《翦商》归结为一个人的恐惧,那就是周武王死后实际执掌大权的周公旦对于人祭的心理阴影。
周公作为周文王的儿子,跟周文王一起在商纣王的逼迫下吃了伯邑考的肉(也有史料称纣王骗他们吃了用伯邑考的肉烹制出来的食物,《翦商》更倾向于前一种记述)。那么,文王吃下的是自己的长子,而对于周公来说,他吃下的则是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朝夕与共的兄长。周公掌权后,大力推行祭祀制度的改革,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全面禁绝人祭。为了不让后人有机会重拾这种野蛮的制度,周公还要把它从历史中消灭掉。他清除了关于商朝人祭的文字资料,并且在自己朝代的文字记述中也避免直接提及“人祭”,导致很多涉及于此的文字读起来隐晦难解。《翦商》认为,之所以周公有如此大的动力做这件事,就是因为他曾经吃掉自己的兄长,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关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历史上的任何人,其作用或许看起来伟大,不可替代,但其实可能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历史不能重来,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但如果回到生产力的角度上来看,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顺应了历史的需要,就会取得成功;如果悖逆了历史的需要,则很可能失败,然后再换一个人来当“伟人”,做出正确的决定。
周公或许的确由于严重的心理阴影而取消了人祭制度,但是从他所做的很多其他决定来看,他一定还有某个更为理性的驱动力,而这个驱动力又恰好与生产力的需求是相一致的。
顺着《翦商》对周朝初期历史的梳理来看,这个新兴的王朝面临的可谓是内忧外患的境地。在内,商朝几百年的遗留不可能一朝间清理干净,不断有商人遗民造反叛乱,威胁着新政权;在外,戎人等蛮族已经掌握了马车等新技术,不断骚扰着周朝的边境。更加之随着版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部族、民族被融入了周人的大家庭,如何稳定这些异族,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现最大程度的合作,这些都是摆在周公等西周初期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很显然,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人祭已经很难达成团结人民的作用了,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周公显然是一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统治者。他对人祭制度的彻底埋葬,让广泛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更让连年征战中的国家有了足够的生产力,可以满足粮食需求,更能够支撑大型军事行动的巨大消耗。
周朝初期另外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就是大举分封诸侯,“封建”便由此而来,建立了层级式的国家体系。然而这一点同样又是生产力驱使的结果。由于远距离沟通的成本太高、效益太低,最好的管理策略肯定是分而治之,而非中央集权。巨型恐龙在脊椎上进化出来的类似脑的神经节,正是这种难于集中管理的结果,进化的选择与人类的选择殊途同归。
分封诸侯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周朝进入了春秋战国的乱世,直至汉朝才最终结束了诸侯手中掌握政权、军权、财权的混乱局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连年战乱,才让诸侯们更加珍惜手中的生产力,让人祭这种制度在诸侯这个层面上也没有了重生的土壤。至此,商朝不仅在实体上灭亡,更在精神上完成了灭亡。随之而起的,是以礼义道德服人的华夏新文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今世界,无论是用猪牛羊,还是用青铜器乃至人牲,“祀”都已经不再能带给一个国家力量了。但是,“戎”仍是国之要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的野蛮并未褪去,而只不过是开启了“美颜”。
祀与戎之间的关系,正是《翦商》在探讨的,也是阅读这本书让我思考的问题。无疑,阅读《翦商》是一趟神奇的旅程,有震撼,有趣味,令人不能释卷。它的可读性构成了一次对作者观念的成功“推销”。当然,你可以不认同其中的某些论断,但你恐怕无法拒绝如此饶有意趣的阅读,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没有答案的思考。 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