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寺
作者:苗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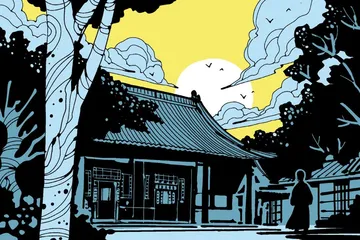 1901年秋天,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快要死了。他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有书记载,78岁的老臣“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李鸿章每次进北京,大多住在贤良寺。民国时期,贤良寺对游人开放,院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解放后,和尚被遣散,寺庙住持成为校尉胡同小学的校长,寺庙的部分房屋用于校舍。后来那一片改造为和平饭店、台湾饭店。有一年,某法国瓷器品牌在华尔道夫酒店办一次宴会,我穿过酒店大堂,被引到酒店大楼后身的一座小四合院中,主办方介绍,这座小院就是华尔道夫的总统套房,当年李鸿章住过的地方。那个院子想来应该是贤良寺留下的遗迹,但修葺极为精致,已经没有任何世事苍凉之感。
1901年秋天,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快要死了。他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有书记载,78岁的老臣“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李鸿章每次进北京,大多住在贤良寺。民国时期,贤良寺对游人开放,院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解放后,和尚被遣散,寺庙住持成为校尉胡同小学的校长,寺庙的部分房屋用于校舍。后来那一片改造为和平饭店、台湾饭店。有一年,某法国瓷器品牌在华尔道夫酒店办一次宴会,我穿过酒店大堂,被引到酒店大楼后身的一座小四合院中,主办方介绍,这座小院就是华尔道夫的总统套房,当年李鸿章住过的地方。那个院子想来应该是贤良寺留下的遗迹,但修葺极为精致,已经没有任何世事苍凉之感。
1901年阴历八月,王照到北京拜会李鸿章。王照曾参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从日本潜逃回京津,身份还是朝廷的钦犯。李鸿章在病中,让秘书于式枚接见王照。王照记录了二人见面的经过。于式枚对王照说:“老前辈从海外归来,必有挽救我们中国的策略,请就此畅所欲言,转达老相。”王照回答:“我无策略。况且天下事非一策一略所能转变。我们中国的缺点,在四万万人知识不够。俾斯麦言,普鲁士能胜法国之功,全在小学教员。日本埋头用功二十余年,教育普及,才能打败中国。”王照此行,是为了推广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这本书1901年夏天由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出版,是一本讲汉语拼音的书。贤良寺中,王照对于式枚说:“我今先莫说秀才、举人、进士没有能力,就说都有能为,全国共计二十万秀才、举人、进士,比日本五千万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少二百五十倍。以一敌二百五,还有什么策略可说!我的下等见识,中国政府非注重在下层的小学教育不可!但是中国的下层教育,有比外国最难的缘故,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语言文字合而为一不可!一切策略,我是外行。”于式枚听了,面有不悦,“这不像老前辈的雅言,老前辈必有雄谋硕画,不屑对我们小角色说出”。王照记录——余知其不懂人话,乃谢之曰:“我真是外行,不是不说。”遂辞而出。以上这段记录,出自王照的《小航文存》,“小航”是他的字。
王照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在鸦片战争时阵亡于定海。他在1894年中进士,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中国知识界有一股反思潮,全方位地思考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其中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有三个地方领先于中国,一是效仿西方设立的学校,二是报纸,三是图书馆,这三件事归结为一个源头,就是文字。天下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这就是普天下万国之公理,所以我们也要搞拼音。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方案。王照在戊戌变法后出逃日本,搞出来的《官话合声字母》也是一种拼音方案。他见李鸿章,大概是看出来推广拼音的关键所在——自己搞出一套拼音方案,编教材,教学生,推广起来太慢,也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方案,搞拼音这事儿,得由朝廷出面。
上海梵皇渡书院有一个用英文学医科的学生,叫沈学,他写的《盛世元音》1896年在《时务报》和《申报》上发表了片段。他在《自序》中说,汉字太难了,“共计字体四万九千余字,士人常用者唯四五千字,非诚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有几次十年”。他说,俄国、日本之所以强,就是用了本国的切音字,翻译西方的“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
沈学身上有很强的“民科”色彩,据说他发明了专门写字母的自动墨水笔,造了一种盲人书写工具,改进了盲人识字卡片,设计了一套哑巴用的看图识字卡片,还准备改进打字机和电报机。他的“盛世元音方案”是以速记符号作字母,基本形式有左弓、右弓、上弓、下弓、直弦、横弦、左侧弦、右侧弦等18种,这些符号兼表声母和韵母,区别在笔画的大小。听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掌握。沈学创建了这套方案之后,每到星期天,就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楼教课,他在《申报》上还登了一个小广告,“创制新字,译天下音义,八下钟尽人能悟,志在广播传证,并不因利。投一名刺,便可就学。如有更胜善法,愿酬洋三千元为资,敬无遗言”。我不太确定,沈学所说的“八下钟”是不是指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能学会一套拼音方案,有点儿速成班的意思。沈学生于1871年,1900年前后就死了,据说死前潦倒,沦为乞丐。
与沈学的“十八笔方案”相比,王照的方案更好理解,他取汉字偏旁为字母,确定12个“喉音”,也就是韵母,50个“字母”,也就是声母。对比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王照方案的声母更多,这是因为他要贯彻“双拼制”,不要三拼,比如我这个“苗(miao)”字就是三拼。在王照方案中,有一个声母为mi,用mi和ao双拼就拼出了“苗”。王照把“衣乌鱼”三个介母和声母结合在一起,这样韵母中就没有“衣乌鱼”开头的复合韵母,声母中就多了带有“衣乌鱼”的复合声母了。比如土字旁,在王照方案中代表声母tu,它跟形为“秃宝盖”的an相拼,就是“团”。再比如,shu是一个声母,再跟ang相拼,就是“爽”。很难想象,李鸿章要是见了王照,能有耐心听他详细讲解这套拼音方案。
1903年年底,直隶大学堂的学生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推广王照的“官话字母”,其中说道:“何谓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推广“官话字母”,头一个好处就是“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袁世凯做出批示:“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切音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结尾说:“姑候学校司体察情形,如何试办,妥酌具复,饬遵缴。”
王照生于天津,他的“官话字母方案”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这套方案传播到南方,两江总督幕中的劳乃宣看到,“深赏之,但惜其专用京音,于各省方言尚未包括”。劳乃宣征得王照同意后,就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拟定了宁音(南京话)和吴音(苏州话)两种方言的字母方案,另定了一个名称叫“合声简字”。劳乃宣原本就是音韵学专家,著有《等韵一得》,专门研究汉字语音的。他在《重订合声简字谱》自序中说,中国文字厉害,很了不起,但学起来太难,教育不易普及。“泰西以二十六字母,东瀛以五十假名,包括一切音;文与言一致,能言者即能文,故人人能识字,实为教凡民之利器。我中国数百兆凡民,欲令教育普及,非学步之不可。”
1908年,慈禧召见劳乃宣,劳乃宣向慈禧解释了合声简字的用处,还上了一份奏折,再讲教育普及的重要,其中说道:“立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将比里连乡,无一人能及公民资格,何以为立宪之凭借乎?”他在奏折中建议,初等小学五年一贯制,第一年两个学期专门用来学拼音,自第二年开始才学汉字。他很乐观地说,以国家全力行之,三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人人能看书,人人能读报,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人民之意见,皆能上呈。他这份折子和他的著作呈送上去后,慈禧太后批复“学部奏议”。然而学部却将此方案搁置。劳乃宣静候年余,杳无消息。
1912年,清廷完了,改民国了。王照写了一篇文章叫《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其中说:“吾国多数人,知识不足谋生,非教育普及万不能救。而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实为教育上一大障碍物。”他所说的教育,“既非前此学部所持尊孔尚武保国粹之谓,亦非令人人明于共和政体备有参政知识云尔也。所谓教育者,瞻瞩虽及高远,而致力专重卑迩。撮其要曰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定其旨曰生活主义融和乎道德主义,个人生活主义融和乎社会生活主义,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循理守分,质直光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王照说,学童教育是人人保全人格之本,可以称之为“质地教育”,跟政治教育、职业教育不是一回事。他提出向日本学习,要有一套完整的小学教育体制,第一步造就小学教员,“三年之内暂勿详计小学,必须先设师范四千五百校,所有全国已往之高小毕业生及初中生皆令为师范新生,计九十万之数所缺无多”。第二步遍立小学校,定为义务教育,姑假定为学生3000万,计其完备之时,通国校数共15万。“先能实行此二步,斯十年后已有蒸腾之势,二十年后元气充盈,三十年后物质文明蓬蓬勃勃发生于社会之中。”王照说,“天下事万无捷径,每言此,不避急功之士所厌恶。”
有些话,看起来真不错,比如“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说话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好事能够实现。王照晚年遁入佛门,1933年逝于北京。和他在贤良寺见面的于式枚是信佛的,他在李鸿章身边做了十多年幕僚,终身未娶,1907年曾经去德国考察宪政,民国之后隐居在青岛。他兄弟的儿子于孝侯过继给他当儿子,于孝侯的闺女叫于立群,是郭沫若的妻子。1949年,北京刚解放,毛泽东就指定黎锦熙、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都出自这个部门。
(参考书目:王照《小航文存》;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