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萨特正名的人
作者:薛巍 萨特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196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瑞典学院说:“他的作品充满自由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作者和哲学家,他是战后文学和知识讨论的核心人物……他的哲学被年轻人欢呼为一种解放。”他1955年访问过中国,1980年4月去世,但柳鸣九说,萨特的作品和思想真正进入到中国还是在80年代,“一个作家真正进入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定程度的本土化”。
萨特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196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瑞典学院说:“他的作品充满自由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作者和哲学家,他是战后文学和知识讨论的核心人物……他的哲学被年轻人欢呼为一种解放。”他1955年访问过中国,1980年4月去世,但柳鸣九说,萨特的作品和思想真正进入到中国还是在80年代,“一个作家真正进入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定程度的本土化”。
柳鸣九自称是法国文学的搬运工、摆渡人,但搬运不仅需要外语能力,也需要“探寻、发现、发掘、研究、鉴定、分析、阐释、说明、介绍、评论”。他当年对萨特的搬运就需要学识和勇气,需要首先对萨特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肯定萨特作品的意义。袁筱一等撰写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说:“萨特从40年代进入中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而80年代是这段相遇的高潮。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奠定了国内的萨特研究基础。”《萨特研究》198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62页,第一部分是萨特的三篇文论,《为什么写作》《答加缪书》和《七十岁自画像》,其次是萨特富有哲理寓意的文学作品,《恶心》《苍蝇》和《间隔》(现在一般译为《禁闭》),还有萨特文学作品提要、萨特作品评论等。这本书“为初期的萨特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最为全面的资料汇编,至今仍是该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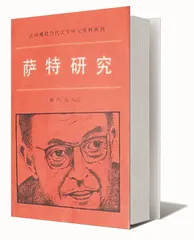 《萨特研究》附有柳鸣九撰写的25页序言。序言的第一节是他1980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回应萨特受到的责备和挑剔,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萨特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道路的一个显著的路标……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行动的强调。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
《萨特研究》附有柳鸣九撰写的25页序言。序言的第一节是他1980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回应萨特受到的责备和挑剔,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萨特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道路的一个显著的路标……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行动的强调。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
序言中还介绍了文章编选的原则,对选目做了解释,指出萨特的两个剧作《苍蝇》和《间隔》从正反两面表现了萨特关于自由选择、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哲理,说明“萨特所主张的自由选择无疑是具有十分明确的善恶标准和道德标准的。”
《萨特研究》选择的内容和柳鸣九对萨特的论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以至到2013年,他说:“至今我对萨特哲理的评价,特别是对他的核心哲理及其文学表现的评价,没有什么变化,也用不着有什么变化。”(除了尝试把萨特的《禁闭》翻译成《间隔》。)读萨特的人
英国萨特研究专家安德鲁·利克说:“1944年5月上演的《禁闭》也许是萨特最完美的剧作,不像《苍蝇》那样冗长和史诗式的虚荣做作,取而代之的是几乎预示了贝克特一样的简洁的语言和处境设置。三个被判了刑的人(一男两女),要在一个非常萨特式的地狱里共度永恒。没有镜子,他们必须依靠彼此的凝视和语言来维持和创造他们自身的形象。……《什么是文学》1947年发表于《现代杂志》,是萨特著作中最为人知也最难理解的一篇。”
利克提及的这篇论文《什么是文学》对作家角色的传统资产阶级概念做了批评,并提议一种新型的介入式作家。萨特写道:“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世界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在这篇文章中,跟他以前的作品相比,“他人”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年轻时也曾深受萨特这些作品的启发。1990年,哈贝马斯在接受美国学者查德·沃林采访时说:“‘二战’后求学时,我遇到了剧作家萨特……我看了《苍蝇》。在德国,这部剧作引发了深刻的形而上学解读。另一部戏《禁闭》则让我们熟悉了政治的萨特……他作品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不仅没有被超越,反而指出了如今广为传播的历史主义和语境主义取向的盲点。”
柳鸣九后来谈到萨特在中国的影响时说:“当年热衷于读萨特的人,很多人后来都在学术文化领域里有所作为,不少人已经成为名士,他们都是从萨特这所学校里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对学术文化感兴趣的人是不曾读过萨特,不曾热衷于萨特的,萨特曾经真可谓是他们的‘精神初恋’。萨特自我选择的哲理投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人群中个人对自主精神、选择精神的社会需要,这便是萨特热的真正根由。萨特之所以吸引人,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哲理的本质特征,他善于把哲理凝聚在隽永的表述中,如‘存在先于本质’‘英雄的自我选择决定英雄的存在’‘他人即地狱’等警句。”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6月出版后,只受到一小撮专家关注,在1943年和1945年之间,它主要被用于给政府配给的土豆称重,因为该书第一版的重量恰好是一公斤。1944年,萨特在法国也受到攻击,他被认定为绝望哲学的最高教士,《行动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攻击萨特的悲观主义,指责他败坏了青年人的道德。批评者认为,存在主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对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社会所感受到的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完全麻木不仁;他的思想是一种精神鸦片,使人陷入自恋,转移了年轻人要担负从法西斯悲剧的废墟中重建一个正义社会这一使命的注意力。
面对这种情况,萨特做了回击,尽力去证明存在主义是一种关涉行动、努力、斗争和团结一致的人道主义哲学。1945年10月,萨特做了公共演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希望由此澄清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曲解。托马斯·弗林在《存在主义简论》中说:“当时存在主义出现在每个人的嘴边,每个人都知道《存在与虚无》,但是很少有人读完了它。因为《存在与虚无》不仅很厚,而且是一部高度技术化的著作,融合了从笛卡儿到海德格尔之间所有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书中包含了许多令人迷惑的新术语,也包括了萨特对德国术语的特殊翻译与描述。书中还有一些口号,最臭名昭著的是‘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1981年,柳鸣九拜见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跟她谈到了萨特与加缪在自由观上的区别,他认为萨特不脱离社会条件,而加缪却有些形而上学。波伏瓦回应说:“是的,加缪也提倡自由,但只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种抽象的自由,而萨特,他虽然也认为自由是人自身的内部的要求,但他同时认为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环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质利益,也要通过物质利益表现。”确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具体哲学。存在主义并不给人们开出道德处方,道德选择没有严格的规则。但“存在主义所说的自由并不是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空洞的自由,通过接受其彻底的偶然性和统一性的缺失,这种自由就会变得具体”。 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