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锡熊:四库苦臣
作者:卜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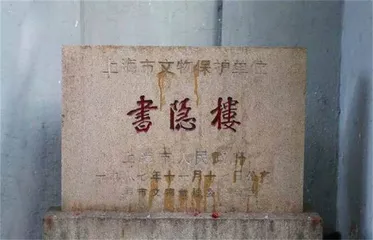 这四个字,是我从韦力的《四库全书寻踪记》中看到的。其中一节为“四库功臣,四库苦臣”,写的就是陆锡熊,拟题甚切。兹一分为二,先以“功臣”谓纪昀,再以“苦臣”状锡熊。其实言功言苦都是相对的:老纪日日埋首于书卷文稿之间,仍不免挨骂,大冬天带着一帮人往避暑山庄文津阁修订错讹,一切费用自理,岂非苦臣?陆锡熊属于四库馆开馆元老,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当然也是大功臣,而最后病死于隆冬的盛京,文溯阁修订工作尚未完竣,怎一个“苦”字能尽?
这四个字,是我从韦力的《四库全书寻踪记》中看到的。其中一节为“四库功臣,四库苦臣”,写的就是陆锡熊,拟题甚切。兹一分为二,先以“功臣”谓纪昀,再以“苦臣”状锡熊。其实言功言苦都是相对的:老纪日日埋首于书卷文稿之间,仍不免挨骂,大冬天带着一帮人往避暑山庄文津阁修订错讹,一切费用自理,岂非苦臣?陆锡熊属于四库馆开馆元老,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当然也是大功臣,而最后病死于隆冬的盛京,文溯阁修订工作尚未完竣,怎一个“苦”字能尽?
若细加甄识,纪昀与陆锡熊都不能算是最早入馆的。第一批选派承担《永乐大典》辑佚的30名翰林,当在三十八年二月中旬已就位,其中应有上节写到的励守谦,其他如刘校之、刘跃云、陈昌图等应也是那时入选的。而差不多两个月后,刘统勋等上奏“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才举荐纪昀、陆锡熊担任总办。两人刚上手就得到皇上的认可,五月初一有旨:
四库全书处总纂官翰林院编修纪昀、军机处郎中陆锡熊,着照懋勤殿翰林节赏年赏之例,各赏给一分。
请留意二人馆职的变化,原来叫总办,此时已称为总纂官。懋勤殿,取“懋学勤政”之意,为清帝在宫中的书斋,收藏历代书画秘本如《圣教序》《皇甫碑》《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墨迹》等,殿内悬有弘历御笔“基命宥密”匾额,日常有翰林官员在此值班。至于懋勤殿翰林年节享受的赏赐标准,查了一番,没有找到。
乾隆喜欢赏人,却也都有些依据,对二总纂的奖赏,自与他们提交的文稿质量相关联。弘历采纳了朱筠的意见,要求所有采录的古籍(不管是各省汇缴来的珍稀图书,还是自《永乐大典》辑抄的古本),皆须提交一份提要,注明作者、成书年代、卷数,并对内容做出简述和评价。各书提要多由纂修和分校官拟写,总纂官的职责之一是核订统稿。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知道能选在四库馆担任纂修者皆一时俊彦,没有几个愿意他人动自个的稿子,改得不妥便可能叫板,且对前代著作、人物的看法,也很难统一。未见二人记述在馆审读润改的情形,也不知在“二总纂”“三总纂”并列的框架下如何分工,只知道他们合作得很不错,尤以纪与陆更可称关系亲切。
陆锡熊,字健男,号耳山,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进士,列于二甲最后一名,给了个“归班铨选”,即等待分配。这个时间往往很长,等个五年八年都不稀奇。锡熊有些幸运,次年春乾隆南巡召试,他考取一等,授为内阁中书,渐迁至刑部郎中。通常的说法,是刘统勋推荐的纪昀,于敏中因师生之谊推荐了陆锡熊。其实统勋才是该科正考官,时任户部侍郎的于敏中为副考官,应该对锡熊都有了解,共同举荐。至于将纪昀放在前面,很可能是刘的决定,更有可能提前已向皇上请示并得到允准。
刘统勋兼掌枢阁,又当金川用兵之际,军政大事无不操心,因而辑佚与编书之事,于敏中从开始就管得较多。感谢张升教授的研究和发现,考定国家图书馆所藏署名陆费墀的抄本《顾斋文集》,实为陆锡熊所著,进而厘清四库设馆前后的多份重要文件和章程,皆由锡熊遵于敏中之嘱拟稿。如乾隆在收到朱筠的四条建议后,命军机处商议,刘统勋等于三十八年二月初六呈上详细答复,逐条做出回应,肯定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提议,并做出初步安排,此稿即出于陆锡熊之手,抄本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收几乎文字全同。可证锡熊虽非翰林,其学识见解则得到枢阁大员的高度认可,不仅于敏中,也必须得到刘统勋的同意。紧接着陆锡熊又起草了“初拟校阅《永乐大典》条例”,附在刘统勋等关于在翰林院设馆的奏报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上呈。原附件未见流传,抄本仅存六条,着重点在开列《永乐大典》征引书目,依照经史子集分类设立辑选的标准,大多被采用。
六月十六日,乾隆于避暑山庄传谕内阁,命对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逐条认真审核,纠正讹误,订补遗缺,编一部《日下旧闻考》,明确要于敏中做总编。随侍帝侧的于敏中次日即致函陆锡熊,请他帮着酌拟凡例,后者即草拟14条,多数被采纳。仅此数例,便可知陆锡熊很早就介入了四库馆的事务,不辞辛苦,也是一个操办大型官书项目的行家里手。当年八月,翰林院的辑佚成果不断呈上,乾隆亲自审读,开心时拈毫题评,特地对二总纂做出表彰:
办理四库全书处将《永乐大典》内检出各书陆续进呈,朕亲加披阅,间予题评。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纪昀曾任学士,陆锡熊现任郎中,着加恩均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
此时纪昀的职级尚在锡熊之下,但其曾任内阁学士,中进士又在前数科,排在了前面。而皇上夸奖二人学问优秀、校书勤勉,则并无区分。
刘统勋去世后,四库馆的实际操盘手换成于敏中,诸如修订体例、区别部类、决定去取等,多由他来把握,并随时向皇上奏报。于敏中对纪昀很客气,人前人后皆不失礼数,称“晓岚先生”,但显然更信任弟子锡熊。流传至今的《于文襄手札》,据陈垣先生及张升、徐庆丰等学者的考绎,乃于敏中在随扈乾隆木兰秋狝期间写给陆锡熊的信,计56封,内容几乎全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关。可知总裁官也不是甩手二大爷,尤其于敏中这个“主抓业务”的总裁,丝毫不敢怠慢,即便是跟随皇上在外地,仍要审读京师源源驰送的文稿,并不断发信提出具体的意见。他与纪昀也有书信联系吗?因无史料记述,不得而知,但从这批手札的文句间读出,即使有也不会多。而于敏中与锡熊书札密集,大约四五天就有一封,大至体例章程、应刊应抄的区分,具体到某书提要中的措辞,皆所涉及,套用今天的话是“做出指示”。
与之相关联,二总纂的排名有了些微妙变化,张升认为:“据档案及提要稿记载,大概从乾隆四十年开始,一直至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总纂官的排序已变为陆前纪后。”这一状况是可信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应不在于陆锡熊本人,而在于敏中理事用人的格局。锡熊做事认真,学问文字都不错,但与纪昀相比,一个是文星,一个是文吏,差距可不是一点点。舍彼而用此,应有纪昀爱自主、锡熊更听话的因素,也显出敏中喜欢弄权,包括编纂的主导权。孰知上面还有一个明察秋毫的皇上,于敏中以及陆锡熊的悲剧,或在此时已经伏下一脉。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