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之名:培训名校里的隐秘骚扰
作者:吴淑斌编辑·陈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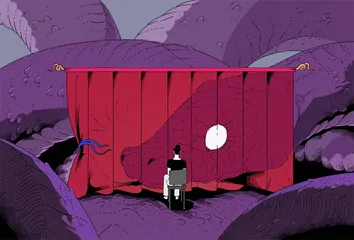 2014年,林琳16岁,在老家山东读高三,同时上着一家当地的艺考培训班。那时候,她的梦想是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去学图片摄影。林琳说,自己从小喜欢摄影,喜欢用图片来观察和表达生活。初中时,她就有了一台自己的相机,后来也持续地参加艺考培训。
2014年,林琳16岁,在老家山东读高三,同时上着一家当地的艺考培训班。那时候,她的梦想是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去学图片摄影。林琳说,自己从小喜欢摄影,喜欢用图片来观察和表达生活。初中时,她就有了一台自己的相机,后来也持续地参加艺考培训。
但这些经历和努力,与她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林琳想上的北影,是国内五所顶尖艺术类院校之一,也是众多艺术类考生的梦想。林琳听说,只有北京的考前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更能提高进入这所顶尖院校的命中率。她去百度贴吧上搜索,看已经“上岸”的学生在北影贴吧和“艺考吧”里分享备考经验,不少人提到了一家北京的培训机构“影路”。
2015年,16岁的于霖也想去北京。但和林琳不同,在高二之前,于霖都没有过学艺术的想法。家里没有“搞艺术的人和氛围”,父母对她的期待也和大部分普通家长一样朴素,“上一所好大学”。她的生活被上课、考试和作业填满,高三时,每周仅有半天假期,也是在家里复习功课。
于霖的文化课成绩并不差。但她所在的河南是高考大省,参考人数排全国前几位,省内却只有一所211大学,要想通过文化课的激烈竞争进入一所体面的高校,于霖的成绩“在河南是远远不够的”。高二上学期的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兴致勃勃地告诉她一条刚打听到的“捷径”——参加艺考竞争会小一些。一家人商量了许久,最后锁定的目标是国内的五大顶尖艺术院校,“家里人想着,既然已经打算‘剑走偏锋’,当然就要选最好的学校”。为了增加入选的可能,于霖在网上做了一番考前培训机构的搜索,最后也选中了“影路”。
根据“影路”的官网介绍,这所艺考培训机构创办于2002年,培训目标是所有艺考生都向往的顶尖五大院校: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到2014年左右,也就是林琳和于霖报名时,影路已经有了不小的办学规模和名气,每年能招收数百名学生,是北京三大艺考培训机构之一,尤其编导专业是其强势科目。创办人杜英哲是北京电影学院2001级文学系本科生、2018级文学系硕士,担任编剧的作品《小鲤鱼历险记》在2007年被央视制作为动画片。
来影路参加培训的学生,都在家庭的支持下付出了不菲的经济成本。2015年,于霖参加了影路20天集训,加上交通费、住宿费和餐饮费,花了大概3万元。这和她老家某河南地级市的培训班相比,费用高出一半多。于霖的父母是公职人员,月薪不过五六千元,“我在网上看到那个价格表,真是惊到了,想过贵,没想到这么贵”。
林琳在影路花的钱更多。先是报名了学费19800元的集训课程,后来还参与过一次收费近8万元的海外训练营。虽然觉得贵,但她们都咬牙支付了。毕竟,在当时看来,这是为梦想的投资。
“您理解梦想对高中生意味着什么吗?”2022年10月的一天,林琳和本刊记者通电话时,说到“梦想”,声音变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年代,是影视行业热钱最多的时候,整个行业的作品迭代非常快。大家都觉得影视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在里面大有可为。我为了艺术,为了梦想,可以付出很多。”
但她要和本刊记者聊的,不仅仅是在影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更有精神和心理上的代价。她曾在培训过程中,感受到了指导老师的性骚扰。当时年少的她无法确认自己的感受,也无法向旁人诉说。但那些经历留下的屈辱感,隐藏在她心里很多年。直到2022年9月19日,一位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施子怡公开发文,实名举报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的创办人杜英哲。文章称,从2007年开始,杜英哲多次借辅导的机会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导致17岁女生辍学生育,“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国内教育界性质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被害人数最多、被害人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场性剥削”。
施子怡的举报得到了很多女孩的回应。有至少21名在影路参与过培训的女生先后发文,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称自己曾经在影路遭受过杜英哲的肢体骚扰,“强吻、搂抱、抚摸都是常有的事”。甚至曾在影路兼职的教员也加入了控诉的行列。林子墨在影路接受过培训,后来又在这个机构担任了几年兼职老师。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曾被杜英哲以“试衣服”的名义实施过骚扰。杜英哲还给她看自己手机里与女性学员的聊天记录,甚至一些女学员的裸露照片。“杜英哲想证明他是真心在帮学生,有些学生和他有‘真感情’,还暗示我也可以拍这样的照片。”
9月22日中午,海淀公安发布通报,称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举证,已将杜某某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被刑拘前,杜英哲在朋友圈回应了女孩们的指控,并试图解释自己的“教学方式”:“要说明的是,无论‘重口味教学’还是‘顾问制度’,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最终这种对恶的失控利用,也吞噬了我”,“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争议,但也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艺术性”培训
来到影路之前,林琳和于霖对“艺术”的了解并不多。她们都成长于内陆小城,在家庭和学校两点间度过自己大部分少年和青年时光,尚未成年的人生平淡日常,没有经历过大的磨难,也少有印象深刻的情感考验。艺术性是什么?顶尖院校要求什么样的理解力和表达方式?什么样的人更可能穿过艺考的窄门,进入代表艺术殿堂的五大院校?她们希望从一家权威的培训机构里快速获得答案。
杜英哲曾是权威的“引路人”。他是老板,是老师,是学员们口中的“杜叔”,会讲授学员们从未接触过的创作知识,还经常宣称自己与某些学校的领导来往密切,“能左右录取名单”。他的教学方式很严厉。林琳记得,在一次20人的集训课堂上,有五六个学员迟到,杜英哲大发雷霆,要求全班一起罚站,怒斥“你们这样,对自己非常不靠谱不负责,这辈子都考不上的”。学员们对类似的断语深信不疑。如果他评价某位学员的外貌,“你的长相是很难考上某某学校的”,那位学员会因此沮丧很久。
对“什么是艺术”,杜英哲也有自己的“权威解释”。林琳记得,杜英哲告诉她们,“学艺术的人要更开放”。在影路培训时,他布置的作业会列出好几个选题,普通的历史、电影话题中穿插着一些与“性”相关的选题,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性经历、性幻想、性审美”去完成。“他会用非常专业的态度告诉你,这就是学艺术的人应该做的。他太正经了,以至于如果你对此产生怀疑,甚至会有点羞愧,觉得‘是不是我还不够开放’。”
林琳曾经创作过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名大山里的男人由于没有亲生孩子,买来一个被拐卖的小女孩抚养,最后在小女孩的父母寻来时,两人已然产生了深厚的父女情谊。在林琳的认知里,这个故事已经有相当纠缠的情理争夺,体现了艺术的复杂性,但杜英哲给出的建议是,“加上一些禁忌的父女恋情元素,才有爆点,能抓人眼球”。最终,林琳极不情愿地改出了一篇“非常别扭”的稿子。
用突破伦理禁忌的方式写剧本,只是教学的一个手段。培训的内容还包括什么样的着装更适合通过面试。于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曾经被杜英哲以“面试试衣服”为由,单独约到家中。当她在房间里换衣服时,杜英哲却突然走进来,对着还没有穿好衣服的于霖,非常认真地点评,“这件衣服不太适合面试”。“我当时真恨不得有个洞能躲起来。”于霖回忆,自己胡乱地套上衣服遮蔽身体,既觉得尴尬吃惊,又对自己的感受产生自我怀疑,“他的样子太正经了。我后来还想过,他是不是真的只是在帮我选衣服?”。
即便是现在——这些女孩已经成年并进入社会工作,但回忆当时的经历和感受,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有让人不适的情节都与“身体”“性”相关,这是一个她们难以坦然讲述的话题。在复述杜英哲对自己的言语骚扰之前,林琳会小声而礼貌地询问本刊记者:“可能有点不堪,您能接受原话吗?”于霖则不愿意过多回忆当时的经历。在谈到“性”相关的话题时,她习惯笼统地用“那些方面”来一概而过。
回到几年前,因为感觉羞耻和自我怀疑,更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自己的遭遇。在“艺术”的由头下,许多让女生们本能地觉得不适的内容从未被质疑过。她们甚至难以辨别,一些行为到底是“性骚扰”,还是艺术类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正常互动。
林琳记得,自己曾和另一位女生被杜英哲约至家中辅导,杜英哲给她们留了大量作业。凌晨5点半,杜英哲进入房间时,两人还没有完成。就在她们试图解释和道歉时,杜英哲和妻子陈昕不由分说,在女孩们的臀部各画了一只乌龟作为“惩罚”。“我本能地觉得特别羞耻。”林琳对本刊记者回忆,“但他很严肃,嘴里还说着作业的事,这让我感觉确实是我自己的错,没能写完作业,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林琳和同行的女生约好,绝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但自己还是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屈辱的5点半”。老板
在参加培训的年轻学员眼里,杜英哲是专业权威的。但叶玫却觉得,杜英哲并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叶玫是杜英哲的大学校友,晚一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与杜的女友陈昕曾是好朋友。她见过杜英哲的书架,没有文学小说、音乐CD,更多的是剧本写作、辅导书等教材类书籍。平时,杜英哲也不会主动讨论文艺电影,“他看的都是爆米花电影,他其实看不起文艺片,觉得商业片才能挣钱”。
不过,杜英哲“很懂一些创作技巧”。叶玫记得,读书时,杜英哲常常能接到些写剧本的兼职工作,他会把剧本拆成好多个部分,找叶玫和其他师妹当“枪手”共同完成,再分给她们一部分稿酬。“他能把一个剧本的章节拆分得很细致,像计件工程一样”,还会带着女孩们参加剧本创作会,看自己如何和甲方谈剧本、谈创作。“像是带我们去见世面,我们都是小地方来的女孩,当时完全不清楚以后即将步入的圈子是什么样的,看他们谈合作觉得很厉害。”叶玫对本刊记者说。
实际上,杜英哲也来自一个“小地方”。他的老家是承德,2001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承德当地的艺考培训机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如今承德每年能考上北影的人仍是凤毛麟角,“放在20年前,绝对是一件大事”。
但大学同学对杜英哲的印象却不怎么样。张宏与杜英哲在大学军训时相识,他回忆,军训没多久,杜英哲就开始欺负一名戴眼镜的瘦弱男同学,动手扇同学耳光,理由是“这个男生不洗澡”——其实那名男同学来自缺水的甘肃,没有频繁洗澡的习惯。另一位同学告诉本刊记者,杜英哲曾经在男生宿舍里公然殴打当时的女友,“把女生的脑袋往床边砸”。
后来成为杜英哲女朋友的陈昕,是他开办影路的合伙人,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女孩们指控的对象之一。叶玫和陈昕是大学室友,她记得刚入学时对环境很陌生,自己一个人躲到阳台上抽烟,陈昕从宿舍里出来,拿出烟盒递给她一支,两人一起抽起来,“我当时就感觉我们俩是同一类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叶玫觉得,陈昕漂亮,有亲和力,笑起来时眉眼有点像徐静蕾,爱穿一件白色衬衫,气质洒脱,而有些肥胖的杜英哲“配不上陈昕”。学员们对陈昕最初的印象是一个“温和的长辈、老师”,关心这些独自来北京求学的女孩子们,会邀请她们吃饭、逛街。于霖和林琳回忆,也正是有陈昕的在场,她们才答应了杜英哲一些去私人场所的邀约——但在这些场合中,陈昕常常很快消失,只留下杜英哲和女孩子们相处。
不少影路的老师是考上名校后回来兼职的学生,从前是杜英哲的学生,成为老师后是杜英哲的下属,即使对身边的异常状况有所察觉,也不知如何应对。林子墨告诉本刊记者,她早就听说过关于杜英哲性骚扰的风言风语,自己也遭受过言语上的骚扰,但无法确证整个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这些行为很私密,我从来没有真正遇到求救者,也不会抓着某一个女生去问‘到底怎么回事’”。有一次,一名女生向林琳提到,自己要到杜英哲家里去接受单独辅导,林琳把她拉到一边,叮嘱她“不要去,我给你辅导就行,我讲得更好”。这个说辞并不有力,却是她当时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
 影路成立于2003年左右。在杜英哲一位大学同学的记忆里,那是艺考刚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初,《还珠格格》火遍全国时(艺考热)就开始了”。
影路成立于2003年左右。在杜英哲一位大学同学的记忆里,那是艺考刚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初,《还珠格格》火遍全国时(艺考热)就开始了”。
叶玫也是那会儿参加艺考的。她记得,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艺考培训,考生可以准备的内容只有些文艺常识小百科。她从书店里买来一本薄薄的百科丛书,背下来应付笔试,其余的只能靠天赋和临场发挥。如果有人想得到一些训练,需要拜托熟人找到心仪学校的在校生,请对方“画重点”,并口授一些面试技巧。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找到这样的熟人。
影路就从这个时候起步,全名是“影路站台艺考培训”。“杜英哲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命名,就是知道学艺术的孩子大多是文艺青年,会喜欢贾樟柯。”叶玫记得,最初的办学场地就在杜英哲和女朋友陈昕租住的一室一厅,一间是教室,一间当宿舍,杜英哲从学校里找来同学或师弟师妹当老师。
团队成立之初,杜英哲便着力于将原本“口口相授”的零散备考内容,用课程和教材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一套应试化的模板。他找来五大院校的在校或毕业生,把校内的课程体系、授课内容、学习片单都尽可能详细地罗列出来。每年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要记下真题,带回来交给影路,分析不同老师的出题风格和偏好,好在下一年的培训中针对性练习。
这种将应试经验体系化的教学方法,很快取得市场成功。影路开班仅一两年,叶玫就看到陈昕在宿舍里的大量现金,百元一捆,用大袋子装着,沉甸甸的,要和杜英哲一起开车运回承德老家。此后近20年,艺考热度不减。尤其自2014年,影视公司进入了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资本化的阶段。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A股涉及影视行业的并购事件仅有7起,而2014年涉及该行业的并购事件共44起,公布了标的价值的并购38起,涉及资产价值301.76亿元——这个数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还在攀升。一位制片人回忆,那段时间,影视项目几乎是不愁钱,几千万元的投资说到位就到位。“大家都在抢好的项目,一般有不错的故事,再有流量明星加持,基本不差钱。”
这股风气也影响到了校园内外的学生。吴桐是北京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副教授,长年教授本科生课程。2014年到2017年,吴桐收到的学生假条数量明显多了,理由几乎都是试戏、谈剧本。“你会觉得,好多人都蠢蠢欲动,好像这个行业里的成功是唾手可得的。”
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本科计划招生604人,报名人数大约为2.8万多人,报录比达到47∶1;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考试报名人数8000余人,报录比近400∶1。影路也在这轮浪潮中循环利用学生资源,实现了机构扩张——将从影路出去成功考上五大院校的学生发展成为机构教师,以此获得在校老师和课程的最新信息。影路的教学楼也从出租屋搬进了商业大楼,从一个小客厅拓展到了两层楼,学生数量从每年十几人发展到三四百人。一位影路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常看到陈昕换不同款式的奢侈品牌眼镜、挎包,还听说“杜英哲在国外都买了房子”。
即便在近10年里,艺考培训市场竞争激烈,越来越多机构加入其中,影路仍然依靠开发高端业务,站住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大概在2013年以后,影路推出“VIP班型”,学生可以任选机构内的所有课程,接受老师的一对一指导,收费接近10万元;还开发了单期费用超过10万元的“海外训练营”。林琳参加过一期,觉得“就像一个夏令营”,去的是容易办下签证的国家。影路的带队老师会带学生参观当地的著名景点,再租一个大屋子作为授课室。在这里,“学员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些,厨艺好的学员会主动下厨”,但课程内容与国内的差别并不大,只是有时会把故事写作的背景设置为国外。另一位参加过泰国训练营的学员告诉本刊记者,杜英哲会带大家去“红灯区”酒吧体验生活,“里面很混乱,他顺势摸你一下,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救命稻草”
采访中,虽然对杜英哲有很明确的指控,但说到影路,很多学员的感情很复杂。
不止一名受访者提到,在应试上,影路和杜英哲是有专业能力的。浙江女孩慧娟甚至称其为“救命稻草”。2012年,她从老家到杭州,再从杭州独自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火车来到北京,参与影路的培训。那里的培训方式像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至今对一节故事写作课印象很深。老师在教课时,要学生“深挖自己内心的创伤,剖析自己,和自己对话”,这是她之前在小城市培训班里从未接触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机构里的讲师都是几所艺术名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常常会在上课之余分享真实的校园生活,慧娟感觉“进入了几所名校的小圈子。在校学生的经验和知识都能够帮助你,我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对这些经历单纯的高中生来说,艺考更大的难度在于对艺术性的把握和评判。“艺考不像传统的考试,花时间反复刷题就能考高分,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人的审美和感觉,以及阅历、经历。”林子墨告诉本刊记者。想冲击五大艺术名校的考生里,有不少生活经验丰富的社会考生。一位学员回忆,自己在影路接受培训的那年,认识了一位连续三年报名影路的考生。他已经30多岁,大学毕业后建立过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但始终有“上北电的梦想”,每年都在参加培训和考试。
相比之下,一直生活在高中校园里的学生显得稚嫩许多。在上课和担任讲师的过程中,林子墨发现,大多数学员的经历单纯,根本无法为写作课提供足够丰富的材料。“很多要参加艺考的学生,甚至没有阅读过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他们读的都是高考要求的名著,这和艺考肯定有差距。老师让你写一个故事,是写一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故事,还是一个带着禁忌元素的故事更容易被青睐?显然后者还是更高级一些。”林子墨说,普通高中课堂上不会出现的内容,在艺术课堂上是常态。“一些有情色镜头的禁片,大家在课堂上一起看电影、拉片,你会觉得我不该看禁片吗?不会。你会觉得我是在更好地提升自己。”
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也告诉本刊,“艺术是见仁见智的,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会比大众作品更强”。他觉得,突出性、爱等因素的作品,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并不是禁区,但作为教学方法时,“有些人天生就很害羞,明显不适合这种学习方法,更不应该以此刺探学生的隐私或者满足自己的私欲”。林琳上大学后才发现,杜英哲所要求的“根据性幻想、性经历创作”,并不是必须学习的内容,“在学校里,课上学的都是《茶馆》这类严肃文本”。
但在好几年前,年轻的学员们并没有能力提出这样的质疑。在影路,学员们的时间几乎全被学习填满。集训课程安排得十分密集。慧娟参加培训时,影路是封闭式管理,宿舍就在教学楼对面,吃饭只能点外卖,作业常常写到深夜。“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很多人又是‘半路出家’。每个人都默认所有时间都应该用来学习。”也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许多学员受到骚扰后,很难做出反应。慧娟曾经被杜英哲和陈昕以“泡温泉”为由约出去,受到了性骚扰。当时,慧娟觉得自己一下子“蒙了”,“那样的环境下,学习压力非常大,面对一个严肃、专业的老师,你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去揭露他、质疑他吗?好像说服自己先专注考试才是最正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林子墨在同一间宿舍里头对着头睡觉,两人却从未提起彼此都受到过性骚扰的事情。打破沉默
林琳至今还保留着那张杜英哲在自己臀部画画作为“惩罚”的照片。她把图片和自己的经历发到微信朋友圈,很快收到杜英哲发来的消息。面对实名举报,杜英哲最初的回应是强硬的,“人性很复杂,我没法猜测几位站出来指控我的女性真实的心路历程,但我愿意拿事实跟她们对线”。
“没想到第一个出来对线的人是你。”林琳收到的信息这么写道,后面跟了一个微笑的表情。随后,杜英哲也发了条朋友圈,是一张林琳的照片。“这是威胁吧?”林琳对本刊记者回忆,“我那天晚上害怕极了。”
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女孩站出来,回忆自己当年的遭遇。慧娟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都刻意不去想这件事,“不愿意去细想遭遇的事情是什么性质,在心里化解了它,自我安慰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最终,在看到其他女生的自述时,她觉得震撼、愤怒、惋惜,“没有想过居然会有这么多受害者,痛恨自己,为什么早知道可能会发生这一切,却没有及时制止”。
离开了那个可能帮自己进入名校的封闭权威的小空间,许多女生能更清晰地确证,自己遭遇的是性骚扰。她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受害者还在保持沉默。“我认识的一个女生,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有些人是被哄骗了,觉得自己是在和杜英哲谈恋爱,有些人甚至和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不正当关系。她们觉得自己不是‘完美受害者’,没有立场站出来。”林子墨看过杜英哲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他总是会说自己和对方是真爱”。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反家庭暴力律师李莹关注性骚扰领域已经有20年,她告诉本刊,发生在职场、学校等特定环境下的性骚扰与公共场所不同,双方之间往往存在权力关系,施害者进行“洗脑”的情况也更容易发生。李莹说,不少女性在性骚扰或是性侵发生之后,会与施害方“谈恋爱”,这其实是受害者的防御机制。“在侵害发生后,女性很容易产生羞耻感和自责,责怪自己不够勇敢、没有做出拒绝,受害者觉得,必须得让自己爱上对方,才能把侵害合理化,心里才能过得去。”
20年里,李莹见过许多次反性骚扰的浪潮,每次都有女性率先站出来打破沉默,带起更多的人。但在李莹看来,社会不应该只要求女性“勇敢”。“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些女性的处境,‘拔剑四顾心茫然’。如果相应的社会救济系统还不够完善,女性会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甚至还会遭受非议,她们站出来后反而是茫然的。所以,谈到性骚扰时,不应该总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去考虑,这不只需要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整个社会的觉醒和法律、支持体系的完善才是最重要的。”
(文中叶玫、林子墨、林琳、吴桐、于霖为化名,实习记者申三对本文有帮助) 性骚扰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