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辑佚第一人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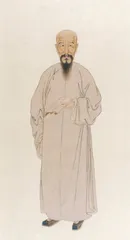 透过高不骞《检书行》的描述,可见在皇史宬正殿最吸睛的,是中间石台上的金匮。“安置金匮二十六,签牌夭矫拿虬龙。造端大清实录字,中有二祖左太宗”,也可证明多数金匮此时是空的,留待后世贮藏之用。张能鳞所见居于C位的《永乐大典》被从金匮取出,放入周边的橱簏。即便如此,它的身份也显得有些与环境不类,毕竟这是皇家的典章库啊,可终康熙一朝似乎并未加以移动,而以兴修《明史》个别外借,则是有的。
透过高不骞《检书行》的描述,可见在皇史宬正殿最吸睛的,是中间石台上的金匮。“安置金匮二十六,签牌夭矫拿虬龙。造端大清实录字,中有二祖左太宗”,也可证明多数金匮此时是空的,留待后世贮藏之用。张能鳞所见居于C位的《永乐大典》被从金匮取出,放入周边的橱簏。即便如此,它的身份也显得有些与环境不类,毕竟这是皇家的典章库啊,可终康熙一朝似乎并未加以移动,而以兴修《明史》个别外借,则是有的。
《永乐大典》的移出皇史宬,可确定是在雍正年间,但具体时间不详。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三:“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廷玉为康雍间名臣和能臣,“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又是胤禛的恩师张英之子,深受倚信,登基仅两天即令兼内阁学士,协管翰林院。时值众皇子拉帮结伙的特殊时期,谕旨每日数十下,皆出张廷玉之手,以拟稿“悉当圣意”,次月特授礼部尚书。元年八月,张廷玉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历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并一直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由于监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张廷玉与纂修诸臣也曾进入皇史宬检书,“得窥金匮石室之藏,恭纪圣德仁功之盛,荣幸已极”。而那时,《永乐大典》应不在宬内了。
张廷玉记述《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没说原因,也没给出一个具体时间。综合各类记载分析,应在雍正元年七月调整明史馆之际。胤禛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觉罗逢泰为总裁,并采取措施,意图加快《明史》的纂修进度。不知何人提议,存放于皇史宬的《永乐大典》被整体调出,以供编者参考。往事必然如烟,出借与整体迁出过程都有些复杂,也模糊不清。后来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曾传谕追查《永乐大典》的丢失问题,谕曰:
近因访求载籍,以翰林院所贮之《永乐大典》内多有人未经见之书,派员查核,约缺一千余本,较原书少什之一,不知何时散佚?闻此书当时在内阁收存时,即有遗失,似系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未经缴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一)
因为《永乐大典》已有遗失,而乾隆君臣已搞不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便只有捋着线头去找。而“在内阁收存时”的说法,也引发本人极大疑惑,一度以为此书出宬后先进了内阁书库,然后才转存翰林院。经过追索查考,搞清皇史宬隶属内阁的满本房管理,下设守尉三人,则知所谓的“内阁收存”,也就是原存于皇史宬的意思。至于所说“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可能指重开明史馆,也可能为纂修《佩文韵府》《康熙字典》或《大清一统志》,总之是陆续借出了一些。借书不还的例子古今都有,改藏、搬运也难免被窃,《永乐大典》的丢失并不意外。
此书贵重,清代前三朝不断有一些官场读书人谈起,赞扬其文献价值,而着手从中辑集遗书者,全祖望堪称第一人。全祖望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史兼通,著述宏富,动意辑抄《永乐大典》是在雍正十三年,那时的他居住在理学家李绂的宣南之宅,读书紫藤轩。李绂任《八旗通志》《三礼》等馆纂修,将借阅的大典散册带回家中,全祖望翻阅后大为惊喜,即商定从中搜辑失传古籍之事。次年春全祖望得中进士,选入庶常馆深造,翻阅《永乐大典》更为方便,也随之着手抄录。而他的朋友(如小玲珑山馆的马曰琯)闻知此事,立即赶来,极力怂恿他雇佣写手,大加辑抄。这简直就是后来朝廷辑佚的一次预演了,项目主持人是全祖望,李绂很可能充当学术顾问,一部分经费则来源于江南盐商兼藏书家。怎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借出大量书册呢?全祖望来了个公私兼顾,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三礼馆”诸位大佬,得到批准,“令抄大典所有经解”。乾隆元年十二月,李绂兼三礼馆副总裁,辑佚之事应该更方便了。即使如此,辑录进展也是充满艰辛,全祖望曾忆写此事:“夫求储藏于秘府,更番迭易,往复维艰。而吾辈力不能多蓄写官,自从事于是书,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业于此,非易事也。”更觉遗憾的是这套《永乐大典》有不少残缺,全祖望不知听谁讲皇宫中藏有正本,曾想奏明皇上允准借抄,以补足之。
庶吉士通常要在庶常馆读书三年,因弘历登基,次年增加一届恩科,全祖望等要为新选的庶吉士腾地儿,仅一年就结业了。而由于辑佚牵扯了太多精力,祖望在散馆考试中表现不佳,一向以学养自负、渴望留下的他竟然被排在最后一名,不仅要离开翰林院,还要回家等待分配。有人说他是吃了李绂与张廷玉不和的挂落,我倒觉得还在其一头栽进《永乐大典》,如入宝山,一门心思都在辑书上,结果把仕宦之路上至关重要的考试搞砸了。
作为一个襟怀坦荡的大学者,全祖望所作所为并不存自私的目的,留下一篇《抄永乐大典记》,公布其辑佚由来与选择标准:
前侍郎临川李公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因与公定为课,取所流传于世者盖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管大义者亦不录,但抄其所欲见而不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赅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其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
全祖望的学术眼光和格局,其对《永乐大典》的用力之勤和评价之高,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只可惜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乾隆二年九月,全祖望弃官返乡,自此不复出仕,这次由几位志同道合者实施的辑佚,也随之消歇。 全祖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