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弗兰肯斯坦》:寻找跨文化连接
作者:安妮 宇宙混沌。黑暗中,心跳声响起。“怦怦”,一颗不知位于何处的心脏有规律地跳动了几下,接着,耀眼的白光突然亮起,整个舞台清晰地出现在观众眼前。我们看到,舞台中心是一副胚胎状的椭圆形垂直支架,里面悬吊着一个人形生物。“胚胎”表面很粗糙,经过手术缝合的伤疤和输液管交织在一起,看起来像个破碎的培养皿。
宇宙混沌。黑暗中,心跳声响起。“怦怦”,一颗不知位于何处的心脏有规律地跳动了几下,接着,耀眼的白光突然亮起,整个舞台清晰地出现在观众眼前。我们看到,舞台中心是一副胚胎状的椭圆形垂直支架,里面悬吊着一个人形生物。“胚胎”表面很粗糙,经过手术缝合的伤疤和输液管交织在一起,看起来像个破碎的培养皿。
“怦怦”,又陷入黑暗,心跳声充满剧场。白光再次亮起,人形生物从支架上跌落。他的皮肤跟“胚胎”类似,四肢、头皮、背部、胸腔上都有可怖的伤口,尽管伤疤已经结了血痂,鲜血还是隐约从周围渗出来。他的动作非常怪异,看得出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黑暗,心跳,白光,人形生物发出野兽般的怒吼。这样反复几次后,我们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有光。
在英国国家剧院2011年上演的舞台剧《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的开头,编剧尼克·迪尔、导演丹尼·博伊尔和男主角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一起为观众创造了这样一个《创世纪》般的场面。后续的剧情中,人形生物学会了使用身体,他跟一位盲人学习欣赏音乐、说话、阅读书籍,知道了什么是伊甸园。因为外貌丑陋骇人,他不被人类世界接纳。“我是谁?”的疑问驱使他逐步接近关于身世的答案:他是一次科学实验的成果,做实验的是一位名叫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
《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是中国观众颇为熟悉的一出戏码。自NT Live(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进入中国以来,这部作品已经以高清戏剧放映的形式在大银幕上持续播映了10年。今年年初,得知把NT Live引入中国的戏剧制作人李琮洲将制作中文版《弗兰肯斯坦》后,我再次观看了英国版的放映。此刻面对这个故事,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在没有神学传统、也未在19世纪初经历工业革命的中国,我们该如何重述《弗兰肯斯坦》?以创造欲讲述“创世神话”
“我也思考了你提出的问题,中国没有‘创世纪’,而且也很难在东方神话中找到对应的故事。”中文版《弗兰肯斯坦》的导演、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前艺术总监多米尼克·德罗姆古尔(Dominic Dromgoole)认为,“创世纪”是一种隐喻,在今天具有不同的意味,“小说创作的背景并非真正的工业革命,而是前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他觉得,如今人类正在经历一个科学技术和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时间段,科学家们改写着世界的进程。“从这个维度看,小说诞生的年代跟当下有一定的相似性。”
两年前,多米尼克在伦敦曾有过一个排演《弗兰肯斯坦》的机会,用的是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剧本,创作于1823年的《弗兰肯斯坦的命运》。为排演来自小说家生活时代的剧本,多米尼克对原著和作家玛丽·雪莱的生活做了大量研究。
1816年,玛丽·雪莱和她的丈夫,那位著名的诗人雪莱一起到日内瓦度假,同行的还有拜伦等“奇奇怪怪的英国知识分子”。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他们被困在屋子里,围着火炉,只能用说鬼故事来打发时间。
玛丽·雪莱讲的故事是关于热衷于研究再造生命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他频繁地出没于停尸间,不断尝试把各种尸体碎片重新拼凑缝合成新的人体。被创造的人形生物真的获得了生命,以极其狰狞的面目“降临”人间,向把他当成怪物的主人弗兰肯斯坦索要爱、温暖与友谊。因为遭到人类世界的排斥,他逐渐变得野蛮而极端,缔造了一系列诡谲的命案与悬疑事件。
作家将故事写成小说是在1818年,完整标题是《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这个标题彰显着时年18岁的玛丽·雪莱对现代科学的怀疑态度,为全人类的福祉盗取火种并牺牲自己的普罗米修斯,化身为了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反人类“科学怪人”。她对经典形象的重构与颠覆非常成功,现在谈起弗兰肯斯坦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到普罗米修斯了。
多米尼克提醒我注意,小说的创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在一夜间想出了这个故事,并把它讲给了身边的朋友。玛丽·雪莱是如何想出这个故事的?她周围的环境对她有什么影响?她是否知道自己创造了一个寓言?……“越接近她,房子里的火炉就越清晰,我像是看见了一座神秘的孤岛。”
但是,玛丽·雪莱真正完成小说的写作是在两年后。两年里,她几乎一直处在怀孕的状态中,甚至失去了两个孩子。“她在孕育生命的过程里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跟她肚子里的奇妙生物共处,她是不是也在想,是什么造就了世界?孩子降生后能做些什么?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孩子将是创造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未来,这个生命将会踏上怎样的旅途?……”
围绕玛丽·雪莱展开的想象带领多米尼克迈向“创造”这一主题。事实上,小说从第一句话“我出生在日内瓦”起就把读者放置在了人类的立场上,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是绝对的主角。中文版采用的是英国国家剧院版演出剧本,接到工作邀约后,多米尼克与编剧尼克·迪尔进行过漫长的探讨,话题也包括这一版本为什么要调转核心的叙述视角,把观众引向人形生物的立场。
“目睹人形生物诞生、与人类相处、毁灭的过程,观众相当于被放到一个原点,带着强烈的同理心观察他怎么学做人,继而有可能触达小说的核心。”编剧把《弗兰肯斯坦》视作一部理性时代的创世神话,试图揭示“成为人意味着什么”。不过,多米尼克更关心的还是人类的创造欲。
其实玛丽·雪莱在小说中借弗兰肯斯坦的实验抛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做好代替上帝充当造物主角色的准备了吗?我向多米尼克询问了他对此的想法。“人类是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去创造的,没人能阻止这件事。”多米尼克告诉我,他曾见过非洲出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把斧头。那把斧头很漂亮,它不过是个生产工具,却诉说着人们自古以来对创造的欲望和对美的追求。“这不见得是件好事,人类也创造丑陋,比如枪支和炸弹。它们令人憎恶,但我们情不自禁要这么做,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在多米尼克看来,《弗兰肯斯坦》探讨的是人的本性和现代世界的本性,因此才具有超越时代的能力。在中文版的创作中,多米尼克再次调转了叙述视角,让观众重回人类立场,想想“创造意味着什么”。为了强化这样的表达,他将玛丽·雪莱作为一个角色,引入了由她创造的故事当中。
演出开始,人形生物诞生之前,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舞台中心的孕妇玛丽·雪莱。她用笔创造了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科学家又创造了人形生物。多米尼克希望观众有明确的认识:眼前的一切都是经由创作而呈现的,舞台上正在进行的是有关创造新事物的思考。“与其说我是在表达人类的视角,不如说是创造者的视角。”
多米尼克提到,虽然世界始终在高速发展,但科技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似乎比200年前更加莫测。“在那个年代,蒸汽机、早期电器什么的,人们多多少少知道运行的原理。但现在的技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至少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我孩子所处年龄段的人可能多知道一点儿,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觉得,今天的人类总自信地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可真正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只有极少一部分人。
整场演出里,玛丽·雪莱一共出场了三次,都在剧情转折的关键点。她没有台词,只是静静地注视角色们慢慢走向失控。仿佛面对创造物,创造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其发展。“没有什么能对人类的创造欲喊停,人类自己也无能为力。”多米尼克说。
 在《弗兰肯斯坦》演出的后半段,人形生物找到科学家,希望他再为自己创造一个女性人形生物做妻子。有一场戏,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的人形生物向弗兰肯斯坦诉说他对爱情的想象。他自比亚当,期待“和天使般美丽的夏娃一起在花园里散步”。
在《弗兰肯斯坦》演出的后半段,人形生物找到科学家,希望他再为自己创造一个女性人形生物做妻子。有一场戏,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的人形生物向弗兰肯斯坦诉说他对爱情的想象。他自比亚当,期待“和天使般美丽的夏娃一起在花园里散步”。
人形生物描绘的图景让弗兰肯斯坦感到害怕。如果他们繁衍出后代再来对抗人类世界,后果将难以预见。于是,弗兰肯斯坦毁掉了已经完工的女人形生物。之后,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爱的争论。弗兰肯斯坦说:“你知道爱的力量有多强大吗?它没有道理可讲,完全不可理喻!它是混乱的、无常的、动荡的、疯狂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无法控制的!”
因为对爱的幻想被击碎,也因为科学家背叛诺言,人形生物学会了说谎,彻底放弃成为一个好人,走向了自毁。
爱是什么?这是《弗兰肯斯坦》在创造欲之外的另一重主题。
“玛丽·雪莱写作的过程也是孕育生命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部关于爱的作品。”多米尼克说,抵达中国后,他跟很多人聊过与爱有关的话题。怎么思考爱?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我们对家庭的态度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的创作是一次寻找爱的表达方式的旅程,如此看来,任何时候重述这个故事都同样必要。”
人形生物第一次听说“爱”的概念是在森林小屋,通过教他知识的盲人。盲人告诉人形生物,虽然他贫穷,但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让他变成天地万物中最富有的人。“会有人爱你的。”从未体验过爱的人形生物陷入梦境,他在梦中唤醒属于自己的爱侣,感受到了温暖。
要在舞台上表现爱的初遇并不容易,尽管编剧在剧本中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女人形生物翩翩起舞。“他的内心反射着无数个类似的个体,他渴望的是陪伴感,或者说心灵上的慰藉,帮助他对抗孤独和悲伤。”《弗兰肯斯坦》的编舞及形体指导王亚彬提到,在英国版中,舞台上有非常具体的自然意象,比如雨水、青草、火焰,人形生物每一次更熟悉世界都有一定的具体环境做依托。为了更直观地表现他的恐惧和挣扎,甚至有一辆象征工业革命的火车头从舞台纵深处开到观众面前。
中文版没有写实的自然场景。多米尼克说,他们的创作更偏向于展示人形生物如何学习人类的行为而非适应环境。“相比人形生物,剧中的人类角色对一些‘人类行为’反而有错误的想法,两相对比,矛盾所在就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实际上,中文版里有相当多的肢体表演段落。在王亚彬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肢体表演线索是人形生物从感官出发,认识身体的过程。他要在人类的思想世界逐步发现自己使用身体的能力,让身体从不受支配的状态走向秩序,具有控制力。演员的表演并不像是经过严格编排过的舞蹈,也不像事先规定好的戏剧片段,看起来更接近即兴。在王亚彬的想象中,人形生物应该充满力量感,行动迅速而敏捷,有很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她把这样的想象灌注到形体设计上,于是,初次亮相时的人形生物状如野兽,到梦见心中的爱侣时,他已经成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动作也变得更自如、更细腻。
多米尼克希望人形生物的梦境由一段双人舞来呈现,因为爱是一种多维度的感觉。拥抱带来的温度、身体的重量、对视时的心灵沟通……都是爱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唯美的双人舞由一套极简的动作编排而成,用王亚彬的话说,是“几次逐层递进的接触”。当舞台上不再有“人类”,观众的目光也就不再聚焦于人形生物身上的伤疤。世间的一对同类,他们指尖的触碰、步伐的跟随、目光的交融都显示着源自生命本身的对爱的渴望。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对爱的恐惧态度与感情上的自我封闭。人形生物穷其精力,渴求的不过是一个他爱也爱他的同类。弗兰肯斯坦身边有未婚妻、弟弟、家庭,他对感情却异常淡漠。每次未婚妻对他表达爱的时候,他总是仿佛出自本能般地推开她。中文版和英国版一样,保留了双男主不同场次对调饰演弗兰肯斯坦和人形生物的设计。多米尼克认为,虽然两个角色完全不一样,但他们就像镜子的两面,在感情上有诸多相似点。“他们有共同的孤独感,都渴望与人交流、融入社会,只是表达方式截然不同。”
我观看了闫楠和郑云龙互换角色的两场演出。观演体验非常奇妙,科学家和他创造的人形生物似乎彼此享有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剧中人形生物的台词:“你活着,我就活着。你死了,我也必须去死。”
演出结尾,人形生物杀死了科学家的妻子,为了报复科学家毁掉自己的爱侣。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科学家必须毁掉人形生物才能终结一切,人形生物只有活下去才能维持科学家生存的意义。他们追逐月光,来到北极圈。人形生物对他的创造者说:“我想要的只有你的爱,我本来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你。”科学家却说:“每一个爱的机会,都被我远远地抛弃。每一丝人性的温暖,都被我无情地击碎。”
这是一个残酷又极为浪漫的结局。茫茫天宇间,两个互为杀妻仇家的人同时也成为对方存在的凭证。他们往冰雪覆盖的远方走去,在人类世界之外,思索爱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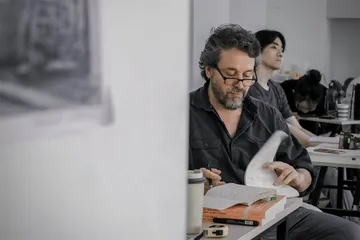 由于玛丽·雪莱原著的人类视角,200多年来,故事中的造物一直被我们习惯性地称作“怪物”。
由于玛丽·雪莱原著的人类视角,200多年来,故事中的造物一直被我们习惯性地称作“怪物”。
“没有人是怪物。”制作人李琮洲借剧中盲人的台词告诉我,他们把剧本里的creature翻译为“人形生物”,因为怪物一词天然的负面意味会影响观众的价值预设。中文剧本译者尚晓蕾也提到,故事中的人类把人形生物称作monster,这是外界的看法,但他自己并不清楚他是谁。“他可能知道自己长得丑,但他不是坏人。我们不希望演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塑造想象中的怪物,自带邪恶,就缺失天真了。”
《弗兰肯斯坦》进剧场之前,我去排练厅看过一次连排。演员们都不带妆,也没换上戏服,每个人都穿着日常训练装,看上去都一样。我问多米尼克:如何找到这部作品与中国观众的连接点?他对我的问题感到忧虑,觉得我欣赏艺术的心态过于紧张。他聊起曾经工作过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那是一家主要做莎剧的剧院,莎士比亚古老的剧作经由当代艺术家的挖掘和重述,如今看来仍鲜活而富有深意。“如果我刻意去追求莎剧跟今天的连接点,可能会让剧作本身的魅力受损,丢掉剧作家原本的一些表达。”多米尼克说,那种感觉就像用锡纸把食材包裹住,为了保鲜而使其无法自由生长,未见得是明智的。
多米尼克是个好奇心非常旺盛的老头,采访时频频问我:“你怎么想?”他表现出强烈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观众口味的兴趣,但在创作中,他还是选择讲一个自己文化语境中的故事。“如果我能做到足够鲜活,观众会自己找到跨文化的连接点。”
实际上,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或者走进剧场再次思考这个故事,无论作品的叙述视角如何变化,我始终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人形生物的立场上,想象自己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未来有哪些让自己走向毁灭的可能性。未知与不确定性对我而言是最吓人的“鬼故事”。多米尼克安慰我说:“欣赏艺术作品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否则你可能都不知道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变化。”
坐在中文版《弗兰肯斯坦》的观众席,我惊讶地发现剧中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他们对爱人善良却驱逐异类,心地好也得不到好报,爱人的方式通常是企图控制人。如此看来,受到人类世界秩序规训的人好像只能努力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尽量不去做一个“怪物”。这样,看不见的人性机器才能持续运行下去。 弗兰肯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