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纪事之动议(8):儒藏说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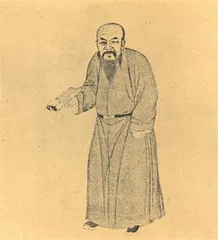 兴修《四库全书》,有一个长期流行、较难理清又无法绕过去的说法,那就是周永年《儒藏说》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自郭伯恭《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开始,直到当下的相关研究著作,几乎众口一词,声称乾隆的开馆修书,乃因受到明末名儒曹学佺尤其是当世学者周永年《儒藏说》的影响。郭伯恭说:
兴修《四库全书》,有一个长期流行、较难理清又无法绕过去的说法,那就是周永年《儒藏说》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自郭伯恭《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开始,直到当下的相关研究著作,几乎众口一词,声称乾隆的开馆修书,乃因受到明末名儒曹学佺尤其是当世学者周永年《儒藏说》的影响。郭伯恭说:
儒藏之说,渊源于明曹学佺,而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亦皆有儒藏之思想,俱未能尽其说。历城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乃援前说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并自筑贷书园,聚书其中,以招来学,复到处宣传,期由近以及远。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于是儒藏之说,由个人而及国家,由理想而成事实,故《四库全书》之成就,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此当时学术思潮之影响《四库全书》者也。
一段话由源及流,似乎言之凿凿,为后来的四库研究者所反复引用,应予梳理和澄清。
先说曹学佺,为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仕至陕西右布政,因得罪权臣罢归。居乡期间,学佺读书写作,感慨“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儒家岂可独无”,遂发奋搜集儒学著作,以经史子集分类编纂。而神州板荡,清军入关,南明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曹学佺倾力辅佐,任礼部尚书,与大学士黄道周一起参决军政大事,后毅然殉节。这样一位仁人志士,政治失意时回归学术,提出编辑大型“儒藏”的规划,乃因处偏远之地,以一己之力,加上时局剧变,流产是必然的,当然也是令人钦敬的。
再说周永年,为山东历城的一个读书种子,乾隆三十六年二甲进士,后参加《四库全书》的编撰,出力甚多。永年的《儒藏说》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节引如下:
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然曹氏虽倡此议,采撷未就。今不揣谫劣,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凡有心目者,其必有感于斯言。丘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而以孔氏之子孙领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于他处。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惟分布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剎,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斯为上策。……
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禀,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欧阳公曰:“凡物非好之而有力,则不能聚。”《儒藏》既立,可以释此憾矣。
有人将周永年称为公共图书馆的创议者,是正确的。周永年提出收集儒家著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广为保存,供天下学子尤其是穷困者研习。这一思路有点儿像武训办义学,是可贵可敬的,也是困难重重、难以付诸实施的,与乾隆兴修《四库全书》之立意主旨却相去甚远。一个是民间行为,要多设收藏借阅之地,为学子提供方便;一个是国家行为,通过全国性的征集、整理、抄补、刊刻,编纂一部旷世大典。差别可不是一点点。
至于周永年在哪一年提出的“儒藏说”、在何时何地兴办的借书园,相关著作多语焉不详,质疑亦集中于此。有人提出在乾隆初年,当时永年还是一个小孩子,显然不可能。张银龙等《周永年“儒藏说”提出时间考兼论其对四库全书纂修之影响》一文反驳甚力,考证出周永年写给李文藻的信在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据此判定“《儒藏说》思想并未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产生什么影响”,并推演此说发生的原因,“起码在民国初,人们即将《儒藏说》思想与四库纂修联系了起来,认为思想提出在前,实践在后,则实践必然是在思想的影响指导之下。这种并无实证的假说,在逻辑上非常具有合理性,也正因此具有极强的欺骗性而畅行无阻”。一些研究者还喜欢强调周永年的庶吉士身份和翰林经历,确实是有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在中进士后,周永年一没有入庶常馆深造,二没有被分入各部院观政,而与邵晋涵都是“归班铨选”,也就是待分配。这个结果最令新科进士沮丧,等待过程往往一拖就是几年,无以为生,多数人只好去做幕友或馆师。由中进士到三十八年闰三月,几乎两年的时间内,周永年居于家乡济南。记载缺略,我们不清楚他回乡后做些什么,靠什么养活一家子人。却也大致可推测他在忙活借书园之事,《儒藏说》的主张,应在此时形成,并在信中向好友讲述。
再具体一点儿,应是在三十七年正月皇上发布征书谕旨、山东巡抚徐绩等遍行晓谕之后,周永年才生发出汇集儒家典籍的念头。结合其在当年初夏写给李文藻的信“有儒藏之说”,我倒认为很可能是受了乾隆征书的启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而细绎其《儒藏说》,怕也很难称得上“思想”,与《四库全书》也扯不上“思想提出在前,实践在后”的逻辑关系,反而更像一个小臣的学习心得与建议。这也正是周永年一入四库全书馆,就闭口不提此说,全神贯注投入辑佚编撰的原因。
研究清史的困难,若说以前多在于史料的匮乏,勾稽不易,如今随着大批档案文献的公布与整理出版,则在于史料的浩如烟海,阅读难周,而个人觉得,更在于人们囿于执念(学者和读者概莫能外),易生误解。不是有一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吗?自有其深刻精警之处,但也提醒我们,追求历史真相可能存在一个思维屏障。譬如当日至高无上的皇帝,如今似乎成了弱势群体,可以被戏说、假说,被嘲谑、批判,较少被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譬如说到编书,就认定只能是读书人的事儿,而皇上只有受到读书人的影响,才会想起去编纂一套大书。本专栏先以一组文章写“书生皇帝”,写弘历的读书与编书,写他对经筵体制的改造、对科举取士的重视,以及对翰詹大考的热衷,意在说明:乾隆帝开馆兴修《四库全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当然会吸纳臣子的意见,会在朝野大量选用读书人充任编纂,却也不必再得到《儒藏说》的啥子启示。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