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诞生100年:诗歌如何向时代发言?
作者:艾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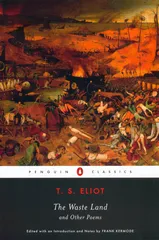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在疫情依然肆虐,管控杳然无期的日子里,人们似乎能在诗人T.S.艾略特100年前问世的长诗《荒原》中,找到某种熟悉的崩坏与幻灭之感。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在疫情依然肆虐,管控杳然无期的日子里,人们似乎能在诗人T.S.艾略特100年前问世的长诗《荒原》中,找到某种熟悉的崩坏与幻灭之感。
《荒原》描述的充满干渴、混乱与空虚的现代世界图景中,充斥着不同的声音与碎片。这首诗中,既有“我很害怕。他说,玛丽,/玛丽,牢牢揪住。我们就往下冲”这样日常的语言,也有“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枝在从/这堆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这样来自《圣经》的语言。与詹姆斯·乔伊斯在1922年同年出版的小说《尤利西斯》中展现的“词语革命”相似,艾略特有意识地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反映无序而复杂的现代文明。
这种碎片感,一直萦绕在当代生活之中,这也让艾略特的《荒原》从诞生之初仅为少数文学艺术界的前卫人士所欣赏,逐渐成为英国诗歌的重要传统,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据2009年英国诗歌节期间BBC发起的一项网络投票显示,莎士比亚之外最受英国人喜爱的诗人中,艾略特排名第一。
《荒原》的构思与最终成形,正是在“一战”之后崩塌的欧洲。1914年2月,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系博士学位的26岁的艾略特,决心像许多美国哲学界领军人物一样去欧洲完成学业。当他刚在德国马尔堡安顿下来,计划参加马尔堡大学在这年七八月份为外国学生开办的暑假班时,战争爆发了。8月,艾略特去到伦敦,后来在牛津大学一直待到1915年6月。
艾略特本已做好屈从一份哲学教职的准备,但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的鼓励将他坚定地推上诗歌道路。二人相识于1914年9月22日,庞德不但带领他进入伦敦的文艺圈子,还四处筹措为他在1917年印刷了第一本诗集。一个成长中的哲学老师,终于转变为诗人艾略特。
出身于美国清教徒家庭的艾略特,此前已在《普鲁弗洛克》《序曲》等诗中,反抗过美国无孔不入的商业思维影响下的情感怠惰与道德朽坏。庞德鼓励他从那些半宗教诗回到《普鲁弗洛克》式社会讽喻诗的路子上来。1915年秋,艾略特开始在战火纷飞的伦敦定居,他先在一所中学担任了一年多时间的校长,后来又在一家银行长期工作。1927年,他入籍英国。
战时的伦敦,给了艾略特观察人性的最好机会。就像英国作家D.H.劳伦斯所描述的那样:“1915年至1916年冬,旧伦敦的精神垮掉了。从某个层面来说,这座城已经死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它死了,成了一切破碎的激情、欲望、希冀与恐惧的漩涡……”
据林德尔·戈登在艾略特传记《不完美的一生》中的研究,《荒原》的写作过程始于长达七年半时间里不断积攒的大量断章。长诗的写作主要集中于1921年,这年10月,艾略特从银行请了三个月病假,一边疗养一边写作,到翌年1月,仍在庞德建议下不断修改。这一创作过程,也是艾略特写作长诗的习惯:“他一般会写下小的片段,之后再将片段相互拼接,而拼接过程中的戏剧性决断则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他自身生活的发展。”
1922年,《荒原》先在艾略特自己创办的《标准》杂志发表,后来又在美国《日晷》杂志发表,引起巨大震动。但是英国批评界对这首诗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它是一篇宣言,揭示了“我们时代的弊端”,而反对者则认为它表现的纯粹是个人的感受,是一种文字游戏。然而,正如彼得·阿克罗伊德在《艾略特传》中所说:“《荒原》成为名作,最初并不是在这些批评家那里,而是在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中。他们认为它显示出了一种现代感受。‘爵士乐’般的节奏、城市与郊区的意象、人类神话学的时髦应用以及引语和戏仿在诗中的出现——所有这一切正像埃德蒙德·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是‘最时兴的巨大轰动’。”
那么,《荒原》这首诗究竟写了什么,它为何会在现代诗歌乃至现代文化史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历史意识与现代心灵的困境
学者陆建德认为,《荒原》首先展示给人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伦敦下层市民的对话、伊丽莎白时期剧作家的声音、但丁的声音、先知的声音,乃至“Twit twit twit/Jug jug jug”等非人的拟声。事实上,《荒原》最初的名字就叫《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报告》(He Do the Police in Different Voices)。
“《荒原》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它的叙事性,这首诗更多借用的是艺术上的拼贴手法。长诗最后面那句‘这些片段我用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可以作为整首诗的一个注解。诸多的噪声,诸多的嘈杂,最后形成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片嘈杂,拼贴出这个时代的一种无序,一种精神的绝望。”艾略特传记译者许小凡说。
然而,这些碎片之所以抓人,还在于艾略特在前人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的诗句中,嵌入当代生活的印象,因而也能共情于读者。许小凡向我谈起最初读到这首诗时的触动:“本科读书的时候,读到第四章中最后一句‘啊你转向船舵朝着风的方向看的/回顾一下弗莱巴斯,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的’,一下就让你与这个遥远古老的腓尼基水手产生联系,他好像不断在叫你,有一种与读者的对话感。在第一章结尾引用波德莱尔那句诗‘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意思说不要觉得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这个虚伪的读者说的就是你。”
艾略特在1919年写作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便谈到诗歌写作中的历史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正是这种植根于整个文学传统的历史意识,让艾略特的引经据典没有沦为掉书袋,而是融入鲜活的当代意识。
《荒原》中现代人心灵的困境,集中呈现为肮脏的、不正常的、兽性的、几乎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两性关系。林德尔·戈登在传记中描述:“《荒原》里充斥着被性或婚姻背叛和摧毁的女人:菲罗美被蒂留斯粗暴地扯掉舌头,说不出受到强暴的经历;勃然大怒的妻子无法与丈夫交流,只能听到哼着‘呵呵呵呵那莎士比亚式小调’忽略她的存在;酒馆里的一个女人过早显得老态,只因为她参战回来的丈夫想‘找点乐子’,让她怀了太多次孩子;打字员对职员毫无欲望却同意和他交合,整件事完成得那么机械,就像她事后往留声机上放了张唱片;在河上平躺的伦敦女人蜷起了膝盖。她让这整件事降临在她身上:‘有什么好怨的呢?’在这里,艾略特将对女人的怨恨化为对她们同样身为城市受害者的悲悯——她们全都没有爱,没有希望。而诗人以其异常的敏锐,以诗的方式聆听她们被迫沉默的声音。”在许小凡看来,《荒原》就是一部“关于爱的失败的百科全书”。
然而,对现代心灵困境的碎片式拼贴,就足以使这首诗成为一个时代的宣言吗?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艾略特如何将那种批评者所认为的“个人感受”转化为支持者所说的“时代经验”。
 在《荒原》诞生之初,一些批评者将其视为一种由个人感受出发的文字游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熟悉艾略特诗歌写作的人,都能从《荒原》中读出那些独属于诗人的生活经验。当他哈佛时期的同学康拉德·艾肯说《荒原》就是艾略特自己的炼狱时,所指正是艾略特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之间充满痛苦与折磨的婚姻关系。据传记描述,薇薇恩是一个经常生病、充满抱怨的有些神经质的妻子,而艾略特在写作《荒原》期间一度精神崩溃,也与永无宁日的家庭危机有直接关系。如果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就不难在长诗第二章《对弈》中辨认出诗人妻子的声音:“今晚上我精神很坏。是的,坏。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
在《荒原》诞生之初,一些批评者将其视为一种由个人感受出发的文字游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熟悉艾略特诗歌写作的人,都能从《荒原》中读出那些独属于诗人的生活经验。当他哈佛时期的同学康拉德·艾肯说《荒原》就是艾略特自己的炼狱时,所指正是艾略特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之间充满痛苦与折磨的婚姻关系。据传记描述,薇薇恩是一个经常生病、充满抱怨的有些神经质的妻子,而艾略特在写作《荒原》期间一度精神崩溃,也与永无宁日的家庭危机有直接关系。如果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就不难在长诗第二章《对弈》中辨认出诗人妻子的声音:“今晚上我精神很坏。是的,坏。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将艾略特个人的幻灭,症候式地看作“一战”之后西方广大青年对一切理想信仰的破灭吗?
陆建德在总结艾略特的早期诗歌创作时便曾说,艾略特具有使个人经验戏剧化的天才——“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化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
对于这种创作方法,艾略特有非常自觉的认识。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沿着浪漫主义诗歌中济慈“诗人无自我”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认为,要获得对于过去的意识,就要不断消灭自己的个性。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化学上催化剂的比喻,将诗人的心灵比作氧气和二氧化硫两种气体发生化合反应生成硫酸时的催化剂:白金丝。在诗歌创作的化合反应中,心灵保持中性,毫无变化。
彼得·阿克罗伊德发现,艾略特“非个人化”的诗学理论受到他在哈佛大学时期的老师欧文·巴比特的影响,将他引向梵文与东方宗教。据说,艾略特在写作《荒原》时一度改信佛教,而“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相比,前者带有更多的非个性化因素”。
在彼得·阿克罗伊德看来,即使在被人们视为来自艾略特糟糕婚姻的直接经验的《荒原》第二章《对弈》中的片段,也贯穿着这种非个人化的戏剧处理。因为艾略特夫妇的感情虽然一直处在一种混乱与困扰之中,但在《荒原》写作期间,艾略特不仅需要薇薇恩与他做伴,还乐于听到她的意见。薇薇恩就曾在《对弈》一段打字稿的边缘写下一个“妙”字。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艾略特和薇薇恩两人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精神困境,意识到了这会给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的后果,于是在此阶段都对以这种可悲的现实中制造出某种戏剧性的场面感兴趣”。
从个人经验到时代经验的转化,除了戏剧化的处理方法,还涉及艾略特对“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另外一个层面,即如何从传统中获取历史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然而,“非个人化”的诗学只是某种理想,一个诗人要做到像蒙田所说的那样“像邻人一样观察自己”,并非易事。至少在写作《荒原》的阶段,艾略特仍然受困于个人意识的“黑暗的胚胎”。艾略特后来对这一诗学理论也有所修正。到上世纪50年代,艾略特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一个诗人可以相信自己不过是表达了私人的经验,他的诗句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种较为隐蔽的谈论自己的方式;然而对于他的读者来说,他所写下的或许恰好表达了他们自身隐秘的感情,宣泄了一代人的欣喜与绝望。”
看起来,《荒原》中那些来自日常经验和文学传统的碎片,让人所产生的炫目的震动,还只是它成功的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正是艾略特那时渴望通过文本书写重构的一种稳定与秩序。就像他在诗的结尾,借渔王的口说:“我是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艾略特试图赋予文学以高度的稳定性与秩序性,对此阿克罗伊德在传记中谈道:“这些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老一辈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威,而年轻一代尚未找到出路。他并不是英国第一个做出这种尝试的人……但艾略特的观点最终被证明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因为他再次证实了文学的价值——既可以成为理解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的途径,又对个人的情感与经验有指导意义。”
(本文写作主要参考赵萝蕤译《荒原——艾略特诗选》,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林德尔·戈登著《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