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是诱人的一座花园
作者:苗千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新书《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中,你提到了生命意识,以及生命面对时间的浩瀚的感受。这其中所谓的“意识”和“感受”,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提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否有什么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新书《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中,你提到了生命意识,以及生命面对时间的浩瀚的感受。这其中所谓的“意识”和“感受”,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提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否有什么联系?
潘向黎:这种生命意识和对时间的感受,是从生命里头自己长出来的,远在我读到《人间词话》之前。
童年的时候,我母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那所中学的校医是一个须发花白的和蔼老头儿,他经常说:“也就刚刚,(我)还是个小孩子呢!”母亲的同事们听了哈哈大笑,觉得他这么老了,居然说自己不久前还是一个小孩子,太好笑了。而我在惊奇的同时觉得这句话有神秘的道理。后来,我自己30岁了,40岁了……有的亲人离去了,朋友、同学英年早逝了,自己有很多白头发了,越来越明白了当年那个老校医的那句话里包含的深沉感慨。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在一个花园洋房里上班,一周去两次,几乎是完美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像大观园里的宝玉一样,突然不自在起来,坐在靠窗的老办公桌前叹气说:“我们这样一天天地过,到底在干什么?”一个前辈同事听了,长叹一声,回答我说:“不为什么,人都要这样过,时间都会过去。这就是人生啊,小姑娘!”
这些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读古诗词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对古人的生命意识、对时间的感慨,特别有共鸣。比如,“谁道闲愁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这种年年来袭的惆怅,至今还会在春天笼罩敏感的人。“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时光不断流逝,朝代兴衰事业成败都是人的事情,大自然是永恒的。
古诗词印证了我的一个认知: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需要人赋予,人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体验,活得充分。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唐诗宋词已经成为了超越时间的经典,我们又该如何挖掘唐诗宋词中所蕴含的现代性?
潘向黎: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时间。凭什么超越时间?凭人性,凭感情,凭见识,凭性灵、文字、音韵的美,凭观察力,凭想象力,凭一切人之为人的体验和滋味。这些很古老,但往往具备了在时间中不为所动的本质的力量。
至于现代性,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艺术作品本身有一种“召唤结构”,随时召唤着接受者参与进去,以再创作的方式接受。在我看来,古诗词对中国读者的“召唤结构”再明显不过,每一首古诗词其实都有巨大空白和不确定性,然后一代一代的读者,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想象力参与进去,最终完成一首首属于自己的诗词。这种好作品的开放性,本来就是一种现代性。读者本身越具有现代性,最终和古人“合作完成”的作品的现代性就越强。
所以,我们在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不要因为总想着“经典”而把它们当成教科书或者没有生命的古董,而要和它亲近,倾听它的呼吸,感觉它的温度和气息,自己也真挚地和它交流,自然而然地投入感情、释放内心,有时候甚至和写这些诗词的人“性命相见”,然后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和自己相通的地方,不知不觉就得到愈疗、滋养,甚至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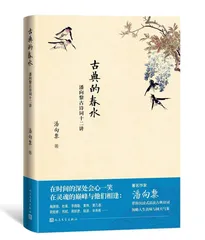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阅读古诗词,除了感受其美感之外,是否可能从中提炼出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指导?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阅读古诗词,除了感受其美感之外,是否可能从中提炼出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指导?
潘向黎:江南的夏天很热,为了消暑,我们可以在读唐诗的时候,留意看看唐代的人如何消暑。有一年我就随手翻找,从储光羲、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人的诗中发现他们度夏的方式:喝茶粥,水亭纳凉,赏景饮酒,清塘泛舟,北窗高卧,山童擂茶,井中浸酒,步月乘凉,铺竹席早睡,入山、习静、食斋……虽然我们现在有了空调和冰箱,但其中很多细节上的趣味和精神性的指向,还是让我们觉得凉爽和愉悦。
在大的方面,我们也能从唐诗宋词中得到重要的参照、唤醒和启迪。比如这阕:“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这是苏轼的《永遇乐》,独自在一个夜里,沉思着历史,感受着时间,慨叹着人生无常。过去都认为这阕词调子非常悲哀低沉凄迷,但我读了很多遍,渐渐读出了其中有限生命对无限时间的叩问。在感叹“古今如梦”的同时,苏东坡也清晰地表明了一种认识:人生代谢不可抗拒,但人和人可以异代同心,因此生命虽然短暂而情怀不灭。这种认识于悲凉中有温暖,是大无奈,也是大通透。
这段时间,因为上海防疫封控,我关在家里超过60天,这种状态对身体、心理、脑力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磨损,我最终在王维和苏东坡那里找到了一些安慰,想必在困境之中,人需要的不是激励和对抗的力量,而是帮助你心灵上挣脱困苦的清旷和超脱。相反,如果遇到了很好的机会,但是感觉自己缺乏自信和奋斗的动能,那就可能适合读盛唐的诗,元气足。还可以读辛弃疾的词,他非常有力量,是个撑天拄地的大英雄,又是一个在大自然中能真正舒展身心的赤子,还是一个深于情、懂得爱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传统诗歌表达的主题看上去比较固定,比如对亲人、爱人的思念,对国家的爱,对时间流逝的感慨,等等。总体来说,这些诗歌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特点?
潘向黎:中国传统诗歌传递给我的,有共同的几个特点,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人对时序和物候的敏感。比如,春天来了,初春,早春,仲春,春残,那种随节令而发生的丰富变化,那种草长莺飞、生机勃勃的美,那种落花满地、绿叶成荫的哀愁,那种时而惊喜时而伤感时而惆怅时而盼望的微妙心情,在诗词里的呈现真是美,令人惊叹而陶醉。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人对生活、对人生的爱,对艺术的爱,经常是和对日常生活的非常细微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普鲁斯特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马德莱娜小点心”的描写,非常细微,非常传神,从感官直通记忆,这一点,中国古诗词里面有很多例子,完全不逊色于普鲁斯特,而文字的消耗量要节省得太多了。
中国人非常重心灵的默契。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遇到天宝年间著名乐师李龟年,其实季节和环境都不错,是春天,是江南。但是,因为这首诗是写“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所以虽然是春天,一定是“落花时节”。这种不假思索的选择“特别中国”,隔多少年读者都很有默契。中国人有一些明确的意象和联想,最初应该是(或主要是)情感选择和审美本能,后来变成了文化符号。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说到传统诗歌的主题,很多诗歌的主题其实也很难说清,有的本来就是不想说清。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商隐,他的无题诗,大部分是很美的糊涂账。就连大家都认为通俗好懂的白居易,也有这样的作品:“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写什么呢?短暂情缘?惊鸿一瞥的美人?飘忽梦境?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猜测,但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也都不能说别人一定不对。
说文化对人的影响,我总是想起王维的《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没有具体形状,无声的,但是空气中到处是,可以沁润人的衣服、头发、全身、灵魂。阅读最好无功利
三联生活周刊:所谓“诗无达诂”。对诗词的理解会融合读者自己当时的心境。相比于之前的《看诗不分明》,你的新书《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中每篇的篇幅更长,其中抒发个人感受的内容也相对更多了。回顾自己之前的解读,“昔我”与“今我”对于古诗词的理解是否会有所不同?在解读诗词的过程中,你希望向读者们传达的不变的元素又是什么?
潘向黎:不变的是我始终真的非常喜欢古诗词,希望和一样喜欢的人没完没了地谈论古诗词,不断交换会心的眼神并深入地切磋。我也希望暂时对古诗词无感的人有一天也能喜欢。每当遇到读者对我说“因为你的书,我觉得古诗词不再是课堂上那么古板乏味的东西了”,或者“这首诗我读过的,现在被你这么一说,突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自己的感受要写那么多?这不是自恋。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如果不面对读者特别坦率地聊聊自己的感受——其实也是借着古诗词袒露内心的角角落落,谈谈对情感、对人生、对生活的各种观察,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呢?我几乎没有必要写,也没有资格写。就是因为“我是我”,一个不是学术立场、学术态度的局外人,这么多年读着古诗词,长大、变老,这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也许有人读了反而更有共鸣;也许有人读了会想:她不是古典专业的,她可以读到这个地步,聊得这么开心,那我也可以。
我写这些书,如果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和古诗词发生感情联系的,古诗词,是如何陪伴一个人的几十年岁月的,那就足够有意思。所以我就特别真切、特别朴素地写自己的感受,怎么相遇,怎么喜欢,怎么不喜欢,是否有误解,怎么困惑的,怎么解开的,年龄变化又带来什么变化,阅历增加之后又带来什么……不装,不藏拙,因为我就是普通人中间的一个,读古诗词的时候,我们是一伙儿的。
真理肯定在学者那里,但我有的是天然的感情。我是兴冲冲地写这些的,我写的时候是真的有触动,有感怀,希望别人知道我这样想,为什么这样想,希望别人和我有共鸣。到了《古典的春水》,因为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见解,我想大胆一点,明确说出来,所以表达上顾忌比较少。当然要尽力避免硬伤,因此各种查证、比对,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另外,到了这个年纪了,我希望比以前两本“阔大”一些。说实话,特别难写,这两年写得又过瘾又累。
我与古诗词相处几十年,有两点感受特别希望告诉朋友们:兴趣是最重要的,不喜欢的东西即使经常读也白读。另外,阅读最好无功利,就是从中寻找乐趣。人生苦短,我经常故意曲解成“人生苦、短”,因为人生确实苦,而且短,如果连阅读都时时刻刻要“有用”,那我们真是可怜。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多次提到你的父亲作为你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对你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于杜甫的热爱也感染到你。那么对于大多数想要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词的普通读者来说,又该如何教育和引导自己走进文学和诗歌的殿堂?
潘向黎:这个不是我写作时的选择,而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只是据实写来。我有这么一个父亲,他并不特别希望我读中文系,并不特别希望我成为作家,他本人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是他很喜欢古诗词,而且他的那种态度和方式告诉了我,读古诗词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我读了中文系,我一直写作,我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要知道我小时候根本看不到任何古诗词的读本,最早的古诗词启蒙读物,是我父亲写在一页一页很粗糙的文稿纸背面的。现在的孩子们有那么多的古诗词读本,而他们的胃口却被学校和教科书给弄坏了,根本不想读,一个字都不想碰。
这里面真的有点命运的感觉。说起来,我这个人是倾向于相信宿命的。如果命运没有做出早早的安排,而一个人又想要阅读和欣赏中国古诗词,那么我建议一定要珍惜自己这个朦胧的兴趣,要真的化作行动。你想想,如果有一座花园,里面繁花似锦,已经经历了千百年而依然盛开,这是多么诱人的一座花园啊。何况古诗词其实更像一枚枚和田玉的“籽料”,被岁月的流水冲刷,被无数人珍爱地抚摸,越来越光润美丽、动人心魄。
同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亲近古诗词有两种比较容易的方法:第一是曲水流觞。对哪一个诗人、哪一个朝代最有兴趣,就从那里入手,然后一不小心又遇到了谁,好像也不错,就再读谁。随意,轻松,不赶进度,不求全。第二是顺藤摸瓜。在哪里遇到一句诗,或者读到半阕词,觉得特别好,或者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就去找出来整首,读一读,如果还觉得有意思,就可以找这位诗人词人的集子来读。作为非专业的读者,我们一般不用读全集,读选集就很好。然后会在注解里遇到其他诗人词人的名句、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学史背景、历朝历代的典故,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瓜”,会引着你遇到越来越多的好诗好词好风景,渐渐地到达“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 潘向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