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的建议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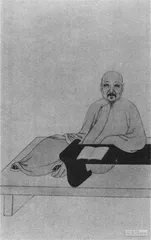 研读清廷的公文,可见存在种种差异:即便是皇上谕旨,使用的措辞和语气、转发的衙门、限定到达的时间也会有不同,而各地督抚几乎个个是人精,能由此选择一种恰当的应对方式。如乾隆历次征书之旨,是礼部以咨文的形式下发的,咨为平行文书,督与抚们未能引起注意也与之相关。10个月后皇上再发催缴之谕,用的是军机处字寄,由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刘统勋签发,各路封疆大吏便有些慌神,赶紧行动起来。
研读清廷的公文,可见存在种种差异:即便是皇上谕旨,使用的措辞和语气、转发的衙门、限定到达的时间也会有不同,而各地督抚几乎个个是人精,能由此选择一种恰当的应对方式。如乾隆历次征书之旨,是礼部以咨文的形式下发的,咨为平行文书,督与抚们未能引起注意也与之相关。10个月后皇上再发催缴之谕,用的是军机处字寄,由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刘统勋签发,各路封疆大吏便有些慌神,赶紧行动起来。
弘历要求访购书籍的两道谕旨,都是发给各省督抚,命他们会同学政办理。这就要说说省级衙门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不设巡抚的直隶与几个将军、办事大臣辖区,其他省份皆在巡抚之上设置总督,通常管理两省军政大事,驻扎某地,因此一些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便权威大减,有些像个催拨儿;而提督学政为钦差之官,有独立衙署,任职三年,不论原衔多低,均与督抚平行,不受其辖制。按理说征书是学政的事,可乾隆深知此事的难度,还是交给各地的军政大员,要求会同学政办理。而实施起来,督抚一般是知会学政一声,具体则交给布政使去操办,皆因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各州府不敢不听。至于学政,整天忙着岁试科试,阅卷量很大,自也不愿多掺和,大多都是做出个积极配合的姿态,而已而已。
但凡事常会有例外,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安徽学政朱筠的做法就显得与众不同。
还是先说安徽巡抚裴宗锡吧。与豫抚何煟有几分相像,裴宗锡也非科举出身,也是花钱捐了个小官,也以通晓吏事、踏实勤勉获得上级认可,一步步走上高位;而不同的,是他属于“官二代”,其父在雍正间做过巡抚、左都御史,乾隆也较早就对他有了好感。接奉军机处字寄,裴宗锡回奏“跪诵之下,不胜惶悚”,然后就叙述自己是怎样布置与催促的,无奈属下八府五州多称“所属并无名人宿望著有成编,无从购送”,呈送到省的只有桐城叶酉《诗经拾遗》《春秋究遗》,绩溪宋代人汪晫纂辑《曾子子思全书》,婺源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合肥知县张佩芳所纂《翰苑集注》等。宗锡说以安徽人文之盛与书肆之多,访求数月,止此数种,显然是属下办理不善,遂亲自动手,查阅史料,将本省历史上的名臣、大儒、理学家等编成名册,注名所著何书,“钞发各府州”。至于本朝著述,则命各地详查方志,顺藤摸瓜,“无论抄本刻本,一并呈送”。安徽属两江总督管辖,宗锡实乃晓事之人,深谙官场规矩,奏称已将收到的图书送交总督衙门,由那里再汇总送往京师。
至于学政朱筠,就有点儿不太晓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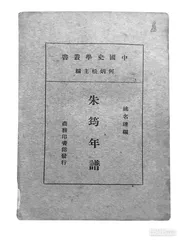 比巡抚裴宗锡提前一天,朱筠单独上奏,而且同时上了两道奏章。一为回应催办之谕,说自己在去冬抵任不久,即接到礼部转发的征书之旨,留心察访,在巡考时“一县一州随处咨询”,并要求教官和诸生提供信息,已经颇有收获——
比巡抚裴宗锡提前一天,朱筠单独上奏,而且同时上了两道奏章。一为回应催办之谕,说自己在去冬抵任不久,即接到礼部转发的征书之旨,留心察访,在巡考时“一县一州随处咨询”,并要求教官和诸生提供信息,已经颇有收获——
其陆续赍到及访闻现有其书可采录者,若安庆则有方以智《通雅》、方中德《古事比》、方中履《古今释疑》,徽州则有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戴震《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宁国则有梅鼎祚《算学全书》、施闰章《愚山集》、吴肃公《街南集》及《阐义》,太平则有徐文靖《竹书统笺》《山河两戒考》,凤阳则有曹楷《闵子年谱》,颍州则有《刘体仁集》,六安则有连斗山《周易辨画》,庐州则有合肥县知县张佩芳《陆贽奏议纂注》诸书,并皆潜心服古,说有依据,足成一家之言,可被甄择。
朱筠显然有些当仁不让,虽也说到“其如何办理章程,开局汇校,一面与抚臣札商,务期搜讨无遗,编次有法,足资广益,仰答勤求”,却完全是以我为主的口气。
回头再看裴宗锡的奏折,真是啪啪打脸啊!朱筠已奏报收获颇丰,并逐一列举作者和书名,老裴还在念叨什么收缴无几,正在想方设法啥啥的——让皇上怎么想呢?巡抚衙门在安庆,而朱筠的学署设在太平,两个人的协调出现了问题,应不在宗锡没有沟通,而在于相距较远,沟通不够,也在于朱筠得旨后自行其是,偏不把这些干货告知巡抚。学政享有单独密奏之权,朱筠人品端正,也不会有意出裴兄的洋相,但瞧不起捐纳出身的官员,认为征书乃学政的管辖范围,不愿意再往安庆绕远道,应是有的。
朱筠的第二折是一份建议书,表示受到皇上“念典勤求,访求遗书不惮再三”的鼓舞,贡献一点个人的想法,一共是四条。因其建议实在与纂修《四库全书》关系重大,文字也不艰涩,今原文照录:
一 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汉唐遗书存者稀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备我朝储蓄之全,则著述有所本矣。
一 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在现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
一 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臣伏思西清东阁所藏,无所不备,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一 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 《集贤书目》《崇文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候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
这样一道奏折,其所底蕴的渊博学识与独到见解,以及对典籍图册的熟稔、对校雠学的精通,大约没有几个巡抚或者学政能写得出,在复奏中属于独一份儿。乾隆一眼就看出其重大价值,朱笔批转枢阁大臣,命集议上奏。
朱筠也算个“生事之臣”。由征书一变而为编书,由扩大内府典藏,升格为编纂一部囊括古今的旷世大典,应该就在于不晓事的朱筠上了篇“生事”的奏折,当然也在于乾隆皇帝具有一双慧眼,并博采众议,形成了新的更完善的方案。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