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武士”奥尔布赖特:“冷战”的记忆迷宫
作者:刘怡 离开政府公职八年以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出版了一本176页的小册子《解读我的胸针:外交官珠宝盒里的故事》,津津乐道地回忆了自己漫长外事活动经历中佩戴的各种首饰以及它们的象征含义。“1993年,就在我刚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管我叫‘那条蛇’(蛇在欧美文化中被视为邪恶和阴谋的化身)。”书中这样写道,“而我恰好收藏了一枚漂亮的蛇形古董胸针。为了表达抗议,每当我要和伊拉克政府打交道时,就会戴上这条‘蛇’。”当参与的国际谈判进展顺利时,奥尔布赖特会戴上有气球、蝴蝶和鲜花图案的胸针;如果进展不顺,则会换成螃蟹和乌龟。俄罗斯总统普京开玩笑说,只要看看奥尔布赖特左边衣领上的胸针图案,就能知道当天会谈的气氛如何。最尴尬的一幕发生在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就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的典礼上——“那天我戴的是一枚沉重的老鹰胸针,而且没别牢。当我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时,都能感到老鹰在微风中颤动。谢天谢地,它最终没有掉下来,否则可太糗了。”
离开政府公职八年以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出版了一本176页的小册子《解读我的胸针:外交官珠宝盒里的故事》,津津乐道地回忆了自己漫长外事活动经历中佩戴的各种首饰以及它们的象征含义。“1993年,就在我刚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管我叫‘那条蛇’(蛇在欧美文化中被视为邪恶和阴谋的化身)。”书中这样写道,“而我恰好收藏了一枚漂亮的蛇形古董胸针。为了表达抗议,每当我要和伊拉克政府打交道时,就会戴上这条‘蛇’。”当参与的国际谈判进展顺利时,奥尔布赖特会戴上有气球、蝴蝶和鲜花图案的胸针;如果进展不顺,则会换成螃蟹和乌龟。俄罗斯总统普京开玩笑说,只要看看奥尔布赖特左边衣领上的胸针图案,就能知道当天会谈的气氛如何。最尴尬的一幕发生在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就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的典礼上——“那天我戴的是一枚沉重的老鹰胸针,而且没别牢。当我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时,都能感到老鹰在微风中颤动。谢天谢地,它最终没有掉下来,否则可太糗了。”
通过具象的胸针宣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不只是一种噱头,它构成奥尔布赖特独特外交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就任国务卿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59岁的奥尔布赖特告诉休斯顿莱斯大学的师生:“在谈论外交政策时,我会尽可能少用抽象的术语,多举一些普通人以及国会两党成员都能听得懂的例子。如果我们的政策在国内都无法得到理解和支持,那它当然更不能指望在国外顺利推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被视为全球秩序主要推动者的岁月里,这种“将外交政策直接带到民众中”(奥尔布赖特语)的姿态无疑充斥着显而易见的乐观情绪,以及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骄傲。实际上,直截了当的作风也被带进了由奥尔布赖特主导的国际谈判中。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麦克法登(Robert D.McFadden)曾经提及,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国务院的几位前同事告诉他,“不同于几乎所有前任,国务卿女士(指奥尔布赖特)在圆桌会议上从不隐瞒自己和对方的政策差异。她会坦率地表明立场,‘我们同意这些,但不能接受那些’,把关键问题向对方点出来”。2000年10月,当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愤然退出在巴黎举行的美以巴三国领导人峰会,离开充当会场的美国驻法大使官邸时,身高仅有1.5米的奥尔布赖特疾步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同时冲着警卫大喊:“关门!我们需要他留在这儿!”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精通七国语言的资深外交家,直到年满六旬时才知晓自己真正的家族史——1997年1月,就在奥尔布赖特宣誓就任国务卿的同一个星期,《华盛顿邮报》根据自己掌握的独立信息源刊登了一则报道,指出新任国务卿的父母其实是捷克犹太人,“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才皈依天主教。而在奥尔布赖特本人的童年记忆里,父母描述的家族史一直是天主教徒版本的。日后她在回忆录《国务卿女士》(2003年)中承认,这一意外发现既是“莫大的惊喜”,也使她不得不再度正视20世纪前半叶欧洲遭遇的空前浩劫与人道主义灾难。在纳粹德国策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中,奥尔布赖特的直系亲属共有26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她的祖父母。这种情感冲击,反过来又强化了奥尔布赖特基于欧洲史经验形成的思维惯性。1999年,她告诉著名记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历史必将重演。”
2022年3月23日,奥尔布赖特的长女安妮通过社交网络对外公布:在罹患癌症数年后,84岁的奥尔布赖特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安详去世。实际上,她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就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夕的2月23日,奥尔布赖特还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短文,回忆自己在2000年初见普京时的印象。四位在世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以及拜登)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奥尔布赖特的悼念,他们在不同时期曾和这位“国务卿女士”有过长期共事的经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Ned Price)在3月第四周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样提到了奥尔布赖特,他表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留在大楼里的影响”。
但奥尔布赖特的身份又不仅仅是一位前政府高官。在接到基辛格(同样是一位欧洲移民背景的国务卿)祝贺自己出任国务卿的电话后,她幽默地表示,“以后这项工作不再是你们兄弟会(fraternity)的天下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身为女性的自豪。在国务卿任内,她频频现身于华盛顿街头,公开回答路人的提问,大大去除了美国公众对高级外交官这一“神秘”职业的不实想象。在2016年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站台时,奥尔布赖特还留下过一句有争议的断言:“对那些不愿互帮互助的女性,地狱会有一个特殊的角落留给她们。”日后她公开道歉说,这并不意味着“女性选民一定要基于性别一致投票给某位特定的候选人”,但“即便时常遭人误解,我仍然不可能忽视女性在现实职场中面对的种种掣肘”。排除这番话里的“作秀”成分,一个率性、固执、充满激情的战斗者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而这,正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留给世人的最直接印象。
 严格来说,当未来的“国务卿女士”于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时,全名还叫作玛丽·雅娜·科尔贝洛娃(Marie Jana Korbelova)。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官,知识渊博,通晓多门外语。然而这些才能在“二战”爆发前夜的欧洲远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家庭——1938年9月,面临德国入侵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到奉行绥靖政策的英法政府的出卖,被迫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出兵“接收”苏台德的德军顺势占领了整个捷克,将其和斯洛伐克变作了两个名存实亡的“保护国”。作为前总统贝奈斯(Edvard Benes)的老部下以及外交部小有名气的犹太裔官员,科贝尔在德国入侵的第一个星期就被列入了占领军的逮捕名单。东躲西藏了十天之后,他决定和妻子安娜以及三个孩子化装逃出布拉格,辗转前往英国避难。在那里,贝奈斯刚刚组建了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委员会”,正需要科贝尔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协助,以取得英法盟国的承认。
严格来说,当未来的“国务卿女士”于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时,全名还叫作玛丽·雅娜·科尔贝洛娃(Marie Jana Korbelova)。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官,知识渊博,通晓多门外语。然而这些才能在“二战”爆发前夜的欧洲远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家庭——1938年9月,面临德国入侵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到奉行绥靖政策的英法政府的出卖,被迫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出兵“接收”苏台德的德军顺势占领了整个捷克,将其和斯洛伐克变作了两个名存实亡的“保护国”。作为前总统贝奈斯(Edvard Benes)的老部下以及外交部小有名气的犹太裔官员,科贝尔在德国入侵的第一个星期就被列入了占领军的逮捕名单。东躲西藏了十天之后,他决定和妻子安娜以及三个孩子化装逃出布拉格,辗转前往英国避难。在那里,贝奈斯刚刚组建了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委员会”,正需要科贝尔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协助,以取得英法盟国的承认。
在伦敦近郊几处租来的公寓里,科贝尔一家度过了五年多的流亡时光。作为贝奈斯的政治顾问,约瑟夫·科贝尔几乎每天都在BBC的捷克语和塞尔维亚语广播频道上发声,呼吁被占领地区的民众与盟军合作,在敌后实施破坏和抵抗。不过在1940年夏天的伦敦,他们首先需要操心的是从德国空军的跨海轰炸下幸存:奥尔布赖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从她记事时起,家里的客厅里就放着一张沉重的大钢桌。每当防空警报声响起,她需要立即带着弟弟妹妹钻到桌子底下,以防整间屋子被炸毁坍塌。或许是担心德军最终会登陆英国、将伦敦也彻底占领,1941年,科贝尔一家决定皈依天主教,并小心翼翼地编造了一部与犹太血统完全“隔离”的家族史,以便在潜在的大屠杀阴影下保护自己的下一代免遭伤害。对此,奥尔布赖特在1997年告诉《纽约时报》:“作为一对勇敢的夫妻,我的父母在当时做出了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而我本人最终因此而幸存。”
1945年10月,在英美两国与苏联达成一致之后,贝奈斯回到了劫后余生的布拉格,再度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领导一个由捷共控制多数席位的新政府。约瑟夫·科贝尔在首都市中心分到了一栋原属德国商人的漂亮公寓,并被升职为驻南斯拉夫大使,带着全家人第二次迁往贝尔格莱德。奥尔布赖特后来开玩笑说,自己最早从事的“外交活动”是身着捷克传统民族服装,在大使馆举办的宴会上向外国官员献花。不过,现实政治的影响到这时为止依旧不曾远离:前流亡政府成员与捷共的合作随时可能破裂,“冷战”的阴影也开始在欧洲上空积聚。为了以防万一,科贝尔将大女儿送到瑞士的一所私立小学就读,并把她的名字从捷克式的“玛丽”改成了法语拼写的“马德琳”(Madeleine)。而危机也果真迅速到来——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件”,多党联合政府宣告解体。同年6月,捷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正式决定加入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并开始清理政府中的不可靠分子。担心自己可能被捕的约瑟夫·科贝尔不愿再回到布拉格,他用尽浑身解数,成功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总部觅得了克什米尔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负责调查印巴分治后出现武力冲突的克什米尔邦争端。马德琳和母亲随后再度踏上跨大西洋之旅,经伦敦前往纽约,最终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落下了脚。
以家庭背景而论,奥尔布赖特属于典型的移民中产阶级子女:定居科罗拉多之后,约瑟夫·科贝尔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开始在丹佛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日后又成为该校国际研究院的创始院长。从1959年到1976年,科贝尔出版了五本关于东欧问题和“冷战”政策的专著,并指导一位未来的国务卿(康多丽扎·赖斯)完成了学士论文。奥尔布赖特本人在定居美国之后,就读的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女子名校威尔斯利学院。然而在她的内心里,童年时代颠沛流离的记忆从未真正远去——在2012年出版的第二本回忆录《布拉格之冬》中,奥尔布赖特详尽地回忆了科贝尔家族从1937年到1948年的遭遇,并且由衷感慨:“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段非常岁月的人都不会对深入骨髓的悲伤感到陌生。”“十年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于欧洲大陆,这一切不应被轻易淡忘。”美国著名国际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曾经评论说,对纳粹大屠杀可能重演的恐惧主导了亨利·基辛格的整个外交生涯;而对奥尔布赖特来说,关于国际政治的第一课便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小国的命运。
 在奥尔布赖特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与她共事过的前白宫幕僚长和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接受了彭博电视台的专访。帕内塔表示,奥尔布赖特是一位典型的“冷战斗士”(Cold War Warrior),“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去探究苏联政权的性质以及莫斯科在世界事务中的目标,马德琳无疑属于其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奥尔布赖特曾经的副手、前美国驻俄大使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R.Pickering)则认为,“尽管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俄罗斯问题,马德琳对苏联政权却不抱多少好感。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她对新的俄罗斯当局也持怀疑态度。这种固执甚至超过了许多一线执行人员”。
在奥尔布赖特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与她共事过的前白宫幕僚长和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接受了彭博电视台的专访。帕内塔表示,奥尔布赖特是一位典型的“冷战斗士”(Cold War Warrior),“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去探究苏联政权的性质以及莫斯科在世界事务中的目标,马德琳无疑属于其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奥尔布赖特曾经的副手、前美国驻俄大使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R.Pickering)则认为,“尽管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俄罗斯问题,马德琳对苏联政权却不抱多少好感。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她对新的俄罗斯当局也持怀疑态度。这种固执甚至超过了许多一线执行人员”。
不过,从学院研究者到“与闻国是”的政策制定者,马德琳同样经历了一系列个人际遇的变化,其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1958年,当她以威尔斯利学院政治学系大三学生的身份在《丹佛邮报》实习时,邂逅了同龄的年轻记者约瑟夫·奥尔布赖特(Joseph Albright)。后者是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创始人艾莉西亚·帕特森的外甥和内定继承人,家族成员在芝加哥与纽约曾经拥有庞大的报业帝国,与东岸政界关系也相当密切。两人在1959年成婚后,一度迁居纽约并全职从事新闻工作。不过到了1962年,马德琳开始在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修读国际政治学硕士课程(未毕业),并系统学习了俄语。1968年,她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法律和政府系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论文主题是研究苏联外交使团。这一时期她的授课教师之一是波兰裔国际关系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是她未来的政坛上司。到了1976年,39岁的奥尔布赖特终于取得新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新生代苏联问题专家之一。
在2003年出版的政坛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中,奥尔布赖特着重提到了她在中年岁月里经历的“三次突破”。第一次是在1972年:当时,与帕特森家族素有私交的民主党资深政治家、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决定出战1972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并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自己的筹款晚宴发起人。尽管马斯基的选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奥尔布赖特自此打开了进入政界的通道,并成为马斯基在国会的首席助理。第二次则是在1977年,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提名奥尔布赖特曾经的老师布热津斯基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后者顺势提携了精明强干的旧相识奥尔布赖特,任命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之间的联络人。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基在当时同样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角色,并在1980年短暂出任过国务卿。他和布热津斯基都有波兰血统,因此奥尔布赖特戏称自己的工作变动是“从一个波兰老板转到了另一个波兰老板门下”。而这两位波兰裔政治家在对苏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同样影响了政坛新秀奥尔布赖特。
 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政治中的蛰伏期:卡特和老布什两位共和党人连续赢得三届大选,声望空前。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在此时迎来了她的“第三次突破”:1982年,她与矢志继续从事新闻业的丈夫约瑟夫·奥尔布赖特分手,开始担任乔治城大学东欧问题研究方向的研究员,并进一步参与民主党高层的政治运作。在1984年和1988年两届失利的大选中,她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和杜卡基斯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日后奥尔布赖特含蓄地批评说,杜卡基斯在选战中游移不定的外交立场反映了“越南战争在那一代美国人中造成的分裂”,而她本人“更多会想到慕尼黑会议,想到主要大国拒绝实施干预时世界可能遭遇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身为民主党人,秉持强硬对苏立场的奥尔布赖特却和“冷战斗士”里根有着更为接近的心态。
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政治中的蛰伏期:卡特和老布什两位共和党人连续赢得三届大选,声望空前。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在此时迎来了她的“第三次突破”:1982年,她与矢志继续从事新闻业的丈夫约瑟夫·奥尔布赖特分手,开始担任乔治城大学东欧问题研究方向的研究员,并进一步参与民主党高层的政治运作。在1984年和1988年两届失利的大选中,她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和杜卡基斯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日后奥尔布赖特含蓄地批评说,杜卡基斯在选战中游移不定的外交立场反映了“越南战争在那一代美国人中造成的分裂”,而她本人“更多会想到慕尼黑会议,想到主要大国拒绝实施干预时世界可能遭遇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身为民主党人,秉持强硬对苏立场的奥尔布赖特却和“冷战斗士”里根有着更为接近的心态。
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的胜利,成为奥尔布赖特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契机。1993年1月,她被新总统提名为“冷战”结束后第二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55岁这一年终于担当起一线外交官的角色。而奥尔布赖特随后就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Ghali)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在1996年直接策划了对加利连任提议的否决,使后者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角逐第二任期失败的联合国秘书长。
按照奥尔布赖特的学术引路人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1997年)一书中的分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可以概括为“三项义务、两大特权”。三项“义务”包括:1.在苏联退出“第一世界”、国际权势分布出现变动的背景下,重新塑造和引导独联体、欧盟、中国、“北约”等重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以“美国优势”(American Primacy)为特征的国际制度。2.在地区层面,预防和遏制局部冲突、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扩散,组织并领导集体维和行动,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3.审视并应对一度被“冷战”压力所遮蔽的地区发展失衡、贸易自由化程度偏低、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等经济和社会弊端,使之与美国领导的开放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两项“特权”则是:在苏联崩塌于萧墙之内、“冷战”宣告结束的历史时刻,美国被公认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和唯一有能力在全球层面塑造经济、安全以及社会议程的领导者。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从海上和空中随时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武力的能力,一切国家在区域安全以及政治议题上的立场,都必须接受美国的认可和塑造,并以美国为中心建构多边框架。
奥尔布赖特在驻联合国大使任内的立场,可以说系统践行了布热津斯基的理念。出于对“美国优势”,尤其是军事力量优势的信心,她一贯主张强硬的“大棒政策”。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奥尔布赖特曾经质问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期力主迅速结束军事行动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上将:“假如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谈论‘卓越的军事力量’,却不能真正使用它,那它的存在有何意义?”1993年10月,当介入索马里局势的美军特种部队遭遇“黑鹰坠落”的惨败,并导致克林顿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后,奥尔布赖特表达了强烈的愤懑之情。随后发生的两起国际冲突,则使这位“女武士”和加利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1994年夏天,卢旺达爆发大规模内战和种族屠杀事件,造成超过50万平民丧生,而联合国未能就是否采取干预达成一致(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本身不愿介入卢旺达局势)。奥尔布赖特据此发起了针对加利的攻讦,指责后者“渎职”“视而不见”。而在波黑内战中,奥尔布赖特竭力促成美国以“北约”名义对塞族武装控制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却谴责联合国应对迟缓、无法阻止冲突规模扩大。一个尚在探索自身新定位的联合国领导人,与固守“美国优势”立场的女大使,已经变得水火难容。
根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A.Clarke)的回忆,1996年夏天,奥尔布赖特把他和另外两位资深外交官召集到纽约,要求他们对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代表进行游说,否决加利获得下一个五年任期的提案。奥尔布赖特本人随后亲自出场,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加利连任,并在11月18日的意向投票中投出了否决票。由于美国代表拥有一票否决权,当安理会召开四次会议仍未能实现妥协后,加利被迫宣布主动退出角逐连任。而在新秘书长人选的提名中,英美两国否决了一切来自法语国家的候选人,最终使得奥尔布赖特本人属意的加纳人科菲·安南(他支持对波黑的空袭行动)脱颖而出。“女武士”的狠辣手腕,至此显露无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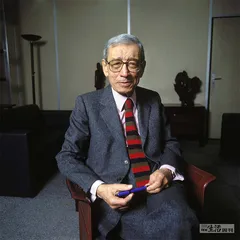 1996年底,埃德蒙·马斯基曾经的副手、71岁的资深外交官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宣布自己由于年事已高,不会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继续担任国务卿。刚刚赢得连任的总统的幕僚班底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以前白宫幕僚长莱昂·帕内塔为首的一派支持锋芒毕露的奥尔布赖特,另一派则支持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佐治亚州资深参议员萨姆·纳恩。最终,由于纳恩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克林顿的预期不合,在民主党内部被称为“自由派鹰派”的奥尔布赖特获得了提名。她也是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担任政府职务最高的女性政治家(由于出生时不具有美国公民权,奥尔布赖特无法参选总统)。
1996年底,埃德蒙·马斯基曾经的副手、71岁的资深外交官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宣布自己由于年事已高,不会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继续担任国务卿。刚刚赢得连任的总统的幕僚班底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以前白宫幕僚长莱昂·帕内塔为首的一派支持锋芒毕露的奥尔布赖特,另一派则支持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佐治亚州资深参议员萨姆·纳恩。最终,由于纳恩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克林顿的预期不合,在民主党内部被称为“自由派鹰派”的奥尔布赖特获得了提名。她也是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担任政府职务最高的女性政治家(由于出生时不具有美国公民权,奥尔布赖特无法参选总统)。
对于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前任克里斯托弗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罗伯特·麦克法登打过一个精准的比方:“沃伦(克里斯托弗)是一位稳健的政策专家,是克林顿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首席辩护律师;而马德琳是一个自己能提出政策的人,她能将克林顿的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的国际事务中。”实际上,就职仅仅两个星期后,奥尔布赖特就让全世界感受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休斯顿发表了那番关于“将外交政策直接带到民众中”的演讲之后,她一口气出访了九个国家,其中既有英、法、德这样的传统盟友,也有与美国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的俄罗斯和中国。在罗马街头,她带着几名随从轻松地散步,笑容可掬,引发媒体热议。面对美国公众,奥尔布赖特高调宣称:“美国对世界不可或缺。我们站得足够高,就得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自负之情溢于言表。
而这种对“美国优势”的自信,很快就被贯彻到了具体的危机应对中。1998年初,伊拉克政府宣布拒绝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官员进入其领土,对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场所进行检查。奥尔布赖特在发出“后果自负”的警告之后,不顾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反对,推动美国海空军在当年12月发动了为期四天的“沙漠之狐”行动,使用大批巡航导弹摧毁了伊拉克境内的多处军事和工业目标。而1999年春天美国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在“北约”框架下实施的针对南斯拉夫联盟的78天大规模空袭行动,更是被观察家直接称为“马德琳的战争”。这场空袭不仅造成大量南联盟平民伤亡,更直接引发了轰炸中国大使馆的重大外交事件,影响极为恶劣。
站在2022年的今天回看历史,我们将会发现:正是在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北约”东扩的方案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埋下了欧亚大陆腹地冲突不断的伏笔。这也是她和布热津斯基主张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的具体落实。相反,在当时方兴未艾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务卿女士”的洞察力就显得较为迟钝了:1998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先后发生了两起针对当地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24人丧生。后来的调查显示,幕后策划者正是后来发动“9·11”袭击的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他们在2000年10月还袭击了停泊在也门水域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科尔号”。而奥尔布赖特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虽然责成当地人员进行了小规模调查,但并未向白宫发出足够分量的警告。未来更大动荡的种子,此时即将破土而出。
不过,尽管奥尔布赖特被视为声名在外的干预主义者,身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本能还是使她坚决反对完全绕开既有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单边主义。2000年10月,奥尔布赖特飞往平壤进行国事访问,成为到那时为止踏上朝鲜领土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在和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她竭力希望就平壤终止核开发以及弹道导弹计划达成一项长期协议,但未能如愿。后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留在牌桌上的那副牌,小布什政府再也没有捡起来。”克林顿政府寄予厚望的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实现长期和平的马拉松式谈判,同样在2000年最终宣告流产。取而代之的是其继任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奥尔布赖特是它们的公开批评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空袭南联盟行动的有机延续。当对武力优势的迷信和四面出击的插手成为常态时,“干预主义”终将变为无视国际制度和全球舆论的彻头彻尾的单边主义。奥尔布赖特助长乃至有力推动了前者,自然也就无法阻止它在共和党保守派的操纵下升格为后者。
2001年1月离开美国国务院之后,一度有传闻称奥尔布赖特可能回到她的出生地布拉格居住,并寻求参与2003年捷克总统大选。但前国务卿女士留在了华盛顿,创办了一家战略咨询公司和一家新兴市场资本管理公司,并继续在乔治城大学兼职授课。作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富于洞见的国际事务评论家,晚年的奥尔布赖特部分修复了自己政治生涯留下的污点。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法西斯主义:一项警告》中,她语重心长地指出:类似特朗普这样的“搅局者”,极有可能导致世界秩序遭受毁灭性破坏。那一刻,“国务卿女士”依然是作为一位美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做出判断,尽管她的出生地远在大西洋对岸的欧洲。 布热津斯基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家族奥尔布赖特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