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时代洪流下,个体的“难”
作者:卡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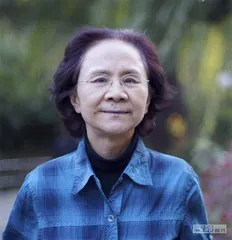 当腾讯影业和导演李路决定将梁晓声的百万字小说《人世间》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找谁来做编剧”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和李路合作过《人民的名义》的周梅森以及好友陈道明不约而同地向他提到了王海鸰。
当腾讯影业和导演李路决定将梁晓声的百万字小说《人世间》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找谁来做编剧”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和李路合作过《人民的名义》的周梅森以及好友陈道明不约而同地向他提到了王海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海鸰编剧的《牵手》《中国式离婚》就有高口碑,可以称为“讲述中国婚姻故事”的影视剧样本。但是,面对像《人世间》这样一个既有长度又有宽度的现实主义作品,王海鸰依然感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王海鸰还是接下了改编。她对这篇小说中的时代很有感情,她和剧中的周秉昆同年出生,她的父母也是周家父母的年纪,剧中所有的时代转变和人物命运发展甚至都可以找到参照系,这些是她接下这部戏的底气。
作为编剧,王海鸰深知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在哪。在情感上,她有着女作家的细腻与敏锐;在人物关系上,她有作为母亲先天的优势;在年龄上,她对剧中人物的命运有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但王海鸰也意识到,要让这个剧本具有史诗性的表达,还需要有一个值得推敲的骨架,所以她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同为编剧的儿子王大鸥。王大鸥写梗概,写时代背景,写人物命运走向,王海鸰则在这个骨架里延展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活细节,这也成为《人世间》被人夸赞最多的“人情味”与“烟火气”,剧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人物对白,她都借用于生活中亲历的细节。
《人世间》里每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流转都带着主动或被动的痕迹,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们往前,“没有好坏,只有立场”。在这一点上,王海鸰告诉我,“我在写每一个人的故事时,都会站在他(她)的立场替他(她)说话,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再到官员、商人,我在写的已经不是人物的‘好坏’,而是时代洪流下每一个个体的‘难’”。
三联生活周刊:梁晓声的原著《人世间》有百万余字,浓缩了中国50年来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且人物众多,改编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读者,是什么打动你?
王海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一直面临着探索、追寻、试错、纠错的过程。40多年听着很长,放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更何况,这是一个近50年体量的小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地方,过去有多么辉煌,如今那里的人就能感受到周围多强烈的萧条和一落千丈,这是根植于东北人心中最大的痛。我就在想,这么苦,这么难,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原著中不仅有大时代的变迁,还有活灵活现的个体命运和人生轨迹。我们的民族素来有对家庭、朋友、婚姻极为传统的理解,这些看似朴实的价值观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吗?这个问题带动着我的思考。“家文化”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这一点极为打动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改编难度在哪儿?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改编难度在哪儿?
王海鸰:梁晓声的原著提供了非常扎实、鲜活和真实的人物基础。刚开始,我和剧组的创作部门以及其他主创开了三次会,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是底色要调亮。我和导演团队之前就达成了一个共识,目前钢铁般金属色的这种沉重文学,一定要调成温暖的、明亮的,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作品。
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没有跟梁晓声做过任何交流,我是有意识地“躲”他。因为一个作者想说的,作品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又搞过影视剧,肯定有很多他的想法。我们开了三次会,在其中的一次会上,他为这个戏设计了一个开头,一听这个开头我就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开头说,一盏煤油灯被点亮,郑娟从夜里爬起来,悄悄为大家做饭,她拿筷子在五香油瓶里蘸了一滴香油。特别真实,这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可是在电视剧里不行,电视艺术需要一个巨大的时代性来展示人物关系,所以剧本里,一出场,周家几口人面临抉择和分离。那次会后,我决定从小说到剧本,一定要保持某种独立性。尤其是我抗干扰能力特别差,我怕我会被带偏,所以只能用一个办法保护自己,就是不再跟梁晓声先生交流。书里说的我都明白,打动我的地方我都知道,需要规避的地方我心里也很清楚,所以谁也不要来干扰我,对原著,我采取了“躲”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关于《人世间》里有血有肉的细节,因为你经历过那个年代,我相信一定是借鉴了个人的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王海鸰: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有年过年我回山东老家,去军区看一些熟人,有一位刚提拔成了政委,还有一位是退休三年的老司令员。我先去看老司令员,那个时候已经9点了,他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人拜年。之后,我又去了新上任的政委家里,长队从院门口一直排出院外,秘书说一个人5分钟。这个剧情,我后来用到了冬梅家。过去,我也经常收到礼物,人家送我礼物都是跟文人交朋友,我曾经收到过一盒冬虫夏草,细看,放得过期了,来不及检查就拿出来送给我。这个经历我也写进了剧本,“送礼”后来成为前20集秉义和冬梅家一个大的戏剧冲突。但近些年来,送礼变少了,以前送的全都是高档礼盒,后来送的就是点家乡土特产了,我从这些小细节上感受到整个国家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从点点滴滴,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剧中你会看到一些很细微之处,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代人的亲历。
 三联生活周刊:在整部剧里有一些关于父母辈和孩子之间冲突的戏,秉义和父亲、秉昆和父亲、冬梅和妈妈、周蓉和玥玥。作为母亲,你是不是对这类情节很有感触?
三联生活周刊:在整部剧里有一些关于父母辈和孩子之间冲突的戏,秉义和父亲、秉昆和父亲、冬梅和妈妈、周蓉和玥玥。作为母亲,你是不是对这类情节很有感触?
王海鸰:这些都是当母亲的体会。我儿子曾经跟我说过,“能让你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后来,我觉得这在中国家庭不是一个个案,这肯定是很多孩子埋藏在心底的一个情感需求。这些台词我加到了秉昆和他父亲这里,“就图让你满意,我拼命去干”,当然肯定有为妻儿的成分,但是在他爸那里争口气的成分是很重的。我对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感受很深。
写作就是写人物关系和逻辑,我照着自己与儿子相处的逻辑来写周家故事,一切就都顺理成章。秉昆和父亲在火车站里争吵,周父对秉昆放了狠话,据说看哭了很多人。写这段戏的时候我并没有动情,但演员演的时候我看哭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擅长的是个体命运的细节,但这个剧还有很多时代叙事需要完成,那么这一部分超出你人生体验的戏是怎么写的?
王海鸰:这个剧本确实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我以前的剧本都是写家庭或是亲身经历,这些对我而言可以说驾轻就熟。但是仅写家庭怕会降低这个剧的分量,也不能反映中国50年。既然小说里具备了一个天然的标志性地区,也就是最辉煌的东北工业基地的落魄,那么在对面也立起一个标志性地区,这样更有利于呈现一个全面的改革的样貌。于是选了深圳的崛起。刚开始写深圳的戏时,虚写,比如骆士宾到了深圳就成了大老板。后来导演团队问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好在我从前写过天津静海大邱庄集团的广播剧,在那里生活过一个月,对企业有感性认识,能挪用的就挪过来;最着急时,走捷径,直接将戏剧规定情境向企业家朋友说明,请朋友来填写人物的相关技术上的对话。骆士宾就这样形成了:开始他是通过走私录音机,倒买倒卖到内地,获得了第一桶金后有了实体工厂,最后转型发展为大集团,这个过程不断在修改完善。还有,官商打交道那段过程我是不熟悉的,这个东西连采访都没地儿采去,谁都会跟你说冠冕堂皇的话,不可能给你讲黑幕。那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官场小说,丁力、周梅森、王跃文的,以间接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剧中,每一个人物角色背后都有他自己性格的缺陷,也有他们和时代命运的冲突,你说谁对谁错呢,其实没有办法去讲得那么清晰。好到秉昆和郑娟这样的人物他们心里也会有困惑。所以在这个戏里你怎么拿捏这种人性真实的分寸感?
王海鸰:我不太喜欢非黑即白。在我的创作理念里,没有绝对的坏人,没有绝对的好人,是人都有他的多面性。我一定要站在这种高度,写到谁的时候我就替谁说话,我自己都在跟自己打架。比方说春燕和于虹打架的时候,我站在春燕的角度,替春燕说话。站在于虹的角度上来想,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怎么能拉下脸面跟郑娟要房?我站在郑娟的角度想,一个房子对老百姓来说可不是小事,但对方已经开了口,如果拒绝这辈子朋友就别做了。所以,于虹开口之前要慎重,郑娟拒绝之前也要慎重。
创作者不能把人物标签化,他是好人就什么事都往他身上堆,跟糊泥巴一样。他是坏人,他就坏得没有逻辑了。我个人觉得乔春燕的变化是有章可循的,她这种人也是我们中间最常见的,其实,她最后的举报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在给自己开脱。春燕说了,“从客观上来说我们等于为党为国家着想铲除贪官,主观上为自己要房”。她也是对的,不是坏到底的人,我是写谁就替谁说话,必须有这个立场,你的剧作才会有力度,否则就会扁平化,人物不立体,观众的共鸣感会差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剧里受到大家最多弹幕抨击的其实是周蓉这个角色,她虽然学习好,也是家里面比较有出息的孩子,为了爱情不管不顾,但是大家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你在写周蓉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剧里受到大家最多弹幕抨击的其实是周蓉这个角色,她虽然学习好,也是家里面比较有出息的孩子,为了爱情不管不顾,但是大家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你在写周蓉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王海鸰:周蓉这个角色其实更接近当下的人,虽然她的人设遭到不少攻击,但是大家觉得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尤其是女性。周蓉不是自私,她是自我。周蓉身上有一种大我。她到了贵州,她关心那个地方。之所以她能让大家引起共鸣可是又被很多人指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给她一个高光时刻,她在贵州教小学生的戏都是叙述性的。周秉义、周秉昆都给了很多戏剧上的高光时刻,而周蓉没有给,其实就差一场戏,这个人物就更出彩了,所以说挺遗憾的。但周蓉很有代表性,有恒久不变的一种人性深处的东西。自我也得两面看,有的时候自我是宝贵优点,比如说,你要不坚持自我,创作就没法进行。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知道东北人本身有属于自己特有的幽默感和表达方式,你是山东人,写这个剧的时候,东北的表达方式你有考虑进去吗?
王海鸰:考虑了,但是我做不到那么方言化。我查了类似于“波棱盖儿”“咋了”“啥”,我都尽量用了,但是没想到,通过二次创作,看了我就想笑。比方说,骆士宾跟秉昆说,30多岁还可以再结婚,郑娟舍不得儿子可以把郑娟也接走,后来雷佳音说了一句“把我也接走呗”,据说这是演员自己加的。这种东北人特有的幽默,不是查点资料、查点方言就能够运用自如的,他们都给做了补充,现场加了一些零碎,这非常好。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编剧能够做到的,真的是一种东北人特有的“小零碎”,当时我就想,要把这个灵感给我,我又能生出一大段戏来。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所有的演员里和你沟通最多的是演郑娟的殷桃?
王海鸰:对,片方为了信息不衰减,让她直接跟我联系,这个很好,我很赞同。我俩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可能都有弱点,离这个角色的生活太远。这种传统、朴素,经历过苦大仇深但依旧乐观积极的女性我们接触得很少。所以,我俩到最后几乎成了商量的状态。比方说有一段戏,殷桃的直觉特别准,“你看我从始至终和大哥没有一次正面交流不真实,我觉得他俩之间得有一段戏”。后来这段戏加了,郑娟对秉义聊起,“秉昆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替他说句话呢,你这么大官”。把郑娟的性格处理得就很饱满,有过怨但也能理解,一下子人物就更加真实可信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发现,剧本是以“年”为坐标串起非常大跨度的戏,这个是故意为之吗?
王海鸰:对,过年对中国人有多重要就不说了,但是北方的年比南方的要热闹,尤其东北,一到过年,外面白雪铺天盖地,家里人从各个地方回来,都聚在屋子里团圆,而且我们这又是一部家庭戏,对一个家庭来讲没有什么比团圆更具有意义了。这个能引起共鸣,让所有的事情在过年时发生更有冲击力。同时,每一年的年夜饭在剧中都有变化,更能形象地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变化。从过去凭票买肉,舍不得吃,有肉吃就行,到吃肉已经稀松平常,到最后大家干脆就是不为吃了,找高档饭店去聚餐,时代性不言而喻。“六小君子”的约定是在初三相聚,很多没有交代的人物在大年初三出现或者不出现,也是时代变化带来了人物变化的最好场景。
(本文图片由片方提供) 文学人世间王海鸰周蓉剧情片三联生活周刊巴基斯坦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