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之家
作者:唐克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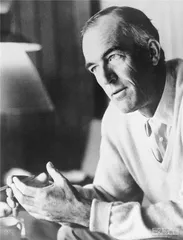 伍重(Jorn Utzon,1918~2008),就是设计了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剧院的那位丹麦建筑师,把他在西班牙马拉加的家安在了大海边。他的家人描述说,他们感觉是住在船上,或者又像置身一座还算舒适的城堡中,因为这里有不受遮蔽的面向自然的视野,一切皆在波动。也有重重厚实的墙壁。后者遮蔽了起居空间上部的视野,好让海面上炫目的反光不至于大量射到人的眼睛里。室内大部分是隐秘的,但你坐下来,在沙发里依然看得见那一片碧蓝色的静海。
伍重(Jorn Utzon,1918~2008),就是设计了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剧院的那位丹麦建筑师,把他在西班牙马拉加的家安在了大海边。他的家人描述说,他们感觉是住在船上,或者又像置身一座还算舒适的城堡中,因为这里有不受遮蔽的面向自然的视野,一切皆在波动。也有重重厚实的墙壁。后者遮蔽了起居空间上部的视野,好让海面上炫目的反光不至于大量射到人的眼睛里。室内大部分是隐秘的,但你坐下来,在沙发里依然看得见那一片碧蓝色的静海。
这两种貌似矛盾的手法结合得颇为成功。虽然,粉黄色的40厘米见方的砂岩在马拉加已经用了上千年,西班牙人并没见过这种富有层次感的住居:富于传统气质的外观,里面却别有新意境,光线的潮汐逐次侵入内部,造就了一种同样随时间变化的景观。这种现代空间甚至受到了当地人的礼赞,他们送给他的书上写着这样的献词:
“献给向我们展示了本地石材的伍重,谢谢您。”
伍重并不是本地人,这,反倒是赞誉之中的亮点。一个北方人,却教给了地中海居民如何使用本地材料。他重视“场所”,看重建筑和风景的关系,但这关系不一定是种俗套:他在有点坡度的端墙上覆盖西班牙瓦(mission tile),还带来新颖的马头墙般的造型,按照伍重自己的说法,这是从中国学来的。1957年,他是少数几个到访过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建筑师之一。他在住宅中置入的烟囱是本地做法,但是他也把不甚安定的因素引入了原本平淡无奇的室内。从昏暗的内室到动荡的海天,设想你是那个坐在幽明转换之间位置的人,时而坐拥城堡,时而感觉在船上,你会体会伍重一直喜欢的东西:
“从茂密的丛林到开阔的平台,情感的转变是如此美妙,就像在斯堪的纳维亚,数周的阴雨连绵和乌云压顶之后,突然间阳光明媚,人们心中豁然开朗,充满喜悦。”
能够这般折腾自己私宅的建筑师自然不是一般人。把悉尼歌剧院项目搞到几度破产的伍重也是如此,他为自己在丹麦和澳洲等地建造了不止一座住宅,都在建筑史上留名。这种“理想之家”其实早已超越了“故居”的概念,因为习惯了把世界各地的文化要素引入自己起居之所的人,绝不会像帕斯卡建议的那样,老老实实待在一个地方。这种自宅,也就是自己为自己设计的理想居所,同时有种“公共建筑”的属性。或者说,即使外人不曾真的频繁来访,当代建筑师其实时刻在意着他和外界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上述那个画面,伍重甚至发明出来一种富有个人特色的空间意象——即使马拉加住宅和此前的歌剧院设计并无相似之处——厚重的屋顶庇荫了个人空间,但是人的高度和视线范围内,内和外的分隔被尽量减省,脚下是坚实的大地,建筑一般认为最核心的柱和墙等于不存在,以他最爱用的折线形屋盖的形式,头顶上的这一部分,仿佛是挪威峡湾里的云朵浮在大地上。
 在建筑画报上不大看见的住宅设计,是有关世界和个体的关系的。即使营造他们个人最亲密的场所,现代建筑师也并不只是待在私人领地的幻境里。选择融入“与有荣焉”的集体乌托邦之中,他所想的,往往也是他人和大众所津津乐道的。
在建筑画报上不大看见的住宅设计,是有关世界和个体的关系的。即使营造他们个人最亲密的场所,现代建筑师也并不只是待在私人领地的幻境里。选择融入“与有荣焉”的集体乌托邦之中,他所想的,往往也是他人和大众所津津乐道的。
比如莱特在芝加哥市大名鼎鼎的橡树公园工作室,是干活的地方也是生活场所。有点旧贵族情怀的莱特在这里养了6个孩子,晚些时候,他以类似的家庭工坊哲学,两度建起了更大的“塔里埃森”(Taliesin),把学徒的个人生活也安置其中,还弄出来一系列狗血的纠纷。又比如约翰逊(Philip Johnson),纽约现代美术馆迄今最知名的建筑策展人,也是操弄建筑名利场的大佬,他在康涅迪格州的新迦南(New Canaan)的“玻璃房子”,虽然只算是一间房,但是约翰逊在此的别业范围可要比玻璃房子大得多,他的“独栋”还得算上外面大得多的庄园,近十座由他构思、工程师和艺术家协力的建筑物。普斯蒂格里奥内(Gennaro Postiglione)准确地指出,建筑师的玻璃“自宅”不免将外界的眼光招惹进来,那些自我意识甚强的强人建筑师,甚至是主动“邀请”了他者的审视。不仅如此,见多识广的伍重们还把这种审视变成了跨越大洲的彼此打量。
那么自宅就不仅是关于“自己”,它注定是跨文化,超越个人和社会边际的。即使正值日美交战,莱特在1943年的自传中也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对日本人居住方式的喜爱:“我终于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国家有着无与伦比的单纯和自然了。这些日本家庭的地板是设计来生活的——睡觉,跪着吃饭,在柔软的垫子上跪着冥想,在上面吹笛或是做爱。”被莱特溢美的日本建筑师也没有闲着,就在战争中,前川国男(1905~1986)依然不可思议地建成了一座高品质的改良和屋,向他潜意识里的和事实上的西方老师们致敬。显而易见,莱特所青睐的“日本性”此时已经混入了清晰可辨的西方影响,一层有着画图桌的房子,不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容器了。审视和自我审视,令当代的建筑师之家既是生活的场所,又灌注了使人焦虑和紧张的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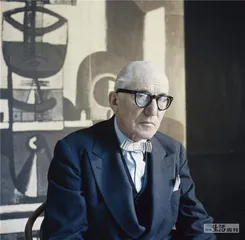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建筑的另一位大师勒·柯布西耶(“柯布”)为自己在地中海边营造的度假小屋就显得有些另类了。虽然一辈子都在为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城市项目而奔走,他晚年位于法国南部马丁角(Cap Martin)的假日小屋却异乎寻常地简陋。1951到1952年间,建筑师每年都到这里度夏,在那他遇见了一位开本地酒吧的朋友,于是借用了酒吧的一堵墙,有了“一座3.66米×3.66米的城堡”。他自诩,为他的妻子设计的这个小屋,是“一个极致舒适和温馨的地方”——同伍重的马拉加住宅一样,挨近去海边的路是柯布看中的一点,“一扇小小的门,一副小小的楼梯,通往葡萄园下的小木屋。仅仅场地就已经很棒了,有着陡峭悬崖的壮丽的海湾”。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建筑的另一位大师勒·柯布西耶(“柯布”)为自己在地中海边营造的度假小屋就显得有些另类了。虽然一辈子都在为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城市项目而奔走,他晚年位于法国南部马丁角(Cap Martin)的假日小屋却异乎寻常地简陋。1951到1952年间,建筑师每年都到这里度夏,在那他遇见了一位开本地酒吧的朋友,于是借用了酒吧的一堵墙,有了“一座3.66米×3.66米的城堡”。他自诩,为他的妻子设计的这个小屋,是“一个极致舒适和温馨的地方”——同伍重的马拉加住宅一样,挨近去海边的路是柯布看中的一点,“一扇小小的门,一副小小的楼梯,通往葡萄园下的小木屋。仅仅场地就已经很棒了,有着陡峭悬崖的壮丽的海湾”。
但那些并不属于他们。小屋的一切都极其“基本”,连淋浴都没有,夫妻俩在其中各睡各的床,柯布的妻子抱怨说,她的头都快挨着厕所了……无关太多“设计”,仅有16平方米不到,入门之后衣橱右边就是按照0.3米×0.3米、0.7米×0.7米的基本尺寸展开的一切:两张床,一张可以收起来的桌子,可以用作凳子的两个木方,圆形的不锈钢洗手池,用天鹅绒帘子围起来的卫生间区域。小屋虽小,还是尽量开了很多的“窗”,西南和东南方向的两扇真正的窗户可以看到海,剩下的“窗”就只有立面上的通风口,还有一些令建筑师得意的画作。没有任何其余的修饰、风格,用以搭建的木料是预制的,略坡的屋顶上铺设当时还没有禁用的石棉,利于屋顶排水、防水。室内却收拾得方方正正,几乎像一个后来出现的“胶囊旅馆”。
这个居所,虽然也是“家”,但是却比柯布自己在巴黎的那个家更鲜明地体现了他简括的空间哲学,它干净利落得像是一部“居住的机器”。相对于他在其他照片中的典型形象,在其中工作的建筑师显得轻松、率意,他真的是“身无长物”——也就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张很多人都熟悉的裸体照片。最终,柯布死在一次在这里的海泳之中。“现代之宅”的前因后果
很显然,一种建筑师营造的是一整个世界,像伍重他们一样,其中不受羁绊的诗意,显然的感性,高标的理想,容易使我们忽视它们现实的和社会的语境。柯布在朋友酒吧旁“凑合盖”的小屋,使我们联想起的则是一个由理念构造的世界:现代之“家”成了某种仅仅基于必要性的“寄居”,剩余的东西要靠各色神话来完成——比如《圣经》中小屋的故事,书念地方的妇人和她的丈夫商议为以利沙“……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王下》4:10)。玄学诗人威廉·布莱克将“在墙上盖一间小楼”解释为借了房间里的后墙立起的一个“神龛”,就像被丢勒等人反复描绘的圣杰罗姆清修的书房一样。柯布类似的姿态,很难不让我们怀疑其中类似的宗教意涵——显然,不仅为大众鼓吹现代,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同样容器的建筑大师,也有圣徒的情怀。
很可能,柯布倚着朋友餐馆建起的假日小屋和书念地方“墙上的”小屋有着类似的原型,只不过是基于一种现代“宗教”。个人的灵修之所压缩在家居日常里,和更大的外部世界相接却无关,马丁角的酒吧、海滩和小屋各行其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就是它不再是完整的,而是被各种不同的功能所分割——据说,史蒂夫·乔布斯在公司里有张异常杂乱的办公桌,在他的屋子里却只放置了一盏落地灯,连高家具都没有。当然,以上这个故事也是“神话”。
不仅为自己建造,也为大多数人设计的居所一定是和“现代”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既是一种技术标准,也是变化了的社会认知。最初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福利居住实验,现在已经是大部分人普遍的安顿之所,把生活意义慢慢寄寓在“安居”上的中国人也正在形成他们对具体化了的“身家”(domesticity)的路径依赖,其中有满足也有缺憾。伍重面朝大海温暖花开的大宅毕竟难以企及,那么他们还得试着从柯布的小屋里往外望去,至少要看到温暖的颜色,自然材料的假象,玻璃框里(现在还有电视机里)的画境,还有那么一点点沙滩的念想。如同本雅明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欧洲人,也是如此走进了商品社会为他们设定的现代性的避难所的——它既是心灵的栖居之处,又是新的囚笼。
在“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视为普通人设计住宅,适逢中国也开始确立西方标准的住宅规范,1949年之后的中国居所,就这样与“现代”不期而遇了。但是我们不太容易感受的是,西方“现代之宅”的前因后果。对于一直习惯于独居的西方人而言,多层集体住宅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罗马的繁荣都市很早就有了类似今天的高层公寓建筑,这些公寓从外观到内里的生活都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大城市,困守在其中一间小屋的租住者有着和当代人近似的“室内生活”。尽管和今天纽约、北京的普通人所能负担得起的住宅相比,罗马标准的花园公寓(Case a Giardino)要大得多,但是没有电梯和卫生间的“顶层生活”在那时要麻烦得多,生活质量也远不能和罗马贵族的庄园相提并论——窗户狭小,面对逼仄街道的蜗居是昏暗的。须知书念小屋靠神赐给的烛台照亮,而柯布的上帝就是他自己,抑或也是不远处的大海(两年后,晚年的柯布才设计了他“再出发”的作品:朗香教堂)。
换句话说,最基本(essential)的建筑内部和人的关系,功能、尺度、空间分割……罗马人就有了,它由柯布这样的时代先锋身体力行而成为新的标准,但尚不适用于每个人,真正的、完整的现代人之家的意义,还有待整个20世纪的建筑师去发明,包括伍重和前川在内。

 对从无到有的中国而言,“现代”的住宅却从一开始就显得光彩熠熠。就在60年前,清华大学的两位建筑系学生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建筑的新形式应该和古代有着很大差异,这是由于古代的建筑是手工业或手工艺的产品,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新技术新材料使得建筑成为与大工业相联系的现代化生产……这时,建筑的性质改变了,人们对自然控制力的巨大改变以及公有制的建立,建筑就有可能首先为了人民的生活服务……现代建筑形式的民族差异比古代要小得多,是社会进化的结果”。——然而,英美各国福利住房建设面积的大规模上涨,换来的却是他们眼中居住标准的降低,“大庇天下寒士”的居住问题首先是个急迫的社会问题,美学还在其次。60年后,我们已经急需打开这种低标准的居住“窗口”,如果不是望向大海,那么还得正视那片同样变幻莫测的人心的海洋。
对从无到有的中国而言,“现代”的住宅却从一开始就显得光彩熠熠。就在60年前,清华大学的两位建筑系学生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建筑的新形式应该和古代有着很大差异,这是由于古代的建筑是手工业或手工艺的产品,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新技术新材料使得建筑成为与大工业相联系的现代化生产……这时,建筑的性质改变了,人们对自然控制力的巨大改变以及公有制的建立,建筑就有可能首先为了人民的生活服务……现代建筑形式的民族差异比古代要小得多,是社会进化的结果”。——然而,英美各国福利住房建设面积的大规模上涨,换来的却是他们眼中居住标准的降低,“大庇天下寒士”的居住问题首先是个急迫的社会问题,美学还在其次。60年后,我们已经急需打开这种低标准的居住“窗口”,如果不是望向大海,那么还得正视那片同样变幻莫测的人心的海洋。
问题是,拥有一间小屋,哪怕,仅仅是拥有它的空间感受,也已经是足够奢侈的。也许,那句关于建筑的名言可以稍作修改了,我们还不算是在世界上诗意地栖居,我们只是在这里悄悄地借住过。 现代建筑伍重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