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稳定“自我”
作者:杨璐 “身边很多人说去上了那个课,魏萌出事儿,我是非常震惊的。每次见面,她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特别灿烂。不过,面对工作肯定是展示好的一面,就像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可能在职场上表现出来。我估计背后,魏萌一定发生了问题。”认识魏萌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身边很多人说去上了那个课,魏萌出事儿,我是非常震惊的。每次见面,她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特别灿烂。不过,面对工作肯定是展示好的一面,就像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可能在职场上表现出来。我估计背后,魏萌一定发生了问题。”认识魏萌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这些年的创业热,投资人群体进入大众视线,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为梦想或者暴富奇迹输送资本,人前风光,但人后,这其实是个工作强度和竞争都很大的职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去上那种课的投资人,相对年轻。投资圈特别像娱乐圈,非常逐利,今年投这个,明年投那个,价值观很不稳定。在这个环境里是很容易迷失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比如去年消费品投资很火,前几个月消费品投资一下子掉下来,很多投资公司里做消费品的投资经理就被排挤掉了,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势利。”认识魏萌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32岁的风险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魏萌在参加里程LEGACY飞跃力工作坊课程时晕倒,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即便是为了在职场更上一层楼,可以去读商学院,为什么要去上这样的课。王丽(化名)在一家巨头企业做管理工作,她因为不太擅长有耐心地与人交流,被领导推荐去上类似的课程。“那堂课大概有40多人,可能5个是男性,40个是女性这么一个比例。教练让大家自我介绍,因为什么样的困惑来学这个课程。女性的困惑大部分是,如何跟孩子相处,如何跟老公相处,如何跟失败的自己相处。男性很多是来考察这门生意,学课拿证书,以后自己也办班。”王丽说。
里程LEGACY飞跃力这样的工作坊,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从美国传播到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又传到中国大陆。李强(化名)上的是跟魏萌同样体系的课程,他说:“这个课程设计了很多互动和充满仪式感的练习,比如两个学员要面对面,互相倾诉、互相指责,互相表达信任或者不信任;比如大家都闭上眼睛,有一些配乐,做一些表演性的活动等等。我不太能进入。”
李强是娱乐圈资深经纪人,名利场上风里来雨里去,很快拆解了这个门道。他说:“我干这行那么多年,只要仪式感一来,我忍不住就开始想配乐怎么样,灯光怎么样,老师的语调怎么样。比如说,它当中很多训练类似于禅宗里的棒喝,不觉悟的时候用一种超强力,棍子打一下或者大喊一声,让你觉醒开悟。这个课程里,就是两个人对着大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行,我觉得太吵了。”
李强是陪着太太去上这个课程的,当时太太刚转行。“在新行业里扑腾一年多,有很多受挫的时刻。她比较迷茫,需要一些心理支撑。对我来讲,我们俩能一起做的事情太少了,陪她去完成这件事是很好的。”李强说课程里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第一节课有很多人迟到,老师就让迟到的学员挨个回答,为什么你的承诺这么容易被打破。他抓住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让人去思考。我觉得还是有点儿东西的。”这个课程不能录音录像,他下课后还把课上受触动的金句记了下来。但是,以李强的阅历,他清楚地知道,人生是不能靠金句支撑的,三个晚上、两个白天的速成培训不可能探索清楚。“课程的销售说,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能量比这个阶段大得多,但我评估了一下,整体来讲收获没有那么大。我和太太就没继续上了。”李强说。
李强比太太大十几岁,他觉得30多岁这个阶段确实会有探索自我的需求,他自己也是在差不多的年纪开始认真跟自己对话的。“可能大多数人开始寻找自我,都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和压力。你会不知不觉走到那个点,你会问,这是周遭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怎么回事?”李强说。三十几岁的年纪,在职场上有了一些成绩和阅历,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很多的选择,可能就会迷茫。“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有超长青春期,没想过什么规划,买张唱片就能很开心。但那个阶段突然感觉人生被捆绑了,好像无法施展,对生活状态也产生了疑问。当时茫然和压力大到让我喘不上气来。”李强说。
李强自己找不到答案,就去找生活态度坚定的人聊一聊。“我有个中学师兄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去他家里找他,希望能够解开心中的疑问。几年没见,他成了佛教徒,听完我的问题,他给我讲了一些基础道理,甚至都不算佛教的。然后,他介绍我看一些书,也是普世道理那种。”李强说,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自己。“贪、嗔、痴、慢、疑,可能是东西方都要面对的难题,因为西方类似的有七宗罪,人的很多内心冲突可能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照镜子一样,我知道了身上有哪些问题,修正了一些想法,希望改变。这时候特别难。”
李强花了10年时间,算是跟自己阶段性和解。“我觉得再往前走就是宗教了,跟我的世界观不太一致。我需要的不是解脱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本性驱使我去做事情,找到了方向感。”李强在楼顶上布置出一个花园,北京风沙大,花园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里像他心灵的秘密空间,焦虑、疲惫难以为继时,给他安稳感。亭子里面摆着茶几,放着他的各种“玩具”,他就在这里喝茶,跟自己对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看,自我迷茫很常见,探索自我和改变自我需要漫长的时间。每个走过“心路”的人都有各自的方法。
 冯驌是家居家装消费决策平台“好好住”的创始人,他开始创业时正逢创业潮,咖啡馆里全是谈融资的人,每个人都在兴奋地描绘宏伟的商业版图。潮起潮落,创业九死一生,并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逐渐安静下来,冯驌却带领“好好住”走过了6年时间,成为这个领域最头部的平台。有这样的成绩,他背地里绕过了很多的暗礁,甚至走过弯路。冯驌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我必须看清所有的现实,来找我的合作方、投资人的诉求是什么,我做的这家公司问题在哪里,我自己到底是谁,擅长什么,能力缺陷又是什么?要想看清楚这些,我要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外界想要什么,现在需要什么?在几者之间权衡,找方向和调整节奏,心理活动非常复杂。但是,我看清了这些,就是成长。”
冯驌是家居家装消费决策平台“好好住”的创始人,他开始创业时正逢创业潮,咖啡馆里全是谈融资的人,每个人都在兴奋地描绘宏伟的商业版图。潮起潮落,创业九死一生,并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逐渐安静下来,冯驌却带领“好好住”走过了6年时间,成为这个领域最头部的平台。有这样的成绩,他背地里绕过了很多的暗礁,甚至走过弯路。冯驌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我必须看清所有的现实,来找我的合作方、投资人的诉求是什么,我做的这家公司问题在哪里,我自己到底是谁,擅长什么,能力缺陷又是什么?要想看清楚这些,我要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外界想要什么,现在需要什么?在几者之间权衡,找方向和调整节奏,心理活动非常复杂。但是,我看清了这些,就是成长。”
有人会觉得开公司做决策是一个商业问题,其实电光石火之间是要清楚自我。拿投资的创业者,有人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生意机会,有人是因为喜欢做一件事,两种起点都会在日后遇到挑战。冯驌说:“创业走到一定程度,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选择。起点如果是生意,困难不能消解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接下来动作可能就会扭曲,就只会为了公司估值高、为了公司上市去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起点如果是兴趣则一定会走到选择的路口,要把生意加到自己的兴趣里。我见过很多人没办法完成过渡。天使轮、A轮,大家都讲梦想,拱到B轮,投资人要求你开始挣钱了,这时候很多创业者就崩溃了,他们会认为商业影响自己的兴趣。”
冯驌是兼顾兴趣和生意的创业者,在创立“好好住”之前,他已经是家居生活方式领域的KOL,创业之后,他也想清楚了兴趣之外,这份事业的价值所在。他本来就是同龄人里经历丰富、有主见的人,还时常把自我探索的感悟与人分享。自我探索和主见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说:“我爸妈都是特立独行的人。我爸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可以放弃世俗看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我爸做书,我姑姑为他鸣不平,因为他拿小头,书商拿大头赚了很多钱。我爸觉得只要这本书是他想做的,拿多少都无所谓,书商挣钱多是书商的事。我妈的特点是理智,能够自己跟自己妥协。有些人总给自己找借口,认为自己不走运,其实应该承认是自己没做好。我妈就是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人,所以她遇到问题心态不会歪。”
冯驌被两个特立独行的人教育,要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父母也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跟主流认同感不一致。“我读小学的时候,早上不想上学,我爸跟我有了约定,每个月可以有一两次,他帮我请假,然后我想干吗就干吗。”冯驌说。读到大二,他就跑去上海工作了。“我当时特别喜欢《城市画报》,给报社发了无数邮件,还打电话,终于拿到实习机会。班主任知道管不了我,有时候让同学联系我,让我回学校一趟,有个检查需要配合一下。我挂过很多科,可能对很多学生来讲就会慌张,我却觉得在社会上被认可带来的安全感,比在学校里被认可的安全感要大。”冯驌说。
冯驌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补考才拿到了毕业证。“我姑姑知道这件事后,想着能不能帮我找老师说一说。我妈的态度是,行,反正你要是没拿到毕业证,以后找不着工作或者去不了你想去的公司,自己承担后果。她就不再管了。”这也是母子俩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冯驌的妈妈给他足够的自由,只要身体健康,学习怎么样、做什么工作、有没有钱一概不焦虑。“我妈给我自由的另一面,就是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这个过程我也痛苦过,我遇到困难时去跟我妈说,她理性客观地分析,分析到最后,结论是我活该。我已经这么痛苦了,你都不安慰我。我是不是你亲儿子啊?后来,我豁然开朗了,我妈的分析都是事实,是我必须对自己做的正确认知。”冯驌说。
 即便现在,冯驌依旧把家人作为倾诉对象。“我妈是做记者的,她虽然不会做生意,但她做了两件非常关键的事。第一个是问问题。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在旁边提问。我妈很客观,她能问出非常好的问题帮助我去探索内心,把一件事想清楚。第二个是记者见过的事情太多了,她会给我讲她从前遇到的采访对象的事情,能给我启发。倾诉对象其实是要有选择的,如果找一个情绪垃圾桶,可能反而会有副作用。”
即便现在,冯驌依旧把家人作为倾诉对象。“我妈是做记者的,她虽然不会做生意,但她做了两件非常关键的事。第一个是问问题。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在旁边提问。我妈很客观,她能问出非常好的问题帮助我去探索内心,把一件事想清楚。第二个是记者见过的事情太多了,她会给我讲她从前遇到的采访对象的事情,能给我启发。倾诉对象其实是要有选择的,如果找一个情绪垃圾桶,可能反而会有副作用。”
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探索中,冯驌发生了转变。他说:“我从完全追求自我变成追求全局,开始站在投资人、行业和社会的角度去想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要的东西变得要么很微观,就是把具体的事情做好,要么非常宏观,希望能推动一些改变,比如让普通人请得起专业设计师,让好的设计师可以成立个人工作室等等。假设很多年后,回顾中国家居行业的发展,不知道我是谁没关系,但我们做的事情是发挥过作用的。我这么想问题之后,公司的方向和取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冯驌的心态稳定性也变高了。“我妈一直跟我讲,要我活得平静一些。我这三年时间,理解了这件事情。我没有自我怀疑了,遇到困难,我知道这是我不够好或者不擅长的,那么这些困难就该遇到。事情做得好,我也不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知道自己要什么
冯驌当了6年的老板,对“自我”的认知也多了一个维度——旁观员工。他说:“公司现在招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看候选人,特别是骨干型候选人时,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的稳定性就很差,工作上遇到不顺或者困难,马上就情绪崩溃撂挑子,马上就把所有问题推到公司、同事身上。”
职场上的不顺利,表面上是业务能力的问题,根源在于“自我”。“能力有问题就需要成长,这时候老板要面对两种员工:第一种,他认定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想成长;第二种更可怕,他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在,只想逃避。业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提高,但一个人能在职场上走多远,核心是人的问题。”冯驌说。
冯驌也关注离职同事的动向,自我认定清晰的和不清晰的发展迥异。他说:“有几个前同事是人才,我们觉得很可惜。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有几个人创业了,还成了我的客户。”在冯驌看来,很多人在用错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人生坐标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或者是依附在主流价值观上的。人需要向内去探索。”
“知道自己要什么”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答案的。于峰(化名)很喜欢谈这些形而上的话题,他发现如果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的人,聊起来特别累。“他们绝大多数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答案,环球旅行啊、财富自由啊,你跟他解释这些奇怪的东西可能是欲望,然后再问他们到底什么东西对你的幸福感最重要,他可能还是告诉你,环球旅行、财富自由这些。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想清楚,会明白人生幸福大概率追求的不是钱。”于峰说。
于峰是朋友们认为心态稳定、分析问题理智的那种人。他高中时拿过奥赛的名次,本来是考清华的选手,因为考试失利去了哈工大,学的是现在所谓的“天坑专业”。于峰说:“我在学校实验室里做的是芯片加工设备那类东西,2007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单位能接收我这样的毕业生,本质上它还是与普通机械专业毕业生类似的工作。”那时候,互联网公司已经兴起,以于峰的聪明,转行不算困难。“我妈总给我举例子说,她朋友的小孩连大学都没上,上了几个月培训班,来北京工作收入都比我高。”于峰说。
于峰还是选择了跟机械电子相关的行业。“一路走下来虽然有点坎坷,但多少是按照自己想要的路径去发展的。”于峰当初面临的问题,其实是现在大学生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哪个专业赚钱多”,在他们看来,除了金融、互联网公司和公务员,其他都是“坑”。于峰却没有这种焦虑,更没有躺平。“走入社会马上就发现不同行业收入差异巨大,但我知道互联网公司做的那些不是我的兴趣点,我对如何把东西做出来更感兴趣。我想清楚了自己的人生要什么和干什么之后,就没有困扰了。”
想清楚其实花了很长时间,不仅关于自己的兴趣,也关于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幸福感跟什么相关。于峰念本科的时候就开始问自己相关的问题。“当时同学间有个小讨论,你愿意做一个学识渊博但不太会跟人交流也没什么朋友的人,还是一个有很多朋友但学识不渊博的人?哈工大是名校,周围同学都是渴求知识的人才。结果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有很多朋友。我经常回味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人会觉得情感联结更重要。”于峰说。
研究生毕业后,于峰的感情不顺利,又来到北京工作,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他说:“那时候每天都在找活下去的意义,当时也想不清楚意义是什么,但又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很美好,还有非常多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得要狠狠地去体会一下。北京的活动多,我变得很活跃。”
在书友会上,书友们讨论起“如果衣食无忧,你愿意去做什么?”,于峰说:“这个事情我后来思考了很长时间,仔细追寻了一下内心,拐了很大的弯。我的想法是,我就全投入到做机器人、做航天工程这样的事业里去。突然间,我就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是2010年的事情,从那之后,我就不动摇了。”十几年来,社会上财富爆发的故事此起彼伏,于峰对这些很淡定。他说:“本质上,这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衣食无忧了,你愿意去做什么?对我来讲,还是每天上班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人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调整好,遇到外在的变化才能正确应对。”
 王丽站在那个课堂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上的课程并不像魏萌上的那样去设计一些引发负面情绪的互动,可里面依然有触动情绪的部分。“课上不会让学员把痛苦讲出来,但是会让你在脑海里按照公式把痛苦分析出来,再进行两人对话。搭档要引导对方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真的就是看到参加课程的妈妈们一边哭一边说。”王丽说。
王丽站在那个课堂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上的课程并不像魏萌上的那样去设计一些引发负面情绪的互动,可里面依然有触动情绪的部分。“课上不会让学员把痛苦讲出来,但是会让你在脑海里按照公式把痛苦分析出来,再进行两人对话。搭档要引导对方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真的就是看到参加课程的妈妈们一边哭一边说。”王丽说。
王丽沉浸不了课程。她今年40岁,没结婚,也没孩子,做到这家巨头公司的管理岗位,收入令人羡慕。如果课堂上这种丈夫和孩子的问题代表了现在很多女性的烦恼,她是没有这些体验的。“这个时候我只能带入工作。比如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一名棘手的员工。我配合老师去带入一些问题,尝试公式,但确实收获不大。我觉得在这个课程里,第一我收获了多元的人生,看到那么多人的状态,第二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发现女人的痛苦很多来自家庭。”王丽说。
王丽大概四五年前想清楚了不生小孩。“我就问自己,如果不要小孩,结婚是不是有必要?”她因为没有进入婚姻,感受不到职场对已婚女性的压力。“我有个同事,特别拼,刚生完孩子一个月就回来工作了。公司其实没有要求她回来,但她的确在非常关键的阶段,可能她自己也不想错过。孩子再大一点儿的女同事,在我们公司如果能有一定的职位,都算半个女强人了。女强人的结果就是肯定有其他人在付出,要么是老人,要么是老公。”
王丽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收获成就感和升职加薪。“我能保持单身状态,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底气是我脱离了被炒鱿鱼的情况,没有35岁焦虑,我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她也不认为有家庭、有孩子,再有事业才是完整的人生。“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套路。我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是修炼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克服它们,再继续往前走。这个修炼,我在职场上足够丰富了,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去做一件事,可能会很累,就为了跟大家一样?”王丽说。
如果跟大家生活得不一样,就要承受其他人好奇的眼光。王丽说:“工作场合,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不太会讲私事。特别熟悉的朋友很了解我,不会有疑问。我也不是不近人情,朋友们遇到家庭或孩子问题,我都积极参与讨论。别人的看法对我来讲不重要。”
王丽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她可能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非常清楚什么事情是不要的。“从小我的原则性就很强,可能跟家庭有关系。我是独生女,父母很开明,只管底线其他的不管。所以,一路以来,我考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第一次发现人与人的这种区别,是我有个同学不知道自己要考什么。她学习那么好,却比我迷茫多了。这还不是个案,很多人是上学我就好好上学,下一步干什么就没有概念了。”王丽说。
王丽当时读的是自己朦朦胧胧喜欢的专业。“我那个专业当时只有四个学校有,选择不多的,而且这四所学校分数线都不低。我没有瞻前顾后的纠结,当时我问过我爸,考砸了怎么办?他说没上一本就找个二本上呗。他们没有给我压力,我就很放松了。我这个人从小就缺根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外界什么情况不太会去顾及。”王丽说。
有意识地探索自我是在工作以后。上班的第三个月,王丽经历了第一个重要转折。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阳朔,早上10点多起来之后进了唯一开门的咖啡馆。我在咖啡馆里看了一本书《牧羊人的奇幻之旅》,整本书读下来,我受到的启发是,如果有梦想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它的阻碍,否则就代表你其实并不真的想要。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总要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不是我在做的东西。这本书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我觉得现在拥有的东西都不重要,我的下一个想要拥有的东西更重要,所以,我不怕失去。我后来的经历里,没有被沉没成本绑架的纠结。”
第二次重要的影响也来自读书的感悟。当时王丽正在心情的低谷期,非常痛苦,她看到《圣经》里的一段话后走了出来。“我不信仰宗教,但发现当人比较迷茫的时候,它总有一些金句能够点醒你。触动我的那句话大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痛苦到最低点了,觉得再也爬不上去的时候,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你已经到了谷底,是不是代表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我一下子心里就舒服了,明天一定会比现在好。”这两件事在王丽看来是相关的,她意识到无论是人生还是职场问题,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比依靠外界或者其他人更重要。
来到现在这家公司,王丽的事业发展得很好,老板也看重她,但她却长成了一个不太懂人情世故的骨干。“我小时候就带着这种性格,觉得我把工作做好了,怎么还有其他要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很幼稚的。”王丽的第三次感悟是通过网络小说想通的,那本书讲的是一位现代女性穿越到古代在后宅里生存的故事。“我明白了,直到自己有了足够的影响力的时候,再用自己的规则去影响他们。”
王丽觉得这在现实中是适用的:“这件事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我虽然还是坚持自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但我不再抗拒去做一些妥协。我会注意一些从前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值得去关注的事情。”
 跟王丽一样,张艳(化名)也是大公司里的职场女性,她负责的项目深受市场关注。张艳没有这个位置的管理者身上常见的紧张感,她不慌不忙,更不“打鸡血”。“我有一个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可能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事情,我并不一定也跟着去争取。在一些大的选择上,我属于那种不焦虑的人,因为我清楚幸福或者安稳的方向是什么。”
跟王丽一样,张艳(化名)也是大公司里的职场女性,她负责的项目深受市场关注。张艳没有这个位置的管理者身上常见的紧张感,她不慌不忙,更不“打鸡血”。“我有一个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可能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事情,我并不一定也跟着去争取。在一些大的选择上,我属于那种不焦虑的人,因为我清楚幸福或者安稳的方向是什么。”
张艳讲话温柔又从容,却能坚定地做出让人震惊的事儿。她是卖了北京的房子、车和车牌,裸辞工作,又把全家人的户口从北京迁到杭州定居的。当初去北京是为了爱情,老公在北京考上了公务员,张艳也顺利地找到了专业对口、解决北京户口且收入不低的工作。北京当时的房价不高,车牌也不用摇号,夫妻俩很快就过上了称心的生活。“我们的房贷很轻松,老公工作比较好,我也站在时代的前沿,家庭状态是安稳的。但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大城市安家有很强的获得感,这对我却没有吸引力。北京太大,我太渺小了。我和老公都是浙江人,未来父母不希望孩子离得很远。”
张艳现在的生活不错,可她主动舍弃的那些北京资源日益稀缺,损失也不小。她不后悔。类似的选择还有教育上的,考验一个中年人是否有坚定的自我,教育确实是一块试金石。“我试图去理解教育上的焦虑,因为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儿,所以我怀疑自己错过了一些信息,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蒙眼狂奔。”张艳说。
分析的结果是,张艳觉得对教育心态的差异是生活的态度差异,背后是价值观。“回到内心坚定这一点,我不渴望外人眼中那种成功的目标。所以,我希望孩子在杭州有一个普通的工作,生活幸福就可以了。目前我的家庭状况不需要通过孩子的高考去改变命运。终极目标想清楚后,现在很多引发焦虑的事情都是些非常短期的东西。”
终极目标虽然很清晰,可教育涉及每天的具体决策,焦虑又带有传染性,对此张艳不断回溯自己的成长,分析自己的学习之路,定力很强。很多家长一想到学习好,就要报补课班,仿佛补课班的数量、补课时长跟成绩成正比。“双减”之后,这部分家长更加焦虑,孩子更累。张艳说:“周末不能补课了,家长就挪到平时。放学到家5点多,补课班6点上课,孩子们就匆匆在路上吃个汉堡或者什么的。补课班回来还要写学校留的作业,11点前都睡不了觉。我的孩子没有补课,数学附加题都是超纲的,没学奥数就做不出来。我觉得孩子好好吃饭和睡觉,比上培训班重要。”
张艳学习很好,上的重点高中名列前茅,大学和研究生读的也是一流大学,对学习很有经验。她说:“学习要以学校为主,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踏踏实实把学校里教的东西消化好,打好基础更重要。学习之外,得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哪怕是看电视。家长不能把所有时间都规划得满满的,不给孩子留弹性。我是独生子女,没有伙伴,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暑假吃着冰棍看电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回忆童年,就是在刷题。”
家长们最流行的那种超前学的内卷,她不为所动,甚至反感。她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是好奇心和兴趣。如果假期把新课程都学了一遍,开学上课就没有好奇心了,那么可能就没有动力认真听老师讲课了。补课班囫囵吞枣把科目赶着讲一遍,上课时又没有好好听讲,劳民伤财,基础却没有打牢固。学生在学校里以正常节奏学习就可以了。”
抵抗住家长之间的焦虑传染,不追求孩子未来成为人上人,并不代表张艳对孩子是放弃或者躺平的态度。她有自己的教育方法,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是最拔尖的但都不错,特别是语文经常考第一。张艳说:“所有学科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语文,因为终其一生,它对个人素养等方面影响最大。这个想法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点关系,其实我的数理化分数很高,但我学的是文科。家里人不理解,我却一点儿不后悔。走向社会,面对人与人的交往,会发现一个人最基础的能力就是沟通和表达,如何说话、演讲、写文章。”她的孩子语文成绩好,也不是补课的功劳。张艳说:“我喜欢读书,孩子也读书,事实证明我孩子的语文特别好。中国孩子最不缺的就是应试技巧,有奔波去补课班的时间,不如在家读几本好的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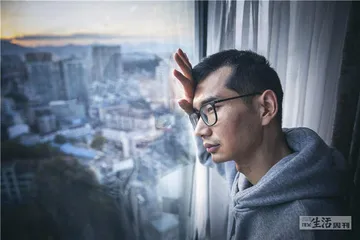 王丽和张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风浪,是在顺风顺水中逐渐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而另一种自我成长则来自把挫折转化成进步。李梅(化名)前几年从一家国企的副总职位上辞职,开了一家小公司。领导对她的决定有点儿吃惊,因为她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完全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告别职场。李梅的去意很简单,她来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学习业务流程,现在到了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李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言谈举止专业又干练。她最近在读一本叫做《坚毅力》的书,作者是逆商理论的提出者,她觉得书中桩桩件件都符合自己的经历。她说:“回首职场生涯,我想做的事情都能成,但是过程绝对是难的,中间真的坎坷挺多,磕磕绊绊。”
王丽和张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风浪,是在顺风顺水中逐渐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而另一种自我成长则来自把挫折转化成进步。李梅(化名)前几年从一家国企的副总职位上辞职,开了一家小公司。领导对她的决定有点儿吃惊,因为她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完全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告别职场。李梅的去意很简单,她来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学习业务流程,现在到了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李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言谈举止专业又干练。她最近在读一本叫做《坚毅力》的书,作者是逆商理论的提出者,她觉得书中桩桩件件都符合自己的经历。她说:“回首职场生涯,我想做的事情都能成,但是过程绝对是难的,中间真的坎坷挺多,磕磕绊绊。”
李梅大学刚毕业时不是现在的风格,她是恋爱脑,舍弃了很好的前途。“男朋友是北京人,婆婆帮我找了一个部委的下属公司,可具体工作就是站柜台。”李梅读的大学和专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分数不比北京大学低,天之骄子做了这样一份工作,人生遇到第一次挫折。李梅也曾迷茫和痛苦,后来还是爱情占了上风,过起了小女人的生活。“先生在央企,结婚就分房,没有生活压力。我整天就想着下班回家给他做好吃的。他外派三个月,我都能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辞职回老家等他。”李梅说。
丈夫出轨了,李梅当时25岁,孩子还小。李梅选择原谅了丈夫,但这件事成了一道坎儿,多年之后回想自己的人生,很多故事还是以此为起点。这件事也打醒了她,她开始花心思在事业上。她的逆商很高,凡事遇到不顺时就从中吸取教训。“有些道理你去问别人,得到的只是安慰。要想走出来,只能靠自己不停地反思。自我反思做得多了,逆商也能提高,遇到事情心态就不崩溃。”李梅说。
李梅外语好,又有专业背景,从一家外企跳到另一家外企,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最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很多外国公司来北京设立代表处,这给了李梅机会。“对人生来讲,选择特别重要,机会来了看你能不能抓住。从一家大外企跳槽去一家代表处时,我老公很反对,他觉得太折腾,但我看中代表处能锻炼人。后来证明我是对的,那家代表处像一所‘黄埔军校’,好几个同事都创立了很出名的企业。”李梅说。
正当李梅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她又面临选择。丈夫派驻海外长期工作,她如果随行又要回到家庭主妇的状态,因为家属的身份无法在当地工作。如果夫妻分居,可能影响感情,丈夫曾经出轨的经历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李梅选择了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她当时去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在国内的销售收入只有5万美元。“机会特别好,等于从零开始做,而且是全权负责。这能给我很大的成长。我跟另一个女孩一起,到2005年业绩做到亚洲第一。”李梅说。
跟刚结婚时相比,李梅仿佛换了个人,但她觉得这才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她从小就要强,比第一名考试成绩低0.5分都能哭一场。“我表面上看特别柔弱,但骨子里认定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李梅一个人又拼事业又带孩子很困难,父母劝她出国团聚,都没让她动摇。“我曾依附在别人身上,那时候没有安全感。安全感就得靠我自己掌控的东西实现。”李梅说。
职场上只靠放狠话没有用,李梅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因为工作关系,她每年要看大量的书,一边阅读,一边带入自己的人生和工作。“人如果迷茫,可能是缺乏认知层面的东西。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案例教学,他犯了错误我不讲大道理,我在吃饭前给他讲我看了什么故事、什么杂志,他听了这些之后,也能听进去道理了。”李梅说。
李梅也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她刚到国企任职时,其实相当于跳到客户的公司,大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继续在外企舒服地待着。“我从前的工作就是把国外授权的东西卖给国内就可以了,所以,我虽然在行业里很多年,但国内的流程是不懂的。我到国企是想学习这条产业链,大家觉得我好奇怪,居然还要来学东西。直到现在,我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还是愿意去了解和学习,我就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让我总结我这辈子怎么过来的,好奇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李梅说。
李梅的自我很坚韧,把挫折当作激励。她说:“我从外企刚到国营公司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不会适应,待不了一年就得走。我不服输,一定要干出成绩给所有人看。但我也不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我在做所有选择之前,一定先想好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承受。我能承受,就继续往前走;但如果我确实尽力了,还没有达成所愿,我就不会再坚持了。”
丈夫第二次出轨,给她的人生又带来一次挫折,她果断离婚。李梅的丈夫事业非常好,原谅丈夫,为了孩子维持家庭,李梅和孩子都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支撑,但她不想那样生活,也不后悔离婚。“这么多年的经历,我非常清楚人一生必须自己成长,不管挣多挣少,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才踏实。不愉快的经历其实也是财富,如果我的婚姻顺顺当当,也许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不离婚,整天吵着过到现在,过的也只是经济上不错的生活。但是,我选择了现在这条路,就要接受。”李梅说。
李梅开始彻底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她曾经变卖北京的房产移民海外,可真的过上闲适的日子又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没意思,只待了两年就带着孩子杀回北京,继续在职场驰骋。李梅说:“孩子的幼儿园换了三次、小学换了三次,高中之后才稳定下来。他17岁时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8年。我的遗憾是他跟着我奔波,身边没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自由也意味着要自己承担风险,李梅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她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所有决定都要我自己来做。它的好处是,所有事情我觉得能干成,一拍脑袋就去张罗。从我个人角度,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遗憾。” 自我于峰张艳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