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仰韶文化的起源:打破“中国文化西来说”
作者:刘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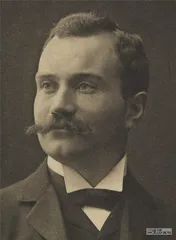 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彩陶,触及中国史前文明的衣襟。他对比西亚、欧洲发现的彩陶,认为仰韶与西方彩陶虽有各自独立创作的可能性,但相似程度使人有同出一源之感。为寻找中西之间的关联,探寻仰韶文化的源头,他打算到前往新疆、中亚的必经之地——甘肃、青海一探究竟。从1923年开始,他与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组成考察团,骑着马,驮着器材,带上助手,手握汉、蒙、藏三种文字的护照,被十名士兵护送着,踏上寻找彩陶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路程。
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彩陶,触及中国史前文明的衣襟。他对比西亚、欧洲发现的彩陶,认为仰韶与西方彩陶虽有各自独立创作的可能性,但相似程度使人有同出一源之感。为寻找中西之间的关联,探寻仰韶文化的源头,他打算到前往新疆、中亚的必经之地——甘肃、青海一探究竟。从1923年开始,他与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组成考察团,骑着马,驮着器材,带上助手,手握汉、蒙、藏三种文字的护照,被十名士兵护送着,踏上寻找彩陶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路程。
安特生首先前往青海考察,直到1923年冬天来到兰州过冬,受邀为当地学童演讲此前的考察内容,引起公众注意,随后有人从家里拿来前所未见的大型彩陶,拉开他在兰州周边考察的序幕,甘肃的史前考古也由此开启。
那些巨大如水缸的棕黄色的陶身,通体光滑、绘有神秘而规律的黑色图案,令安特生着迷。他在《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记述发掘其中一处墓葬的场景,“我们登高了数百米。肥沃的河谷远远落在我们后面,像一条深绿色的带子,再远望,更遥远的谷地也呈现眼前……我们终于来到一个高地,这里地势高亢,视野开阔。我们马上发现大量盗掘的遗迹,堆土中彩陶的碎片随处可见,彩陶片和我们在兰州购买的华丽而又完整的彩陶器属于同类……我坐下来,试图复原墓葬形成时期的情景……史前时代的洮河居民沿着陡峭的山路把死者送到10多公里之遥的山顶上,墓地高出居址足有400米,在那里人们可以俯视他们出生、成长和劳作的地方,他们的坟墓则沐浴在阳光和呼啸的风声中……”
一年多的时间里,安特生与助手在甘青地区调查、发掘了49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其中在甘肃发掘了马家窑、边家沟、瓦罐嘴、齐家坪、辛店、灰嘴、四时定、寺洼山、沙井等遗址。而发掘的同时,他们更是广泛向村民征集、购买彩陶。到1924年10月,考察团收集的材料够装25辆平时用的马车。为防土匪抢劫,安特生在兰州耗费108张牦牛皮,定做了两张大皮筏,把文物像包化石一样裹好,顺黄河而下,直到包头铁路,辗转回京。中瑞两国达成协议,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两国平分,先全部运往瑞典做记录、研究,之后一半归还中国。瑞典为此成立东方博物馆,安特生出任馆长。
在瑞典研究期间,安特生根据彩陶的纹饰和器型,按照由简到繁的演变逻辑,将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依远及近,自公元前3500年开始,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每期估为300年,前三期为新石器向青铜过渡的时代,后三期为青铜时代。其中的齐家期以单色陶器为主,仰韶期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900年,以彩陶为主,前后又分成马家窑和半山两个类型。因为相比河南仰韶的彩陶,甘肃彩陶更为艳丽,他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同时,他注意到甘青地区的彩陶没有发现陶鬲,于是他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制陶技术是西方经新疆传至甘肃,在此发扬光大,又从甘肃传至河南,与当地以鬲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融合而形成仰韶文化。
他的发现和分期,令甘肃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热门地区,也为甘肃史前考古搭起框架。自“中国文化西来说”甫一提出,中国学者就大多持抵触的心态,但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反驳,在当时几乎成为定论。夏鼐和地层里的证据
安特生在上世纪30年代重返中国,当他看到新疆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完全不同时,感到认识仰韶彩陶的来源为时尚早,他本人也承认,没有证据能说明甘肃仰韶期的遗存早于河南仰韶文化。
但那时依旧没有证据。安特生的分类,最为考古学者诟病的,是他不重视文化地层,虽然安特生是地质学家,但考古地层不同于地质地层,会有“打破”关系,并非埋在下面的器物就比上面的晚,而且安特生收集的大量彩陶源于征集,根本不知道原初位置在哪一层。
按照专业、科学的考古方法,为文物断代分期,需要地层考察与器物的类型学并重,不仅要分析碳-14的半衰期确定年代,还要逐一剖析同一文化层的文物类型,再与其他遗址已经发现的文物做比较,完善文物的谱系。就仰韶文化而言,对时代变化最敏感的器形是尖底瓶,中国学者通过分析尖底瓶的特征确定类型,再通过与尖底瓶同一层的陶器扩大类型的范围。
在40年代,地层分析已能够帮助中国考古学者推翻安特生的假说,夏鼐即为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位。从1944年开始,因抗战时局胶着,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夏鼐只能到相对安宁的西北,考察、发掘遗址。他在甘肃向村民询问安特生发掘的踪迹,验证安特生分期的结论。
夏鼐的日记中显示,文化地层的区分方法已经被他应用到中国考古中,除了在发掘中分辨不同颜色的文化地层,他也根据彩陶的纹饰判断时期。然而,当时夏鼐面临的情况是,经过安特生此前的寻访,文物出土多,则盗掘更甚,甚至引发当地村民盗宝的争斗,许多时候只能捡到零星的碎陶片。发掘时也阻碍重重,因春季挖掘会破坏庄稼,当地农民不是坚决阻挠,就是要高价赔偿。
即便如此,他也仍有重大发现。1945年4月至5月间他来到临洮,沿洮河两岸寻访遗址。他在《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记载,5月13日,他在宁定县魏家嘴村阳洼湾墓地试掘到两座用齐家文化墓葬,殉葬陶罐是典型的齐家期陶器。但关键的是,他在墓穴未下半部分的填土中发现两片仰韶期(实即半山类型)的彩陶片。
“填入墓穴的土,下半部是稍带棕色的黄土,厚约0.8米,甚坚实,但并未经过夯打。至于上半部的填土及墓葬周围的表面土,都是颜色稍深的棕色土,厚约0.5~0.6米,土质松软,似经后期翻动过。下层的填土,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扰乱过的痕迹。”夏鼐分析,“就这两片彩陶的位置而言,如果是埋葬后墓上的土经过扰乱翻动以致这些彩陶片混入,那么墓中的人骨和彩陶片既这样挨近,也必定会被动乱的;但是我们却绝对地没有找到这些尸骨被扰动过的任何痕迹”。未被扰动的填土必定比墓葬的年代早,由此首次从地层上证明仰韶期早于齐家期,“中国文化西来说”获得了第一个实际的反例。也因洮河流域仰韶时代的彩陶独特,夏鼐将安特生的“甘肃仰韶文化”重新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1956年、1957年间,河南庙底沟遗址和三里桥遗址被发掘。两个遗址均可分为两期,其中它们的第一期都属于仰韶文化,而庙底沟二期具有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特征,三里桥二期则属于龙山文化。由此,中原龙山文化的前身是仰韶文化被证明,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也被打破。
而上世纪70年代末,磁山-裴李岗文化被发现,并在老官台文化中发现较多简单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的先声,“仰韶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而对于“甘肃仰韶文化”的起源,如今在马家窑遗址上,已经发掘出直接压在马家窑类型之下的庙底沟文化类型。
(参考书目:马思中、陈星灿编著:《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夏鼐著:《夏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科学出版社;夏鼐著:《夏鼐西北考察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考古文物夏鼐仰韶文化炎黄文化仰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