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身体?
作者:孙若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曾写了《身体转向》一文,讲西方哲学领域之于身体认识的发展和改变。那么,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又是怎样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当下,当我们再去讨论身体,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身体越来越重要,还是恰恰相反?为此,我们专访了汪民安。中国的身体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曾写了《身体转向》一文,讲西方哲学领域之于身体认识的发展和改变。那么,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又是怎样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当下,当我们再去讨论身体,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身体越来越重要,还是恰恰相反?为此,我们专访了汪民安。中国的身体观
三联生活周刊: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身体的概念有真正的认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研究的呢?具体到中国,这种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汪民安:很难说人是从具体的哪个时候对身体的概念有真正的认知的。我想在有文献之前人类就应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了。因为在我们都熟悉的早期经典著作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文学,还是中国先秦思想著述,身体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显赫的存在了。这些文献都体现出清晰的身体观念。
如果不是从文献而是从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人类的开端,人类就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局限了,就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工具。法国古生物学家勒鲁瓦-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认为,如果没有工具,人就难以存在,就没法存活。他的意思是,人的工具就是身体的外置器官,就是一个人工器官。他借助这种人工器官来保存生命,来捕食,来防卫。如果没有这个工具性的外置器官,人就活不下来。也就是说,没有体外的工具器官就不存在人这一生物类属。去年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和古汉有过合作,他写过一本书叫《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讲的就是人的身体天生是有缺陷的,因为爱比米修斯赋予每一种动物强大完整的谋生本领,但没有赋予人同样的本领。所以普罗米修斯就给人类盗火,换句话说,人是通过外在的工具活下来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不完备的。可见,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能力和身体缺陷。
至于说到中国古代的身体观念的认知变化,坦率地说,这类文献浩如烟海,太复杂了,很难说清楚。儒释道都有大量的从不同角度关于身体的论述。有谈论身体本体,即身体的内在构成问题的;有谈论身体和外物之间的关系的,即关于身体和宇宙、自然、政治以及其他身体的关系的问题的;也有谈论身体的技术问题,即所谓修身和礼仪的伦理问题的。这些不同的身体视角有各自的问题框架,但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身体本体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宇宙论和世界观,而世界观的问题又决定了我们的伦理选择问题。
但对中国哲学来说,到底什么是身体呢?我们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气”论传统。我觉得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将身体看作一个气化过程。气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人的本体。就像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言,“人在气中,气在人中”。气分为阴阳二气,它们在体内辩证地争斗,试图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旦阴阳二气失衡了,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医书也是这样讲的:“气血,人身之二仪也,气为主而血为配。故曰:气化即物生,气变即物易,气盛即物壮,气弱即物弱,气正即物和,气乱即物病,气绝即物死。是气之当养也明矣。”(《医方考·气门》)身体就是一个动态的、争斗的、辩证的气化过程。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身体观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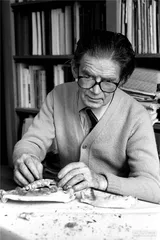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的传统里,怎么看身体和意识的关系,和西方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的传统里,怎么看身体和意识的关系,和西方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汪民安:西方的哲学传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二元对立。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基本上都是将身体和意识对立起来的,它们可以各自独立。柏拉图认为灵魂可以摆脱身体;笛卡尔说,我哪怕一条腿被锯掉了,但是我的意识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中国的气的概念同时包括了身体(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和身体交织在一起,不可区分。气是一种精神化的身体或者是身体化的精神,它是一个能量整体。正是气产生了万物,万事万物都是气化过程的效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将精神与身体进行严格的二分。而西方最早的对于身体的理解还是物质化的。非常粗糙地说,西方观念中是将身体看作一个静态的结构化的物质,他们的兴趣和问题是:身体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他们强调一个科学化和物质化的身体。比如身体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等不同物质逐层递进和叠加起来的,这些物质同时也是可见的和确定的。而我们几乎说不清楚气是什么,只是从气的功能来描述气。因为气是不可见的,只有效果而无形象。
不过,到了晚近,尤其是从叔本华开始,欧洲的身体(生命)概念有了一些变化,他们特别强调力的概念。受叔本华的影响,尼采、弗洛伊德和柏格森都特别强调了身体的不可见的内核:冲动的力和能量。这就是19世纪以来欧洲新的生机主义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到德勒兹这里达到了顶峰。我觉得这个力的身体哲学传统和中国古代的气化的身体观念有相近之处,二者之间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对话。比如说德勒兹的身体概念,就是说内在的力在体内不断地奔突和冲动,力也分为两种力:肯定的力和否定的力、消极的力和积极的力等,它们也在永恒地争斗。这非常接近中国的阴阳二气之间的争斗。中国的气的争斗讲究平衡,但是,尼采主张肯定和积极的力应该战胜否定和消极的力;叔本华与尼采则相反,他很消极和悲观,所以尼采说他像坟墓中的人。与中国强调气和气之间的平衡不同,欧洲更强调两种力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不过,对于19世纪以来欧洲生机哲学中的“力”的概念,我的印象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尼采、德勒兹很少提到中国思想,但力和气确实有一些可以比较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德勒兹讨论画家培根的时候,认为培根那种面目模糊扭曲的身体是因为力在体内狂奔,冲毁了身体各器官的稳定性,让身体变得流动起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人物绘画中,器官也不是非常确定清晰的,尤其是跟西方的写实油画相比。中国古代的人物画不太着意画脸部器官,而是特别喜欢画衣服,衣裙似乎更能表达人物的生命,这跟中国的“气论”有关。最著名的就是吴道子,所谓吴带当风,他画的衣裙都像是被风吹起来一样飘逸抖动。但这种衣裙的飘逸不是由外在的风刮起的,而是因为体内的气的饱满外溢。
无论如何,力和气,非常值得进行比较。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还没有真正地展开。对中国哲学熟悉的人,大多对这段从叔本华到德勒兹的欧洲思想不太熟悉,反过来也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大约20年前,你在文章《身体转向》里梳理了哲学领域对于“身体”认识的变化,那么,艺术和身体的关系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三联生活周刊:大约20年前,你在文章《身体转向》里梳理了哲学领域对于“身体”认识的变化,那么,艺术和身体的关系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汪民安:绘画大概从一出现就在描绘身体。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现在,身体都是艺术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在20世纪之前的艺术中,身体基本上都是绘画或者雕塑的描摹对象。也就是说,身体的外在性成为艺术要处理的对象。当然,描摹身体的外在性更多是为了挖掘人的内在灵魂和精神一面,这在伦勃朗的众多自画像那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我觉得20世纪的现代艺术与此不同,现代艺术放弃了对身体外在可见性的描绘努力。他们对身体的内在性感兴趣,但这种内在性又不是像伦勃朗那样通过对外在性的描绘来表达的,这种内在性也不是魂灵或者精神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要直接展示内在性,或者说,要展示那种不可见的身体。但什么是内在性呢?身体的内在性就是力、能量或者意志。现代艺术致力于展示这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我觉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残酷戏剧是这类身体艺术的开端。阿尔托相信,身体内部有一种力在呼喊、奔跑,他说身体内部就是一种永不停歇的田径运动,每一次喊叫都是一个田径式的冲刺。他的剧场要展示的是身体内在的力的喧嚣和奔腾,他要让力以及力所引发的紧张、残酷和血笼罩、灌注在整个剧场之中。除了阿尔托之外,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和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舞蹈都强调身体内在的力的爆发。
在绘画领域,画出身体的内在性是从培根开始的。培根跟以前的肖像画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通过将身体的内在性和外在性进行并置性的扭曲来展示力的流动过程,培根画出了肉的不断撕扯,肉的不断遭蹂躏而动荡而起伏而喊叫的过程。在培根这里,人体不再是一个结构,至少不是一个机器化和物质化的结构,人体是骨头和肉交织而成的整体,是这一整体的动荡、起伏和扭曲,是全部的肉的扭曲。德勒兹将这一扭曲的身体称为“无器官的身体”。身体为什么会扭曲?就是因为它充斥着力和力的争斗。正是通过这种肉的内在扭曲撕扯,培根画出了不可见的力。
除了让这种不可见的内在之力涌动起来之外,从20世纪中期开始,还出现了一种身体和艺术关系的新尝试,这是从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开始的,也有很多激浪派艺术家有非常激进的尝试。这些艺术家相信身体的偶然性是艺术作品的起源,创作过程是身体的偶发行为,它既不取决于训练有素的身体技术,也不取决于理性的深思熟虑。除了波洛克之外,克莱因是这方面的代表:克莱因让身体涂满颜料的模特在地上的画布上自由滚动,滚动形成的图案就是最后的作品形式。艺术不过是身体的偶发行为。他们相信,偶然的身体,而不是理性或者技术,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但是,这样的身体尝试对艺术家来说还不满足,在20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更激进、更具挑衅性的身体艺术潮流,这是从维也纳行动派(Viennese Actionist)开始的。这些艺术家将鲜血、内脏、分泌物作为作品的素材,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身体艺术。身体本身直接作为作品的对象,这是个受难的身体、被肢解的身体、破碎的身体、流血的身体,甚至是被死亡阴影所覆盖的身体。艺术家让身体处在可能的极限状态。这个潮流的最后尾声大概是以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为代表的英国YBA一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运动中还出现了很多女性艺术家,像小野洋子、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阿布拉莫维奇等。这个潮流在20多年前对中国艺术家产生过很大影响,90年代北京“东村”的艺术家也可以放在这个潮流之下。我要说,这类与身体有关的艺术实验,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最有意思的艺术潮流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身体艺术潮流后来的发展如何?在今天,艺术家对身体的关注点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身体艺术潮流后来的发展如何?在今天,艺术家对身体的关注点是什么?
汪民安:这几种身体艺术潮流如今都已经退潮了。今天艺术家对身体的关注出现了另外的特征,既将身体和技术关联在一起,也强调科技对身体的改变。在这个科技艺术潮流中有一个分支被称为生物艺术(Bioart),这样的作品创作越来越具有实验室的意味。艺术家和科学家合作,或者艺术家本身就有一定的医学或生物学知识,他们通过新的技术来改造、重塑或者发明一个新的身体,这类作品的开端标志是卡茨(Eduardo Kac)在2000年创作的《绿色荧光兔》,他让一只活的兔子变绿了。一个新的被技术创造出来的身体,一个不同于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身体,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
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说,20世纪有这样几种模式探讨艺术和身体的关系:将身体看作一种内在活力的奔突;将身体看作艺术创造的起源和条件;将身体作为自我技术和自我实验的对象;最后,在新科技的条件下,去发明一种新的技术化身体。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身体艺术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
汪民安:这既跟我刚才说的生命哲学的兴起紧密相关,也跟社会的历史变化密切相关;或者说,艺术和哲学同时感受到了时代的某种变化。不过,尼采和弗洛伊德可能比艺术家走在更前面一点。正是尼采和弗洛伊德对欧洲理性哲学的霸权提出了抗议,他们突出了身体、力、本能、无意识或者力比多这些原来被理性主义所压抑的一面,并且将这些看作人的更基础、更始源的决定性要素。强调本能的生命哲学开始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强调本能、力、性和身体的艺术潮流也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当然,确实可以具体地谈论艺术家受到哪些哲学的影响,比如说,尼采之于阿尔托、弗洛伊德之于维也纳行动派等等,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其说艺术家直接受他们的影响,不如说艺术家此时此刻的特有经验可能契合这种新的哲学潮流。在20世纪初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的转变,即不同领域的知识学科同时发生了转型。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从哲学到艺术同时有一种强调身体的转型呢?
汪民安:有很多这方面的解释,人们要么归于启蒙理性的过度伸张,要么归于战争导致的痛苦创伤,要么归于技术治理效率的铁笼捆绑等等,大体上来说,在20世纪,理性确实开始受到尖锐的质疑。阿多诺和卢卡奇后来都对此做了反思。卢卡奇在5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理性的毁灭》,这个书名恰当地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氛围:时代的不幸都归结于理性的过度发育。一旦明亮可见的阿波罗秩序遭到怀疑,那些底下的狂奔乱舞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就会喷薄而出。尼采、弗洛伊德、阿尔托和巴塔耶以及紧随其后的艺术家都是狄奥尼索斯在20世纪的幽灵再现。我要强调的是,这些不是人类的新事物,而是对苏格拉底之前的古老艺术的一次充满差异性的往复轮回。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轮回,艺术史也一直在轮回。不断有艺术家在转向这种希腊时代的酒神精神,像16世纪后期的丁托列托、格列柯,19世纪的戈雅等等,只不过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时代极为罕见,这些作品在它们的时代像闪电一样瞬间发光,但又快速地归于沉寂。只是到了20世纪,这样以身体为焦点对象的酒神式的艺术才大规模地涌现,他们一度短暂地占据了20世纪的舞台。
三联生活周刊:把身体作为艺术品来创造的初衷是什么呢?
汪民安:实际上,我们对身体的认识非常有限,人们很少尝试自己身体的可能性。比如说,你会觉得鼻子唯一的功能是闻,耳朵唯一的功能是听,你对此从不怀疑。但是德勒兹讲“无器官的身体”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想象用嘴去听、用鼻子去吃、用耳朵去说话呢?为什么不能把身体器官的既有功能重新悬置起来,去实验它的新的可能性呢?他提到了很多改变自己的身体的行动者,包括抑郁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他们实际上就是在重新发现和使用自己的器官,他们的乐趣就在于此。所谓“无器官的身体”的核心在于,要让既定的器官功能失效,要重新发明和发现自己的器官功能。
福柯在给德勒兹的书写序的时候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我的法西斯主义。所谓“自我的法西斯主义”,就是我们被我们自己所统治和规训。怎么被自己统治和规训呢?就是我们从来不想象、创造和发明一个新的自我。我们臣服于自己既有的身体结构,我们也习惯了我们的臣服,接受了这种臣服。如果要打破这样的臣服,那怎样去发明和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呢?人们的一般方法就是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改变自己身体之外的一切,人们发奋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新人。但对德勒兹和福柯而言,这都不是真正的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改变。发现和实验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身体的可能性,让自己的身体不断地趋向一个极限,获得一个特有的从未尝试过的全新经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自己。只有身体的自我实验,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才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自己。
大家都熟悉的阿布拉莫维奇和谢德庆的作品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我绝对相信,阿布拉莫维奇和谢德庆的作品毫无疑问会跻身20世纪最伟大艺术作品的行列。还有许多舞蹈者的作品,比如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舞团DV8,他们中的残疾人发明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运动和舞蹈。你看,身体在这里展示了奇迹。对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完成一件作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束了这件作品,就可以甩掉它和遗忘它了;相反,完成一件作品可能就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发现的开始。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如今人们讨论身体,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进入的,这种技术化的身体不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身体。如果人离不开手机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赛博格。如果这么说,人从一开始就是使用工具的动物,那是不是人从一开始就算是赛博格呢?或者说,现在的赛博格和以前的赛博格又有什么不同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如今人们讨论身体,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进入的,这种技术化的身体不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身体。如果人离不开手机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赛博格。如果这么说,人从一开始就是使用工具的动物,那是不是人从一开始就算是赛博格呢?或者说,现在的赛博格和以前的赛博格又有什么不同呢?
汪民安:像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和斯蒂格勒都承认,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实际上,马克思在他们之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了。但是,哈拉维讲的赛博格(Cyborg),不是指人和工具的一般结合,而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物,是硅元素和碳元素的混合物。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流通的信息通道,这使得以碳元素为基础的有机体和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电子部件之间能够互动,从而使硅与碳在一个系统中运行。所谓的赛博格就意味着这样的硅元素和碳元素不可分离的复杂编码配置,这就将人和机器的区分打破了。这是用混杂性来破除单一性,单一的有机身体概念瓦解了。
而斯蒂格勒将人和工具,也就是他说的外置器官的结合,可能同这样的赛博格还不太一样。尽管这样的工具对人来说是决定性的,但是人可以短暂脱离它们,比如人在不工作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这些工具。人和它们是一个目的性和功能性都很强的临时性结合,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体外的结合,一个力学结合。但是,对于一个装有假肢或者一个心脏起搏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持久的内在的结合,一个信息流通式的结合,一个不可分的编码配置。
而控制论对于身体的理解也不同于赛博格。尽管赛博格摧毁了有机物的同一性,但是它还是保留了有机肉身这样的概念。对于控制论理论家来讲,他们相信肉体化的生命只不过是整个生命漫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在他们看来,生命实际上是可以脱离肉体的。我们谈到的生命一定是以肉身作为介质或者根基而出现的。但是对控制论来说,所谓的生命就是一个信息通道,是一个计算式的信息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套计算程序就可以是生命了,完全可以摆脱肉体这样的物质媒介。就像AlphaGo没有肉体,但仍被看作是生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就是生命本身,是一个没有肉体的生命。控制论很久以前就大胆地想象过,将来我们的肉体要消失了,可以有一个插口插入大脑,把大脑里面的信息下载到电脑里保存起来。虽然肉体死了,但你作为一个信息生命还存在着。几百年以后,我把你的电脑打开,把信息复活,你就复活了。
三联生活周刊:控制论认为身体不重要,但有相反的观点越来越看重身体。
汪民安:是的,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控制论的想法是将算法模式看作是生命,这样肉身可能越来越不重要了,就像苏格拉底将灵魂看作是生命而因此贬低肉身一样。但是,基因技术与此相反,它们更强调身体本身的重要性。它们通过干预基因的方式来干预身体,来不断地完善身体,旨在让人的身体更健康、更聪明、更漂亮。总之,它们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身体。但是,它们也可能塑造出一个令我们无法想象的陌生身体,一个能够代替人身的身体。
无论如何,我们的身体夹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科学这两种技术之间,有时候受到它们的刺激而感到兴奋,有时候被它们的威力所震慑而感到恐慌。这两种技术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张力,福柯宣称的人的终结就存在于这种张力之中。如果说,瘟疫伴随着人的整个历史的话,那么,要一劳永逸地消除瘟疫,或许只能借助这两种技术了。而这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就是人的终结。也就是说,想要让人无所顾忌地活下来,也就要在技术的帮助下让人死去。我们的时代正是因此而饱受折磨。 汪民安艺术家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