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流行文化亦敌亦友
作者:薛巍 油画《三个哲学家》(意大利乔尔乔涅作品)
油画《三个哲学家》(意大利乔尔乔涅作品)
哲学和幽默的共性
哲学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风趣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93节“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但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对比较了解德国观念的人来说,读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尼采对康德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普通读者则会茫然。尼采在这里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上帝、自由、永生这些东西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说,为了确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必须预设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对于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这种出尔反尔,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海涅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中说,康德之所以又请出了上帝,是因为他在破除宗教之后,出去和他的老仆人散步,突然间觉察到这位老人热泪盈眶,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鉴于他的老仆人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要不然他们就会郁郁不乐,他为了显示自己不仅是大哲学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这三大预设,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嘲讽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应该叫“先验麻醉剂”(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
哲学家著作中有一些比较形象的比喻,通过这些比喻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理论上的差别。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分为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两大阵营。英国的洛克说,人类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没有经验之先的所谓天赋观念或固有原理,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经验。德国的莱布尼茨则认为存在天赋观念,但天赋观念并不是生来就明白与清楚的,它需要经过一段发展过程,即需将人们心中潜在的普遍的知识逐渐地展开,才能成为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人心既不是白板,也不是一座已经成形的雕像,而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经过加工、琢磨才能渐次成为一座雕像。当年老师让我们为斯宾诺莎的心灵理论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这要求透彻地理解他的认识论,同时又能锻炼形象思维能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数学教授、《数盲》一书的作者艾伦·保罗斯还写过一本《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的一面》(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在序言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妙语,一本哲学书完全可以由笑话组成。我对分析哲学及其难题总是抱着一种兴趣,我认为,在哲学抽象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之间的界线特别值得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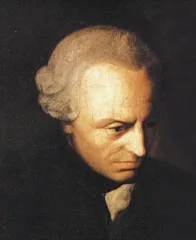 康德
康德
从刘易斯·卡罗尔充满语言游戏和胡言乱语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跟维特根斯坦考虑过的问题有关联的片段。片段一:爱丽丝把手放在头顶上,以便感到她在以哪种方式长大。片段二:毛毛虫说:“背得不对,简直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片段三:爱丽丝说:“停一分钟让人喘息一下好吗?”国王说:“我够好的了。只是我不够强壮。你看,一分钟就这样可怕地飞驰而过。你想停止一个想象中的猛兽不成!”保罗斯分析说,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显示了关于某些概念的逻辑混乱。一个人用不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头顶上,来判断他是在长高还是在变矮(除非只是他的脖子正在生长)。一个人也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正确地背诵一首诗,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在背诵那首诗。接下来的一段,错误地像说“列车”一样地来说时间。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论点就是,很多哲学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是由于对语言的误用。
《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书籍则是普通人也能看明白的读物。读笑话学哲学的依据是,“幽默和哲学就其精髓来说都是富有人性的,就像它们的确要求的那样,要求一种超越自我及其境况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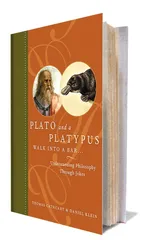 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
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
比如在讨论境遇伦理学时,这本书讲了下面这则笑话:一伙武装劫匪闯入一家银行,命令顾客和银行职员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拿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首饰。银行两位会计也在队伍中即将轮到被抢劫。一位会计突然把一样东西塞到另一位会计手里。那位会计小声问:“这是什么?”第一位会计小声回答说:“是我欠你的55块钱。”
作者用这样一个笑话来说明柏拉图的美德理论: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天使,对哲学系系主任说:“我可以授予你如下三种东西中的一种:智慧,美貌或者1000万美元。”教授立马就选择了智慧。一道闪电过后,教授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桌子看。他一位同事小声说:“说话呀。”教授说:“唉,我本应该选择要那笔钱的。”琢磨一下才知道,这个笑话要说的是,在天使授予系主任智慧之前,他笨得不知道应该要钱,所以智慧是得到金钱的前提,智慧比金钱更重要。
 《新哲学》杂志
《新哲学》杂志
给哲学披上有趣的外衣
借助流行文化能达到普及哲学的目的吗?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斯蒂芬·阿斯玛对此表示怀疑。哲学从来跟流行文化都没有和谐共处过。传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以思考宇宙为己任,严重地脱离世俗世界,据说他走路时总是抬头看天,有一回不小心掉进了路旁一口井里,遭到女婢的嘲笑。海德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就是:“哲学是本质上无所取用而婢女必予以取笑的那种思考。”哲学是沉思的、孤独的、超脱的,流行文化则是拥抱现实世界、众乐乐的。
世界文明史上有很多关于神灵、恶魔和精灵的传奇故事。当哲学家希望重塑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时,他们就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故事。这表现在西方哲学的起源中。当泰勒斯把注意力转向看得见的事物,比如水存在和运动的模式时,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就开始取代神话学。这些先驱们用他们的学说取代关于神和他们干涉人类生活的故事。柏拉图批评得更加直白,他在《理想国》中要求禁止荷马的神话故事。虽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用科学取代神话的倾向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故事现在是前所未有地流行。在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让人们更加沉溺于故事中。向流行文化的消费者传授哲学时,教师们希望因势利导。
借助流行文化传授哲学,就好比博物馆的做法: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曾经引进了一个时尚物品巡展,展出哈雷摩托车、巧克力和杰奎琳·肯尼迪的衣服,希望参观者在看了这些时髦物品后,会踱步到那些更实在的永久性展品的展区。但这一招并不奏效。
虽然有人在大力地普及哲学,但最终哲学依然会跟流行文化保持对立和疏远的状态。不是因为哲学存在偏见,或自视为精英,而是因为它是一门尤其对自己的历史加以反思的学问,需要经过高度的训练、整体的理解和概念化思维能力,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并非轻易加以掌握的技巧。在这门最古老的学科中,不理解它的历史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未曾广泛阅读过原著的人会感到自己无法进入某个哲学家或哲学问题。这种被排斥感可以通过做一些必须的研究来加以消除,比如补一些知识。但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检查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能力,有别于通常经验性的研究。
“哲学通俗化虽然面临很多障碍,但是将它变得更加有趣还是大有作为的。老派的哲学家或许会把流行文化看做臭水沟。但王尔德说得对,我们都身处臭水沟中,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仰望星空。” 哲学研究康德哲学思想流行哲学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