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过度依赖,然后……
作者:王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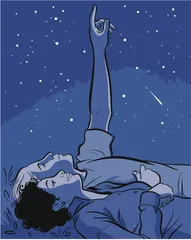
依赖的开始
有的人觉得自己在爱情关系中极度独立,可是并不。依赖往往是在微妙中诞生的。
比如美国作家米切尔的《飘》里面的郝思嘉,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个要支撑家庭的女人,也因此对爱情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她和白瑞德的复杂关系中,从开始的吸引、抗拒,到结合、分离,一直处于所谓的独立状态。小说叙述经常进入到郝思嘉的个人心理状态,她的个人期许中,自己是独立的,自己的迷恋对象,是那个永远得不到的卫希礼,对白瑞德,只是勉强、将就和利用——可是,作者在超越郝思嘉的个人描绘中,详尽描写了她对白瑞德的感情并不止于此。
她并不知道,其实她是极度依赖白瑞德的。这种爱情来自最原始的吸引力,尽管米切尔的描绘非常隐晦,可是毫无疑问,白瑞德雄厚的男性的富有侵略性的气质吸引了她,她情不自禁地屈服,尽管她欺骗自己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跟随了白瑞德。随后的两人关系中,郝思嘉一次次地向白瑞德倾斜,早年爱慕的卫希礼逐渐成为虚妄的影子——她对他是全身心的依赖,他的行为准则是她的标准,他的男性魅力是她为之骄傲的地方。
这种依赖关系,在她没有完全察觉的时候占据了她。她以为她在利用他,占有的是他的金钱和关系,可是情感上的依赖逐渐控制了她,最后当她明白的时候,白瑞德已经离开,她只能告诉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句豪言壮语,怎么听也觉得有点凄凉的勉强——尽管是郝思嘉一贯性格的体现。
 电影《乱世佳人》。根据美国作家米切尔小说《飘》改编
电影《乱世佳人》。根据美国作家米切尔小说《飘》改编
有趣的是,在小说中,白瑞德尽管表现得非常有魅力和有独立个性,可是他也依赖着与另一个不相干的女子的关系,韩媚兰——表面上两人相敬如宾,可是白瑞德在占有了巨大的世俗成功后,依然渴望着灵魂的洁净,这时候,宗教感极强的女子韩媚兰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以至于他在观察郝思嘉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总是拿韩媚兰作为比较对象。
依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表面化。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的状态里,已经深刻地依赖着对方,除了最肤浅的经济关系和肉体关系等所谓契约系统的依赖外,更深的依赖在于:依赖一种熟悉的感觉,依赖一种既定的关系,尤其是在心理上,捆绑成了无法分开的状态,觉得一切事情,都无法与对方分开。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依赖就变成了过度依赖。一位熟悉的朋友,详尽地描绘了她对自己昔日的爱人若干年内过度依赖的状态,这种状态,到了最后,成为两人分开的主要原因。
她是在29岁生日的前一天遇见他的。她一直觉得自己很独立,也很强大。那时候,刚刚在大学读在职的博士不久,有人会觉得一个29岁不结婚的女博士状态应该不佳,可是她丝毫不觉得:她算得上漂亮;工资不高,工作却很有趣,在一家不错的科技公司做总监;有自己的房子,刚考上博士,学习着自己感兴趣的古典美术学科。在她看来,自己这么优秀,有人爱上她,进而为她痴迷不悟,都是顺理成章的。
他是个公务员,他们的见面,并不是经过了平庸的熟人介绍或者那么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而是通过参加一次装模作样的古典音乐会鉴赏栏目。她是那个栏目主持人的朋友,在那次鉴赏会上,她被请去充人数。而他是古典音乐的热情爱好者,有相当的古典音乐知识。两人坐在一起,他纯粹没话找话,用最初级的古典音乐知识来搭讪,她立刻讪笑,表示自己对这些浅薄知识的厌恶,说她既不喜欢这个讲座也不喜欢误导人的鉴赏,而他也告诉她,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古典音乐,并且开始谈版本,两个人在嘲笑台上的主讲人的过程中达成一致,迅速发现可以谈到一起。
在交往的过程中,她神速地展现了自己一贯的骄傲,她对历史、对文学的认知比一般人深刻,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熟悉和热爱发自内心,萨特和波伏娃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名字。而他对她的一切极其迷恋,在他30岁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女人,既成熟大方,又天真活泼——本来也是,一般公务员的世界并没有那么丰富,这样一个乐于展现自己有趣的女性也很少见。
她向我描绘他们交往数个月后他对她的迷恋:“我在校园散步,他打电话说想念我,我说你就想吧,没空搭理你,一句玩笑话,他在电话那头就开始哭泣了。我是他的初恋,他觉得我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他。这种让人心动的迷恋,很让我觉得愉悦,比起一般的男女调情游戏,纯真的感情触动了我,让我在认识了他几个月后开始考虑和他的关系。”
在她没有依赖他之前,是他先彻底依赖她的。
她是骄傲的女性,一直以为自己会有更好的归宿。她希望自己未来的爱人是位学者,或者是位出色的作家,从来没有指望他是个平凡的公务员,可是他感情投入的纯度极其高,让她洋洋得意,自己的吸引力这么强。甚至有点迷惑,自己的魅力真这么强?“他甚至会在公交车上为我哭泣,在众人的目光中,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后来解释说,是因为那阵子特别柔软,想起我,就觉得心疼。他举出廖一梅的文字作为佐证,30岁的男人,遇见性,遇见爱,都不奇怪,难的是遇见了解——他觉得彼此之间是彻底了解的。”
虽然在公务员系统中,可是他一直有自己的追求,他热爱古典音乐,热爱文学,而这个女人是第一个能与他畅谈一切精神话题的人,而且常常比他高明,他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心态,就是觉得,这个女人,可以解决他的一切问题。在他心目中,她是骄傲的天鹅,做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也就是这种极度的迷恋,让她终于放弃了防备,觉得自己可以依靠这个男人的爱情,她说自己在设计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时候,本来没想到这么快投降的。可是他极度的依赖,让她产生了柔情——这么依靠自己的人是可以相许终生的。
互相依赖
热恋常常是让人糊涂的。事实上,两人的热恋期也很长。就是在热恋状态中,她逐步发现,自己对对方的依赖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强。突然有一天,她惊异地发现,自己的骄傲感没有了,这个男人比一切都重要。
她向我解释,她的极度骄傲其实是有自卑的底子的。小时候,她和父母生活在小城市,因为父母属于那个小城的外来者,所以事实上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她从小就和同学关系一般,总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小城市,后来通过升学到了北京,一路顺风地读了上去,逐渐觉得自己的未来可以很美好,过去的一切被抛弃在后面,可是心底里的自己却还是个被孤立的小城女孩,那个自我会不时地跳跃出来。“我一直对自己说,我是强大的,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确实如此,我工作很出色,因为工作也有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都是些让我愉快的朋友;地位和金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所以,剩下最让我渴望的,一直是让我能够死心塌地的爱情。在他之前,我谈过几次恋爱,但是都不是特别投入的那种,总觉得,会有好的在后面,其实等到真正恋爱的时候,哪里还计较什么条件,我越来越有此生无遗憾的满足感。”
她说那时候自己极度依赖自己的爱人。先是从精神上如此。“每天双方都有十几个电话来往,明明可以发短信解决的事情,也绝对是抄起电话就打,下班后就在一起,如果出差,更是不得了,几乎是一个小时一个电话。同事都觉得我变化特别大,本来是独立的性格,现在却特别爱撒娇、爱笑,现在想想,这其实是自己放弃了自我的表现——当然也有可能,原本的自我就是个喜欢被宠爱的小姑娘,后天的自我才是假象。”
然后是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本来我的工作很不错,职场应付得游刃有余。可是那一年,正好和领导闹别扭,一气之下,在12月31日辞职,年终奖都没有要。按照道理来说,我的男朋友性格比较沉稳,应该会劝劝我,而且他在公务员体系中,特别知道分析利弊轻重。可他过于爱我,完全什么都听我的,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听说我要辞职,就是很简单地说,没事,他有钱。”
她30岁的时候才觉得被爱是件很好的事情。过去她没有用过别人的钱,包括对父母,也注意不要亏欠。工作后她很注意,经常性地给父母大笔的钱,觉得那是自己的本分。“可能因为父母都不是特别能干的人,潜意识里觉得我不能依赖他们,他们该依赖我才对,这时候,第一次出现一个我全身心可以依靠的对象,心理满足感很强。”
在她辞职的第一周,他们就办好了去欧洲的签证,两个人选择了很少有人去的巴尔干群岛,因为那里有她喜欢几位的作家的遗迹,在松林中去寻找那些作家的墓地,那是她感觉最美好的旅行。
“在我失业的几个月里,他把他的银行卡给我,让我每个月可以继续消费,我这时候已经彻底地放弃了自己过去的独立习惯,觉得这个男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其实她并没有那么缺钱,包括他给她的银行卡,她也没有多使用,但是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这个男人的出现,让她放弃了过去努力维系的独立的自我,然后交出了自我——有点像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一句话,见到他,她忽然变得很低很低。“我觉得女性很容易走到这一步。哪怕自己再强大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从心底里一直在寻找那个值得放弃警惕性的人,其实你看看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知道了,强大如她,也是完全依靠萨特的喜怒哀乐来判断自我得失的。我分析,她和那位美国作家的关系,是寻找自我的表现,因为在萨特那里完全丢掉了盔甲,所以她重新在别的男人身上找回自我。”
因为学习过心理学,所以她能够比较清晰地分析自己和对方每一步的行事动机和心理因素。她的讲述,也使我如同在观看一部有趣的电影,可以顺畅地理解下去。
双方这种对爱情的依赖,如果掌握得好,是很有助于爱情的持续发酵,并且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的,可是,在我们的爱情系统里,从来就没有那么四平八稳的故事,老天也常常要作弄人,让双方经受考验,经受磨难——能不能过去,需要更高的情商和智商。
过度依赖之后的控制
毛姆在他的小说《刀锋》里讲过几个爱情故事。小说从主人公和他的朋友们的青年时代讲起,一直到他们之后的哀乐中年。其中并非女主角的苏菲令人印象深刻,小说开场的时候,她是个满脸雀斑、梳麻花辫的女孩子,充满了热情,喜欢崇高的事物,尤其是诗歌。可是小说结束的时候,她成了风骚放浪的妓女,虽然也还在朗读诗歌,可是感情于她,已经成为一钱不值的东西。
苏菲经历了惨痛的人生才有了这般结局。她很年轻就有了自己的理想对象,按照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的话:是芝加哥的女孩子们普遍觊觎的对象,英俊、富家子弟,两人没有现实烦恼地结婚,生孩子。可是这种爱情早已经埋下阴影,小说中别的人说到他们俩,都觉得非常可笑:在他俩的世界里没有外人,他们几乎没有一刻分开的,爱情浓烈到了极端。用小说里世故机警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话说,那种爱是杀人的。
果然,当苏菲的爱人和孩子在一次车祸中死亡后,苏菲就不能继续正常生活下去,她开始放浪的人生,当婆家不能忍受她的行为出钱把她送到欧洲后,她更是走向了极端。小说中的我,也就是毛姆的结论是:对于苏菲来说,那种崇高的两个人之间的爱,对于她是天堂;当天堂失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待在人间,索性走向地狱,这又是一个过度依赖爱情的故事。
我的朋友告诉我,她确实有段时间和苏菲的感觉一样,爱情是天堂。不过任何天堂都一样,除了美好的事物,也有苹果,也有蛇。
“我开始了控制。本来我不是一个喜欢控制对方的人,可是感情浓烈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既然我对你是全部开放的,你对于我也要全部开放。那时候我开始看他的手机,参加他的每一个聚会,研究他的短信和微信,看到陌生的电话,我都会要求他马上当着我的面拨回去,每天下班去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回家。”
她反思自己的这种控制,其实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按照道理,他们的相爱中并没有第三者出现,并不需要这种对对方的强大的控制。“可是我过于依赖这种感情的存在,本来爱情应该带给我强大的安全感,可是我内心里那个无依靠的小女孩总是会跳出来,要求保证爱情的绝对纯粹。”
这其实有点像王朔那部曾经风靡的小说《过把瘾就死》,从小缺乏正常家庭关怀的女孩子杜梅在长大后,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押在男方对她的感情上,这成为她的赌博,男方稍微退让,她这边的砝码则加重一轮。
而当男方努力挣脱这种束缚的时候,悲剧诞生了,很少有感情能经受这种长期的考验。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事实上,无法去责怪杜梅或者男主人公的任意一方,心理上的原罪,是无法通过谴责解决的。90年代,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当时为了丰富剧情,也为了让男女主人公的冲突有合理的解决方向,结果把王朔的几部小说糅在一起,最后改成了男主人公身有绝症,女主人公知道情况后,双方以泪洗面的大结局——单纯的心理爱情剧,在当年的观众中,似乎还真是无法得到广泛的接受。
这种控制,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双方能接受的程度。“但是没有人是能够长期忍受这种控制的。”她觉得,是自己的控制过于古怪和琐屑,以至于激怒了他。“有一次我们俩去香港,他的女同事喊他带什么东西,口气亲昵了一些,我当场就哭了,要求他把这人的信息都删除掉,并且不能给她带任何东西。”
她的依赖感除了控制,还体现在许多琐事里:“有段时间我处于换工作的间歇,索性整天待家里。他每天上班,走之前要安排好我一天的饮食,早餐做好,放在桌上;我不会做饭,他上班也会为我订餐;晚上下班也是他做。我习惯了这种被安排的生活,我生气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做一桌我喜欢的东西给我吃,怕我继续生气,会叫朋友过来陪,怕我不给他面子,这种被娇宠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是自然的爱情体现;我不想工作,他就会习惯性地向我承诺,他不会让我有经济窘迫的感觉。甚至在没什么额外收入的情况下,也托人从巴黎带回包给我——在我看来,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她还记得,那个包是赛琳(Celine)的新款,在巴黎也不是那么好买到,这个包似乎再一次证明着爱情。
其实这种依赖和控制,已经超越了一般爱情的对等原则。当一方放弃了自我,全身心依靠对方的时候,双方关系一定是有新的平衡和调节,稍有偏差,就会陷入困境。“我依靠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这段感情上,一切都不如我们的感情重要。但是有几个人的感情,能经受这种不断的重压呢?”其实过度依赖有个形象的画面,本来两人是肩并肩地行走,可以突然一人放弃了自己主动的行走,逐渐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另一方身上,这时候,除非另一方能够挺住,否则,就会被这种重量所压垮,到最后走不动。
尽管爱情是很浓烈,但是按照一般的爱情规律,任何爱情都有从峰谷到峰顶再到峰谷的波动,需要双方不断地协调,才能维持在一段水平面上。
“现在想想,我是在测试我们的爱情。看我能折腾到哪一步,看我们的爱情是否能经受考验,我内心是不明白的,非常茫然地做着这一切,以爱情的名目,无尽地索取。”
终于有一天,矛盾爆发了。“我出去旅游,结果发生了通俗电视剧的剧情,当我提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和别的人约会,他反复和我解释,仅仅是喝杯酒,谈了谈心事,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可是在我看来,这种微小的精神出轨,甚至比肉体出轨更加可怕,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是对我们感情的背叛。我在沙发上无声地哭了几天,觉得天塌下来了。在感情上,我是绝对主义者,情商并不高,我还记得自己总是重复昆德拉小说中看来的一句话: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他对我说,过日子不能那么绝对,混混就混过去了,在我看来,这完全属于不负责任的说法。”
再度的依赖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短暂地分开了一段时间。我说我要理清自己:我反复告诉自己,感情这样下去就是绝路,双方没有建设,也就没有结果,我们必须要有可以协调的空间。可是另一个我又跳出来,对我说,爱情就是绝对的,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有时候想想自己都觉得好笑,已经30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极端。”
这时候,有家上海的企业负责人找到了她。这家企业是她喜欢的类型,结果一拍即合。“我没有和他分手,就直接告诉他,我回家休息几天,也确实回家和父母住了一周,一周后我直接去了上海,什么解释都没有,其实也是那时我根本没有能力理清两人的关系。”
这种分开对于他是晴天霹雳。在她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和单位请假,专门来上海看她。“我都没有告诉他,是他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才告诉他说,我不想回来了。结果他的情绪瞬间极其低落。”他在上海见到她的时候,双眼红了又红,说要她照顾好自己,并没有彻底反对她留在上海,现在想想,也许是他的情商比较高的缘故,明知道反对也没有用处。
但是他回到北京后,还是每天都会打冗长的电话来倾诉。“告诉我,从我离开后,花瓶里的花都萎谢了,他也舍不得换掉;衣柜里大量的我的衣物,他也舍不得寄到上海来。他始终在等我回去。”
那家企业是她喜欢的类型,而且也不便于立刻离开,因为那意味着对对方的不负责任。“我们开始了两地奔波的过程,我后来说,每月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交通费上。朋友说我‘作’,在上海话里,这个‘作’有很多解释,最重的是谴责,就是不好好过日子。我反思我自己,是没有好好过吗?我依恋感情有错吗?结果还是不忍心责怪自己,只是一味责怪他,谁让他不够爱我,才有那种精神出轨。”
“在上海工作一年后,他的坚持不懈的柔软,终于又让我感动了。我决定回归北京,因为意识到自己还是最爱他,而这个前提是,他真的是我一生中要依靠的那个人,在我的认知系统中,始终存在两个原始命题:一是爱情对于我最重要;二是找到爱情后我会放弃一切。哪怕在北京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我也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他是公务员,也没有调动工作的本事,所以我决定还是放下工作,回到他的身边,重新开始两人的新关系。”
这次回归,事后证明对于两人的关系改善,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她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她还是把生活重心放在两人关系上,她告诉我,因为当时的心态是,这辈子就是他了,所以对两人关系放肆而无忌讳,两个人都没有深刻反思,这种一方过度依赖的关系需要调整。
按照成熟的心理学界的观点,索取和付出一定是对等的,没有无穷尽的索取,可是在他们的关系上,她真的扮演了索取方。“我并不是不知道满足。可是内心里的无助感会肆意泛滥,我没有在两人的关系上添砖加瓦,而是习惯性扮演弱者。”
她还记得,自己经常性地翻看对方手机。现在反思,那是自己的暗黑心态在作怪。“其实双方在感情关系中,没有信任就没有发展的基础;我不是不信任他,还是老话,我在赌博,到底我们的感情能走到哪一步。”终于在一次看与被看的争吵中,他把自己崭新的苹果手机摔得粉碎,那一刻后,她心里惊跳了一下,原来他并不是无理由地迁就她。“爱情是有限度的,这个道理我绝对明白,可是我总觉得我和他的爱是例外,恨不得是遗世独立的爱情,比别人的都伟大,都好,都可以永存。”
可是那一地的苹果手机碎渣似乎是一种真相,让她明白自己也不能例外。
遗憾的是,在那个阶段,她没有修正自己的能力,越是害怕爱情的消失,抓得反而越紧。“我也看‘心灵鸡汤’,许多‘鸡汤’都说,爱情就像一把沙子,握在手中,你越抓得紧,沙子流失得越快,我也知道两个人的相处,需要彼此的尊重和善意,可是就是纠正不了,在我看来,爱是无穷大的,在爱的系统里,什么都得让步。这种理论,最初他也是赞许的,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中,这个其实是无法实现的,爱情永远有退让,有将就和苟且,这才是人生。”
她持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对付世界,对付他。“比如我很讨厌一些人和一些价值观,他如果不同意我,我就非常生气。比如他去和外面公司的人应酬,我就很生气,在我的系统里,这种应酬是没有意义的。”
不仅仅要求爱情的纯度,她也在蓄意制造生活的纯度。她不是懂得妥协的人。
终于在两个人认识四年的时候,毫无预兆的,或者说,一步步走到那里的,他向她宣布,他已经无法承受她的爱,他们还是分开吧。
当然又是一番哭泣,包括哭泣着拥抱,哭泣着摔东西,哭泣着离开家门。
在她的信念里,从没有觉得这辈子会与他彻底分开,尤其是有那次短暂分手继而复合的经历,使她进一步确认,他们不会就此失去联系。确实,在分手后,她每天电话他,两个人在电话里争吵、指责,有时候又是短暂的柔情蜜意。两人有阵子对话基本如下:“你还爱我吗?”“目前不爱。”“曾经呢?”“很爱。”“以后还会爱吗?”“不知道。”
现在分析,其实那是两人分开的短暂不应期。她觉得,还能失而复得,因为她过于相信这爱情的与众不同;而他,在逐渐走出这段感情,在他看来,这段感情结束后,理所当然应该开始下一段感情。她给我看他们的照片,他英俊、沉稳,有他的吸引力,在分手后很自然能吸引到新的人的喜欢。
这种暧昧的电话持续了几乎半年的时间,两个人只是不再住在一起,有时候也吃饭,也逛街,甚至也会拉手,她继续勉强他拥抱她,有时候在半夜寒冷的街头,她也会习惯性地把身体靠在他身上,恍惚产生错觉,就是两人并没有分手。但是再没有外出旅游,没有彻底的亲密关系——“我太依靠他了,以至于觉得,只要我努力,他就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
直到他身边出现了新人,她还是抱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在一起散步啊,吃饭啊,看电影啊,他并不是每天和她在一起,他告诉我,不是每段感情,都需要那么撕心裂肺。这时候,我还在侥幸,觉得他会回来,其实他只是怜惜我而已。”
终于,一次约他不出来,二次约不出来,她发现,他不再是她的了。过去她在街头一跺脚,他就会过来哄她,现在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有她在原地,孤独地行走。“我才明白,世界上真没有命中注定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些东西,失去了,那就永远失去了。”
她从手机里删除他的号码。强迫自己忘记他的一切联系方式。最后也终于做到了。
她是靠阅读心理学著作解决自己问题的。“我看的是认知心理学体系的书籍。”其实在人的世界里,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就像古希腊谚语说的那样。“我不知道在感情关系中,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我觉得爱是笼统的,不需要分类,也不需要维护,爱的名义下可以做一切事情。所以我就为所欲为了。”
“你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观。”我终于忍不住提出批评。
“确实是。我自己也觉得羞愧,怎么30多岁的人,情商那么低,完全不具备理解爱情的能力,我后来看书才认识到,我是始终在寻找安全感的人,可能源自于我在小城市长大,我们家又属于后搬去小城的,缺乏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所以特别没有安全感。当我长大后,努力在亲密关系中制造安全感,而且我把亲密关系局限于爱情关系——我朋友不多,能够交心的好友更少,他事实上担当了朋友、亲人和爱人三位一体的角色。”
她到现在才意识到,安全感只能自己建立,不能别人给予;过度依赖只能让被依赖方厌倦,除非他是奇人,足够强大,以女人的依赖为乐;而爱情也只是爱情,它是有机体,有生长也有削减,不存在永恒的爱,至少在现实中,那种永恒的高纯度的爱比较少见。
“我想想我是不是‘作’,不是,那个阶段我只能如此,我做不到掩饰自己。”
分手后有次看卡佛的一篇小说,里面离婚的男女再次见面,女的对男人说:我以为我们不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一辈子会在一起,可是,我们还是分开了。“我就一直在想,我和他再次见面,会怎么样?会说什么话?后来想想,还是不见面的好,至少在没有彻底放下他之前,不需要见面,只会让我显得难堪。”
我想起了海明威小说《太阳照旧升起》结尾的话,这么想想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拿出来劝她,似乎再好没有。不过她似乎已经不需要劝慰,从那段关系中走出来的她,恢复了自信和骄傲,一个自信的女人,始终是不会缺乏爱情的。
(文章的主人公希望隐去自己的姓名) 依赖爱情婚姻情感恋爱两性女性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