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农村选择了我
作者:孙若茜(文 / 孙若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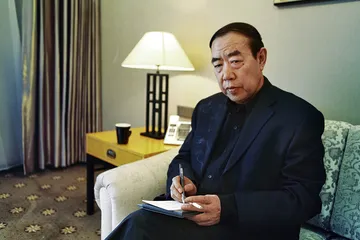 ( 贾平凹 )
( 贾平凹 )
2012年8月14日,60岁的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带灯》的后记里写道:“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今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发行《带灯》,本刊记者就此书专访了贾平凹。
内容的隐喻
三联生活周刊:首先在编排形式上,和以往不太一样,书里有极多带框的小标题,且并不是作为故事节点的划分,我从责编那儿了解到,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为什么这样设计?
贾平凹: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围绕一个人物展开,以她的视角来看乡镇日常事务,这样写容易在结构上单一。我多加点东西把故事铺展开来,给人感觉不是单纯地写一个线索,可以把对生活的一些领悟或者一些别的事情渗透在小段里。且一段一段进行,是有形式感的,好阅读。为啥加这个小框子?它是启示性的。
 ( 《带灯》 )
( 《带灯》 )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跟《圣经》有一些关联?
贾平凹:《圣经》也是这种分法。中国人原来写小说的分法,一个内容或者一段给上几个字才开始,或者一个标题下有一个内容或一个故事。《圣经》就不是,它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也分小节,你说它是随着时间顺序,它不是,挑出一个故事,它也不是,反正是随心所欲的,到那儿它就停下来。它可以同时涉及好多东西,你如果不分这小节,好多东西塞不进去。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有大量的隐喻,比如虱子,比如主人公的名字,比如你说天气就是天意。
贾平凹:除了故事线索,增加了好多生活中一些领悟的东西,那些小哲理倒不是从别人那儿借鉴的,而是完全从生活中获得的。
人生虱子是指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带来另外的好多副作用,像华阳镇,矿区虽然发财了,经济发展上去了,而地面坍塌,带来环境污染和不好的影响啊。上一辈人不让高速公路进村,要保住风水,但是保住风水后,这个地方又特别贫困。然后到下一辈,元天亮帮忙引进一个大工厂,引进大工厂后飞来了虱子,隐喻着可能这地方将来也被污染,被破坏,生态被破坏变成残山剩水。
三联生活周刊:虱子毕竟成了习惯,如果没了虱子,人还会怀念虱子在身上的感觉。
贾平凹:虱子毕竟代表一个落后的东西,不卫生的东西,或者污染的东西。带灯和竹子,一直抗拒,不让身上生虱子,到后来她也还是生上虱子了。因为在这种环境里,你没有办法清高,你和上访者打交道,最后必然要有些扭曲,整天干这个工作,自己也把自己异化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刚好和带灯原来的名字“萤”的隐喻“萤虫生腐草”契合了。
贾平凹:她的生活环境确实是很恶劣的那种,她在这种环境中不是靠自己来拯救什么,起码她最少不让社会污染,保持自己的一个纯洁。但是她毕竟是个萤火虫,发出的光毕竟是微弱的,而且必然走向一个悲剧的命运。
三联生活周刊:除此之外,书里也提到萤火虫的另一种含义。
贾平凹:因为萤火虫还有一个习性,就是它进攻蜗牛,有它残暴的一面。萤火虫是以蜗牛为食的,它附着在上面,开始给蜗牛抚摸抚摸,然后把刺扎到蜗牛身上,就吸取它的营养。这体现在她跟上访者打交道时,有同情心,也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手段,不这样就无法完成工作。她就像那萤火虫,她说咱们和上访的人纠缠,其实咱们也是一样,啥人治啥人,一个事情的两面,咱们是其中一面。任何事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是谁都离不开谁,要是人家不上访,咱就没饭吃了。
三联生活周刊:设置隐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么?
贾平凹:里面全是对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一些想法。文学有很多种写法,有些作家喜欢写激烈的、明显的、尖锐的,还有刺激性的,我的写作喜欢任何东西都隐起来、藏起来,藏起来的这种写法是让文学的味道更能长远些,有回味的东西,不是一见面就给你刺激,过后就没有了。文字之后隐藏了好多东西,供每一个读者做思考,你怎么想都可以。
叙事的直白
三联生活周刊:把内容的意味藏起来,但是叙事上力求直白。
贾平凹:在叙事上,尤其是带灯的工作上我就不跟你胡绕了,就直接是解决问题的,发生啥事情,披露就披露,需要批判的,丑陋的东西就直接拿出来。因为能上访的都是一些丑陋的事情,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中国的各个方面,政策方面,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贪污问题,或者人性里暴露的恶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叙事去掉修饰,语言风格也就跟着有了变化。
贾平凹:其实就是学两汉,两汉是史实的笔法,没更多装饰的东西,就直接写事件,它不需要那些技巧、修饰,只有给元天亮的信是小资情调,文艺青年那一套,爱情信嘛。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的作品都是靠细节推进,这次依然有一些相似的处理?
贾平凹:叙事过程中还是用《古炉》、《秦腔》的办法,只是去了好多修饰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故事贯穿下来的,不是一个案件,是不停地有各种不同的事情。这是乡镇的日常工作,今天出现这个问题,明天出现那个问题,一会儿计划生育,一会儿救灾,这一系列繁琐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之下,故事和情节对你来说不太重要?
贾平凹:对,我起码不是那么做的,里面没有一个主故事,我主张写的东西一定是要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一切都是来自大地上,而不是编出来的东西。情节太完整吧,我觉得都不真实了。在一个传统叙事里,《红楼梦》,包括《金瓶梅》,它都是日常琐事,你觉得更真实,如果你的故事太圆满,一看就是编的,编的故事就不是生活中真正来的一些东西。
现代意识
三联生活周刊:语言、叙事上的改变和心理上的变化,哪个是你更想得到的?
贾平凹:中国呈现出这么多的事情,它是有特点的。外国人他不理解,上访和压制上访,外国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在中国会导致这些东西,完全是文化起作用的,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下面人和人的关系。人的思维定式不一样,为一个小事情就可以上访跑20年;政府为了面子,就是半路要截你,这种思维都是一种文化思维。
出现这种东西,我一定要选择符合中国文化、中国人思维的东西,把握住以后就能写出中国目前出现的困境,这样在困境中走出来,用什么担当,用什么举措,解决好了或者解决不好,都可以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经验。
我在写《带灯》时有这种意识,这次写作过程中,我想为什么中国危机这么多,如果用一种“左”的观念就是改革开放不好,如果用“右”的观念,就是体制不好,这两种极端的否定或极端的维护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下面产生这种东西,我把这呈现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而不是我想当什么斗士,或者我想维护旧的东西,我觉得,不研究文化,就达不到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形式上的,要在写法上突破一点点也确实难,难得很,难得要命。
三联生活周刊:那就是现在经常谈到的现代意识吧?
贾平凹:经常在下面跑,好多问题看得你惊心动魄,忧心忡忡。永远在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的圈子里,你觉得永远都是盛世,啥都好。当然也会有好多苦恼,但你觉得国家没事儿。到下面跑就觉得这样下去危险得很,就人心惶惶。用带灯的话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但文学也只能呈现问题,然后让大家关注,思考,不糊里糊涂,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对了,不可能改变什么东西,也回答不了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的带灯遇到、解决过几乎所有形态的问题。
贾平凹:我当时写的虽然是带灯,但实际上写的是乡镇,最基层政府。在我心中,中国的基层都是这样子,它里面牵扯到乡镇里的明争暗斗,以及招商引资的一些情况,环境污染问题,群众和干部的矛盾问题,政府人员和基层群众的矛盾,这里面都在渗透,包括选举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一部分人富起来后怎么掠夺资源的问题,实际上一个乡镇也是大众的小小缩影,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带灯解决过所有的问题,你要把这个小镇扩大成中国,也就是中国的形态。
三联生活周刊: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是对乡镇的另一层了解,所以你会在“后记”里说自己现在除了供地藏菩萨外,又请了个土地神回来,这也是隐喻吧?
贾平凹:在我心目中,乡镇干部是土地爷土地婆,就是管一方的土地。在咱心目中,土地神冒一股白烟出来,小老头或者小老太太,管着吃喝拉撒睡。他是神里面最小的一个,但他是与老百姓最近的一个,老百姓才敬他。
乡镇干部跟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摩擦也最多,给他解决问题的是这些人,得罪他的也是这些人。世上的事情,大官安然无事,到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就牺牲掉了。面对老百姓来做事情,容易产生的社会积怨都积到他身上,对政府的不满全部都发泄到他身上。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带灯的悲剧。
贾平凹:所以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带灯说她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佛桌前,佛是庄重的东西,她作为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国家做事,执行的是很神圣的使命。但虽然在佛桌前,火焰往上升,泪往下流,就是表示她的处境。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给带灯一些所谓的小资色彩,人物原型就是这样么?
贾平凹:没有这样一个原型,我不敢这样处理,这样就会觉得不真实。一般人觉得乡镇干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读书,一天就是喝酒,在下面训斥老百姓,然后干些工作。但是接触带灯的原型确实是那样一个人,她长得没有多漂亮,但特别智慧,特别聪明,她没有多少学历,周围没有文学圈子,也没读多少书,完全是天生的,她是没受污染的一个人,特别单纯,脑子反应特别快。乡镇干部是包几个村庄,山区的村庄都远得很,她一般出门几十里路,一个包里装几瓶矿泉水,到镇上买两个粽子,背上就走了,天黑才回来,中午累了就趴在山坡草窝里睡上一觉,这是真实的。然后在那儿看书,有时没事儿就一看一天。她看不上周围的那些小干事,就知道想办法在那儿捞些钱喝些酒,她一般不弄那个。她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一般,但她能力强,上访的人经常胡搅蛮缠,要把他们治住,她有各种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她的智慧在书里都体现了,但是书里的带灯特别漂亮,这是为了让角色更理想化吗,更显出她的悲剧性?
贾平凹:她代表一种悲剧,把她毁灭掉就更能启示大家对环境的理解。真像一朵花开在牛粪上,有营养,但就是臭烘烘的环境里长一朵花,那个花自生自灭,没人欣赏它,自己就枯萎了。我经常到山区去,看到野地里突然有朵花,不像公园里的花也不像家里培植的花,它完全是野性的,不加修饰的,但是特别艳,你能感觉那种气息,开在山里也没人看,它完全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完全是它生命需要,需要开就开,需要落就落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才可能写那么多信。
三联生活周刊:从信里能特别清晰地看到她的命运走向。
贾平凹:对对对,完全是为了塑造人而安排,如果让元天亮出场,带灯的丈夫也出场,那就成另一部爱情小说,而不是现在的这部。重点不是说她的爱情,但是生活中必须得有爱情,她也向往这个东西,理想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是农村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农村题材?
贾平凹: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中国农村目前出现这种东西,你总想解决这个东西。我关注我现在的处境,解决我目前的问题,然后跟着中国大部分人走,我也不能离得太远。但是怎么跟,怎么跑?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它解决了啥问题?将来给人家提供它的一份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书的“后记”,你说自己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为什么说“必须”?
贾平凹:那个时期看了好多《山海经》的注本,我都不满意,最多从文字上,比如说这个字代表着啥东西,这个字代表古时候的一种鸟啊或者树的名,历代都是这样注释。但是我看完后,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最早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山海经》来的。看这个没有任何修饰的东西,没有任何华丽的东西,完全是当时的人对外界的一种看法。比如里面有一种树长着三面脸,动物吃了后能长寿,拿现在说,有三副面孔,见领导是这种面孔,见女朋友是那种面孔,见下面人又是一种面孔,你活得很自在。为啥说长寿呢?它活得时间长,就是活动余地更大一点。这完全是按照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建立的信息和思维系统,如果照着这个思维解释《山海经》,要说的话多得很。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是想追根溯源?
贾平凹:是追根溯源,《离骚》就是很悲愤的,《山海经》是很本源的东西,你到老了就不要装饰的东西了,不要那些虚幻的东西了,就要那些很本真的东西,我是从本源的方面说的。
(感谢实习生甄紫涵整理采访录音) 文学贾平凹选择农村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