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抗震救灾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3月13日,一位岩手县居民正在仔细查看幸存者信息 )
( 3月13日,一位岩手县居民正在仔细查看幸存者信息 )
3月11日下午,我从网上得知日本东部海域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当晚便接到通知准备去现场采访。朋友介绍了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曾梅(化名),她答应帮忙。当天夜里传来不好的消息,东京成田机场已经关闭,新干线和东京市区几乎所有的轨道交通全部停驶,通往东北方向的高速公路也被关闭。
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传来好消息,成田机场已开。上午9点半左右,我登上了飞往东京的CA925次航班。
震多了不愁
飞机全满。我身边是一位日本华侨,已经在日本生活了20年。“日本学校的防震教育做得好,我所有关于地震的知识都是我女儿教给我的。”这位女士对我说,“比如,地震发生时一定先把房门打开,因为地震会导致门窗变形,打不开门就没办法逃生了。”
她还告诉我,日本所有出租的房子都必须备有自救包,里面有锤子、铲子等挖掘工具,以便被埋时能够自救。“不过后来我自己买了房子,就没准备自救包了。来日本这么多年,经常遇到地震,都习惯了。”
 ( 3月13日,家住日本福岛的这位居民开始清理被海啸冲毁的家园 )
( 3月13日,家住日本福岛的这位居民开始清理被海啸冲毁的家园 )
日本时间14点左右,飞机顺利地降落在成田机场。一出舱门就看到从天花板上震下来的灰渣,还留在走廊的地毯上没有清理,候机室里仍有不少游客滞留,地板上还铺着很多睡袋,从样式上看是机场统一发的。但是,整个候机室相当安静,秩序井然,人们的表情也很镇定,看不出任何惊慌的神色。
今天还敢飞往东京的外国人大概全都是记者,与我同机到达的还有一位土耳其某电视台驻北京记者,被临时安排到日本采访。“我不知道总部为什么派我来,现场视频网上多得是。”他自嘲地说,“第一个告诉我地震消息的是我妈妈,她从土耳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安全!”
 ( 3月12日,东京羽田
机场大厅被困的旅客 )
( 3月12日,东京羽田
机场大厅被困的旅客 )
到日本的第一件事肯定是租手机。我在租手机处遇到3个《华盛顿邮报》派来的记者,因为缺乏交通工具,正焦急地打电话四处求援。“我们的美国驾照没法用,而且机场所有的出租车全都租出去了。”一位记者对我说,“刚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答应送我们去仙台,张口开价2000美元,还不敢保证送到。实在不行,我们只能租直升机了。”
说话间,我突然感到地板左右摇晃了起来。那个美国记者也停止了说话,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大家一脸惊慌。但我朝四周一看,发现周围的人全都像没事一样,好似这次余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 3月12日,日本佐世保军港内的美军“托尔图加号”登陆舰前往灾区实施救援 )
( 3月12日,日本佐世保军港内的美军“托尔图加号”登陆舰前往灾区实施救援 )
一部分机场快轨已开,我顺利地搭上16点发车的JR线电车驶往东京和曾梅相会。车厢非常拥挤,一位在成田机场工作的国航工作人员向我描绘了地震时的情景:“地震一开始我就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周围的日本人也这样,没人往外跑,大家都相信房子不会倒。这次地震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摇晃得非常厉害,我估计至少有6级。不过,我感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严重,超市里也没有发生哄抢,生活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一个多小时后,电车到达东京。我采访过汶川和海地的地震,以及印尼海啸,养成了“找不同”的习惯。这次日本大地震虽说震级很高,但我一点也看不出东京和平时有任何不同,房屋全部完好,街上秩序井然,昨晚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步行回家的人大概都已经安全到家了吧。
 ( 3月12日,日本仙台市部分居民聚集在一所小学的屋顶等待救援 )
( 3月12日,日本仙台市部分居民聚集在一所小学的屋顶等待救援 )
曾梅和她的日本丈夫中岛(化名)租了一辆小车来接我。中岛今年40岁,是日本一家著名电器公司的工程师,不会说中文。“他是个典型的日本男人,固执但做事精细,什么事情都要先订好详细的计划再动手做,所以他对你坚持要去仙台感到非常不解。”曾梅说。
果然,中岛拿出一个iPhone,给我看上面显示的公路地图。“新干线和通往东北方向的高速公路仍然关闭,普通公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预计从东京开到仙台需要2~3天的时间,所以是行不通的。”他说。
 ( 3月12日,日本自卫队直升机在岩手县灾区救出受困的居民 )
( 3月12日,日本自卫队直升机在岩手县灾区救出受困的居民 )
我向他解释了记者工作的特殊性,希望他破例冒一次险,先开到海边,然后沿着海岸线向北开,能开到哪里算哪里。他沉默了许久,又拿出iPhone研究了半天,然后突然说:“那我们今晚不住东京了,立刻出发向北开,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上了车我才发现,他俩什么换洗衣服都没有带。“他就是这样,虽然有点一根筋,但一旦想通了就雷厉风行。”曾梅笑着说。
 ( 3月12日,孟加拉达卡大学校园内,学生们手持蜡烛为日本受灾民众祈福 )
( 3月12日,孟加拉达卡大学校园内,学生们手持蜡烛为日本受灾民众祈福 )
中岛打开收音机和卫星定位系统(GPS),迅速输入地址,我们一行三人在夜色中向北方驶去。没开多久就遇到了堵车,几乎完全开不动。中岛立刻在GPS上按了几下,然后迅速调转车头驶入一条小道,果然快多了。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又堵上了,这次中岛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线路,只能跟在后面缓慢地向前挪。
“这个人是赶回东北老家探亲的。”中岛指着前方的车牌对我说,“我估计很多人都这么打算,所以才会这么堵。”他又指着对面开过来的一辆出租车说,“这辆车挂东京牌照,但车里没人,肯定是送记者去前方采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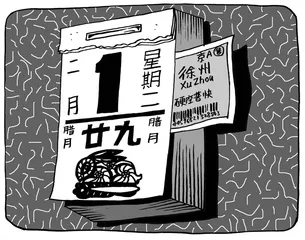 ( 3月13日,美国菲尼克斯春季棒球比赛前,球员们悼念日本地震遇难者 )
( 3月13日,美国菲尼克斯春季棒球比赛前,球员们悼念日本地震遇难者 )
说话间车子经过一家卡拉OK厅,我看到里面挤满了人,中岛再次为我做出了解释:“很多日本人住在距离东京5~60公里远的卫星城,平时坐电车去东京上班,电车一停,大家就都回不了家了,只好住旅馆。这次地震比较严重,旅馆全满,大家只好住卡拉OK厅,而这些公共场所也都对此有所准备。”
“高速公路为什么关闭呢?看上去没坏啊?”我问。
 ( 日本首相菅直人称此次地震是日本“二战后遭遇的最严重灾难” )
( 日本首相菅直人称此次地震是日本“二战后遭遇的最严重灾难” )
“高速公路有很多地段都是高架路,虽说应该损坏不大,但为了保险起见,需要检修后才能通行,而且可能也是为救援车辆留一个快速通道。”中岛解释说。
“他们日本人从小就在地震中生活,对这种情况真的是很习惯了。我老公不是研究地震的,可相关知识特别丰富。”曾梅对我讲述了昨天地震的情况:“我来日本3年,经历过很多地震,以前每次地震后我总是习惯给老公发短信开个玩笑,昨天地震不一样,摇晃得很厉害,而且时间很长。还在晃的时候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告诉我赶紧躲到浴室里去,不要上街,因为有可能被电线杆或者广告牌砸到,家里最安全。然后他又立刻给我在国内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电话刚打完就断了,直到夜里才又重新开通。”
“我预感到这次地震震级很高,通信线路有可能中断,就赶紧给她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否则就没机会了。”中岛平静地说。
“你凭什么知道这次地震震级很高呢?”我问。
“这次地震一开始的上下震动时间很短,也很轻微,此后就是幅度很大的左右摇晃,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说明震级很高,但震中距离东京很远。相比之下,1995年那次阪神大地震虽然震动的时间不长,但上下震动非常剧烈,说明震中就在脚底下,距离城市很近,所以那次地震造成了大量房屋倒塌,但这次就没有。”
接着,中岛给我普及了一下地震知识。地震波分为纵向(上下)和横向(水平)两种震动,前者传播速度快,对建筑物破坏程度大,但衰减得也快,后者则正相反。他正是根据两种震动的时间和强度的对比判断出这次大地震的基本情况,并根据以往的经验迅速做出了反应,事后证明他的判断基本正确。
正聊着,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声清脆的鸣叫,接着一名播音员插播了一条新闻,曾梅平静地对我说:“这就是预警,马上将有一次余震。”此时我们的汽车正好被堵得停在一座桥上,几秒钟后,车身果然开始摇晃起来。“真准啊!”我赞道,同时却立刻感到这事有点奇怪,因为他俩并没有因这次预警而立刻跳出车子逃命。
“现在余震多,这种预警每天都有好几次。”中岛解释说,“一部分日本手机机型也有这种服务,不过我没买,觉得没用,因为这种预警的准确性只有20%左右。我更愿把宝押在建筑物的防震性能上。”
据他说,日本在1981年通过了建筑法,要求东京市的新建建筑必须能抗9.5级地震,所以一般地震他是不怕的。“不过,政府之所以制定这个法律也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因为建筑标准提升了,政府就可以增加税收,从开发商那里赚到更多的钱。”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我租来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我拿出一看,上面写着一个英文单词:Earthquake(地震)。可是,这次我们却没有感到摇晃。“也许这次的震中距离我们有点远。”中岛说。
我突然想到,我的手机对一小时前发生的那次有感地震并没有做出反应,看来这个预警系统并不是很可靠。
“地震预警是利用地震波和电磁波传播速度的差异做出来的,因此距离震中越远,预警的提前量越长。”中岛说,“可是,距离震中越远,破坏性也就越小,预警也就越没用,这也是我不觉得这个系统有多么重要的原因之一。”
“看来你对日本政府的很多做法不满啊。”我说。
“是的,我觉得政府做得很不够,遇到地震日本人只能自救。”
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不买地震保险的原因:“因为大城市的新建建筑大都很可靠,所以一般小震真震不坏,如果真遇到那种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所有保险公司就都会破产,所以东京人很少买地震保险。”
俗话说,债多了不愁,看来日本人是震多了不愁啊。不过,通过和中岛先生的对话,我发觉我以前听到的很多关于日本抗震的消息都不够准确,很多措施的背后都另有隐情。
此时已近午夜,我们决定在路边找个旅馆休息。中岛拿出手机搜索附近的旅馆,一连打了将近10个电话,回答都是客满。好不容易在土浦市内发现了一个旅馆有空房间,我们便离开公路,开进了土浦市区。这里距离东京有70多公里,距离海边尚有50多公里,市区内仍然有电,但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我们找到一家7-11便利商店,打算买齐明天需要的水和食品。超市里面大部分货品都全,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品也有不少,只是面包和饭团这类即食食品不见了。“地震后肯定有人抢购食品,但缺货更主要的原因是交通中断,新鲜食品供应不上。”曾梅解释说。
日本的旅馆按人头付费,每人3000日元。“我们的原价是7000日元,但今晚我们限制供应水电,不能洗澡,也没有空调。而且因为人手不够,房间没有打扫,所以只收半价,对不起。”服务员抱歉地说。
“没咖啡了。”一位顾客走过来提醒服务员,他立刻鞠躬致歉,然后一溜小跑地过去给前厅里提供的免费咖啡加水。
我的房间很小,但所有设备一应俱全。虽然有点冷,但床上铺着厚厚的毯子,毯子并没有按照标准的方式叠好,但非常干净。打开电视,正在播放直升机拍摄的海啸场面,只见渔船和小汽车像玩具一样被海水席卷着冲向桥梁和房屋,人们在房顶上大声求救。很快,画面切换到了民众自发拍摄的海啸录像,那场景比任何一个专业记者拍出来的都要震撼得多。
此时已是夜里2点,我很快就在直升机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梦乡。
防不胜防的海啸
我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吃罢早饭我们立即出发,并打算在出城前加满油,可好几家加油站都关门了。“紧急时期往往只有少数加油站开门,集中供油,互联网上会有详细的信息。”中岛说。
还没等他用iPhone上网查询,就见到了一家开门的加油站。油价几乎没变,普通汽油仍然是154日元/升。排队加油的汽车排出去几十米,大家情绪镇定,没有一人抱怨,更别说加塞了。
加满油,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线路直奔海边。一路上仍然看不到多少地震的痕迹,所有建筑都完好无损,只有几面矮墙被震倒了,还有一些老式房屋的瓦片掉了下来。大约开了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大海。车子向左一拐,开上了沿海公路,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路边的树墙上挂着一辆小汽车,一根红绿灯架倒了下来,横压在路面上。灾难,几乎是在一瞬间跳进了我的视界。
这是一片浅滩,沿着海边种了好几排松树,但显然没有挡住滔滔洪水。居民区距离海边尚有1公里远,但仍然是一片狼藉。我看到一户人家正在清理院子里的沙土,便过去询问是否可以问几个问题。老伯伯放下手里的铁锹,简单地向我描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原来,这个村子名叫大洗村,地震发生后村民们立刻接到了海啸预警,便跑到附近一座小山上避难。此后发生了两次海啸,第二次海啸的海水高度超过了4米,把一层的房间全淹了。但因为跑得快,全村没有一人遇难。
老伯伯语速平缓,表情镇定,似乎只是在描述一次小事故,一点没有看出惊慌的神情。在征得全家人允许后,我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我们拍完照并致谢后便迅速告退,继续向北方前进。
又走了一段,眼前出现了一个海港,几个巨大的集装箱被海水冲到了距离海岸线足有1公里的路边,可以想象海水倒灌时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不过,在这个全民皆拍的时代,海啸发生时的全过程早已被电视和网络视频传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客厅里,文字的力量在此时显得格外无力。
我下了车,徒步走到港口,两艘十几吨重的渔船叠加着搁浅在岸上,一位外国记者正在拍照,一个渔民模样的人骑着自行车绕着渔船转了几圈。“我猜这艘船的主人很可能得自杀。”中岛悄悄对我说,“渔船都是渔民租来的,他们赔不起。”
不远处,一群渔民正在修补被损坏的渔网。我们开车过去,打算找几个人问问情况。车子刚刚驶近,一位渔民拦住去路:“一边去!”他用了一个有点无礼的词,仅次于“滚开”。
我们知趣地立刻掉头走开,继续向北行驶。这一带沿海的房屋很多,凡是海拔低的房子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家具和各种杂物散落在地上,不少人家的主人正在打扫屋子,没看到任何志愿者,更别说军人了。事实上,因为这里的受灾情况和北边的宫城县相比算是轻的,因此我们一路上几乎没有见到任何救援车辆,只有几个专业人员在测量道路和桥梁的损坏状况。这一点和汶川地震后那种全民动员抗震救灾的情景很不一样。
又开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了福岛县,该县最大的港口小民浜海港也是一片狼藉。这是日本东部的一座重要港口,可以看到堆成小山一样的煤,以及巨大的储油罐。港口边上就是一家大型化工厂,可以闻到轻微的化学品味道。从受灾情况看,这座海港短时间内是无法恢复的,不难想象,这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肯定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灾区的电力供应全部停止了,大部分商店都已关门,红绿灯也停止了工作,全靠司机们互相礼让。大家都很守规矩,每一位被让的司机都会礼貌地冲对面的司机挥挥手,再点下头表示谢意。
路上看到一家便利店还在营业,几十名顾客在门口排了一条长队。过去一看,原来售货员在用计算器计价,怕算不过来,所以每次只放5个人进去。
我们又往北开了3个多小时,沿途的景象大同小异,凡是靠近海边,海拔又低于5米的房屋全都遭了殃,无一例外。不少海岸线上建有各种形状的防波堤,但对于这样百年一遇的海啸全都不起作用,受灾情况没有任何区别。14点左右我们开到了位于茨城北边的一个海滨度假村,一幢幢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隐藏在树林里,可以想象受灾前一定是人人羡慕的海滨别墅。可在海啸面前,贫富差别被重新定义,原来价格高昂的房产一片狼藉,原本因为远离海边而价格低廉的房产却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幸免于难,主人肯定大呼万幸。
考虑到截稿日期临近,我决定往回走,这次就不去仙台了。
人定胜天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幢完全损坏的房屋。沿途没有一幢房屋直接因为地震而倒塌,海啸虽然淹没了所有沿海的房子,但大概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海啸不够强的缘故,所有受灾房屋都是只坏不倒,估计修一修还能使用。中岛告诉我,日本乡村居民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哪幢房子是谁盖的大家都知道,因此没人敢马虎,一旦偷工减料被人发现,一辈子的名声就毁了。
但是,就在距离度假村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我看到了第一幢彻底倒塌的房子。这是一处夹在两个山包之间的小村子,名叫富神崎,只有十几户人家。在台风频繁的日本东海岸,这里原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为了防止滑坡,两边的山坡都用水泥糊住了,看上去好似铜墙铁壁。沿海的一侧也修了一排防波堤,足有3米高。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这次百年一遇的大海啸,相反,两座小山包反而让海水聚集了能量,把坐落在山谷里的富神崎村变成了海水展示力量的舞台,其结果就是整个小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面朝大海的几幢房子全部倒塌,状况惨烈。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联想到关于日本防震能力的种种神话。确实,日本可称为是全世界抗震能力最强的国家,同样级别的地震,在日本造成的损坏肯定要比我国小很多。但是,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能防得了这次大地震造成的海啸。由此可见,起码从目前的情况看,所谓人定胜天是很难做到的,人类社会远没有达到能抵抗一切自然灾害的时代,无论怎样预防,大自然都会想出办法给你一个意外。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地震还算是容易防的,只要愿意花钱把房子盖结实了就行了。海啸怎么防呢?总不能沿着海岸线建一排10米高的围墙吧?那样的话估计就没人愿意住在海边了,谁愿意一开门就看到一堵墙呢?而且,如果再来一次高于10米的海啸呢?谁也不敢打保票说这不会发生。
换句话说,任何预防灾害的办法都是有成本的,人类社会也远没有达到不计成本防止一切灾害的时代。
“日本在防灾方面也是分等级的,首先要防的是地震,其次是雷击和火灾,海啸得排在第四位了。”中岛对我说,“日本发生过那么多次地震,没有一次引发了这么大的海啸,像这样严重的海啸在日本近代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我们没有经验。”
那么,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就只能束手就擒吗?显然不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害呢?我在高萩市找到了答案。我们开车经过高萩市市政府的时候,正好看到一群人在排队。下车一看,原来是在排队领水。这里完全断电断水,日本自卫队和红十字会专门从外省运来饮用水,每天24小时供应。排队领水的高萩市居民大约有100多人,在市府门前的小广场自觉地排了3圈。为了方便刚到的市民找到自己的位置,专门有人站在队尾,高举一块牌子,上写“最后尾”。
这个广场的一侧有幢两层小楼,据说是市政府的办公大楼。整个楼虽然没倒,但墙体发生了严重的损坏,是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建筑物。
现场有一个高萩市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我找到了这个指挥部的总负责人,请求采访。这位戴着眼镜,身穿工作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礼貌地对我说:“我现在很忙,不便采访。”然后冲我抱歉地点一点头,继续回去工作了。
我还注意到,排队的市民表情平静,没有任何人在大声喧哗,现场安静得出奇。
所有这一切,都和汶川地震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在另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开车来到高萩市立中学,该校体育馆是高萩市最大的地震避难所。校长把我们领到体育馆里就告辞回去工作了。我看到馆里有几十人在避难,孩子们在聊天,老人们在唠家常,人人表情平静,看不出一丝异样。
“地震发生后我们立刻就开门了,最多时这里住了将近1000人。现在大部分人都回家收拾屋子了,晚上再来这里睡觉,因为我们免费提供饮水和食品。”在现场负责管理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这座体育馆是30多年前建的,是全市最结实的建筑物。学校里一直备有应急物资,比如毯子和睡袋等等,今天正好派上用场。”
我还注意到,避难所的厕所前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大便方法”。原来,因为停水,学校把游泳池的水运到这里,在小黑板上写下使用方法,教市民们如何自己舀水冲洗厕所。
恰在此时,两位政府工作人员来检查房屋质量。如果验收合格,学校马上就可以复课了。
第一次亲眼目睹日本人民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我被彻底镇住了。你可以嘲笑说这是一个死板的民族,但在面对灾难时最需要的品质就是遵守纪律;你也可以讥讽说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但在面对灾难时最重要的就是务实精神;你更可以笑话他们无处不在的危机意识,但正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自然灾难,才养成了居安思危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日本民族的宿命感让他们面对灾难时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们敢于正视人世间的无常,敢于承认大自然的威力,并以不变应万变,依靠良好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系,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定胜天。■ 中岛海啸日本东京地震地震自救日本日本海啸抗震救灾日本地震亲历地震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