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帅才”朱光亚
作者:王鸿谅 ( 1966年,朱光亚陪同聂荣臻(中)在核试验现场(左为王淦昌) )
( 1966年,朱光亚陪同聂荣臻(中)在核试验现场(左为王淦昌) )
留学与归国
朱光亚逝世的第二天,北京也下了一场大雪,和当年钱学森走的时候一样。“两弹一星”元勋里,他是解密得最晚的,他推辞各种采访,拒绝出书立传,不愿意进入公众视野。写他的文章,送审到他那里之后基本中止,他总是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这种沉默低调,或许与他毕生的事业有关。“两弹一星”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自己搞核武器太艰难了,这个领域里的科学家们都是一样,埋头科研,保守秘密,关心的是大事业能否成功,根本不在乎个人得失。”
朱光亚和中国核武器事业的缘分始于1946年。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正在秘密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蒋介石批准了50万美元作为研制经费,种种乐观的迹象显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召集国内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学习关键技术。俞大维推选了在物理、数学和化学三个方面各有成就的3位教授,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3位教授应邀从昆明西南联大赶往重庆,拟订计划,筛选青年人才一同赴美。数学方面,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推举了唐敖庆、王瑞酰;物理方面,吴大猷挑选的则是自己的学生朱光亚和李政道,都在西南联大,前者是21岁的年轻助教,后者是19岁的“大二”学生。
朱光亚对这个机会曾经心生犹豫。他的父亲朱懋功罹患肺病,只能领到一半薪水,他除了学校里的课程,还在天祥中学(即昆明一中)兼课,以补贴家用。在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爱国民主运动影响下,他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对于国民党政府选派的留学也有所抵触。临行前,朱光亚经过南京,专程向大哥朱光庭征求意见,朱光庭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直到辞世,他鼓励弟弟不要考虑那么多,机会难得,各取所需,反正是先学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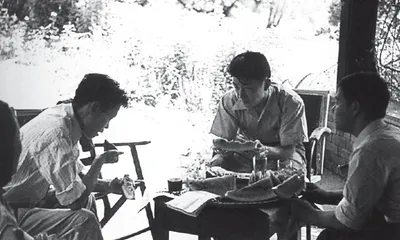 ( 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1947年相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 )
( 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1947年相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 )
1946年8月,朱光亚和李政道等人一起,随同华罗庚赴美,从上海吴淞口码头登船,搭乘“美格将军号”远洋军舰,9月抵达旧金山,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曾昭抡会面。等待他们的是事与愿违的坏消息:美国政府此时已经下令,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曾昭抡建议大家寻找适合的大学,或任教,或选择理想的专业深造。朱光亚选择了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也译作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在学长张文裕、王承书的一致建议下,他师从副教授威登·贝克(Wieden Beck),学习实验核物理专业,成绩优异,功课全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1949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留学时期的朱光亚已经很有号召力,他多才多艺,爱好古典音乐,有一副共鸣腔的好嗓子,指挥过校学生合唱团的合唱,待人谦和热诚,又有组织能力,不仅是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也是留美中国学生中西部地区科协分会的会长,和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他被爱国进步思想吸引,并且积极投身其中。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年底,他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到了1950年2月,签名者已达53人。这封公开信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在此之前,1950年2月底,朱光亚已经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取道香港回国。个人利益和国家需求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就像那封热情洋溢、激励过一大批海外学子的公开信里写的一样:“也许你已经得到了ECA的救济金,也不管它以后还能继续多久,也不管它有没有政治作用,想靠它完成你‘继续研究’的打算,把个人的兴趣看得太重了,忽视了国家人民的迫切需求,这种思想太自私自利了。”他的心境,应该也正如公开信里的豪迈激情:“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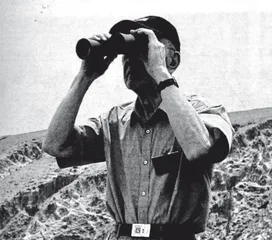 ( 朱光亚在核试验基地视察 )
( 朱光亚在核试验基地视察 )
密执安大学的时光,对于朱光亚还有一层特殊意义,他和相伴一生的妻子许慧君就是在这里相识、相恋。许慧君到美国稍晚一些,1948年才留学密执安攻读化学硕士,她系出名门,来自广州高地街的许氏家族,外公廖仲舒是廖仲恺的哥哥,父亲许崇清曾经担任中山大学校长。相比之下,朱光亚家世普通,祖父辈为逃避战乱从江西迁徙到宜昌,他1924年出生在宜昌,3岁时跟随父亲迁到武汉,在长江边长大,父亲朱懋功早年毕业于平汉铁路的法语学校,先后在宜昌的轮船公司和武汉市外国人办的邮局工作,母亲万怀英是旧式的裹脚妇女,勤俭持家。许慧君在参加进步活动的时候,结识了作为演讲者、组织者的朱光亚。朱光亚回国半年后,1950年8月,硕士毕业的许慧君也选择了回国,受聘于当时的中央卫生研究所,朱光亚专程前往广州接她,他们在王府井森隆酒家举行了婚礼。这是朱光亚人生新的开始,婚姻和事业,一切充满希望。
“两弹”梦想
 ( 朱光亚在美国与妻子许慧君合影(摄于1950年) )
( 朱光亚在美国与妻子许慧君合影(摄于1950年) )
回国后的朱光亚,处于不断的调动之中,一步步从讲台走到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核心位置。1950年4月他被一封加急电报召到了北京,在北大物理系任教,负责光学和普通物理两门课程。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北大在沙滩的红楼校区为他准备了一套平房,包括卫生间、卧室和厨房,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好的条件。他行装简单,除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籍、有关物理实验的材料、上学时的笔记本之外,就是各种唱片,从贝多芬到冼星海,都是省吃俭用买下的,古典音乐是他一生的钟爱。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朱光亚和一批物理学家被调到东北吉林,创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20多名教师白手起家,面对几百名学生,开设3个年级的几十门课程。朱光亚主讲大学一年级的力学、热学和三年级的原子物理学。和在北大的时候一样,他对于教书育人始终充满热情,治学严谨,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就是东北时期朱光亚的学生,他回忆说,朱光亚的课“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影响深远,一辈子受用”。
1955年是朱光亚事业上的重要转折。这年初中央做出发展中国核工业(也称“原子能工业”)的重大决策,原子能教育成为新的重点,正如周恩来年初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的那样:“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成立一个物理研究室,并决定在北大和清华设置相关专业,作为有计划的正规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的培训中心。根据钱三强的推荐及“归队”的召唤,同年5月,朱光亚被高等教育部调回北京,参与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它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6组,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系,后改名为技术物理系)。7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正式成立,主任是胡济民,副主任是朱光亚。100名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选调来的品学兼优者,9月转入北京大学这个专业,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院士是其中之一,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年朱光亚先生讲的课是《核能谱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思维严谨、深刻,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讲解得很透彻。虽然只上了他一年的课,但我终身受益。”
原子能科学一直是朱光亚的梦想,虽然在美国没能如愿学习到原子弹的制造技术,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这门科学的热情。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威胁要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朱光亚写了题为《原子弹与原子武器》的文章,说明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如何防御原子弹,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原子战争。文章由北大油印后在校内外广泛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专门赶到北大采访他,王府井新华书店还在橱窗里展示了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授原子弹有关知识的大幅照片。1951年5月,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随着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朱光亚1957年从北大调至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再次调至二机部新成立的九所,也就是核武器研究所。九所的历史说来有些拗口,1958年二机部成立九局,由李觉担任局长,九局下设九所,负责具体的科学研究,九所后来扩建为九院,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机构变革背后,是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最初苏联是承诺全面协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九局和九所的成立,就是为了接收和学习这项技术,结果1959年6月,苏共致函,以苏、美、英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和苏美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为由,提出先不把苏联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等两年后看局势发展再决定。分析完来信后,中央做出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格局下,原子弹的研制,对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意义深远。从1960年开始,2000余名专业军人、7000多名民工、2000多名建筑工人的庞大队伍,来到青海海晏县金银滩大草原,开始了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同年8月,在二机部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完全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研究起点从一份并不完整的讲课资料开始。早在1958年7月,几位苏联专家曾经给宋任穷、刘杰和钱三强等人讲过一次知识性的技术课,苏联专家组组长聂金说不要记录,将来不仅会运来模型,还会派来专家,提供相关资料。课程讲得很快,但听课的领导们还是抢记了一些并不系统的东西,课后翻译整理出的记录稿和笔记本一起存放在档案室。这些笔记由邓稼先、李嘉尧和朱光亚一同重新整理,朱光亚在主持召开九所全所组长以上技术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详尽介绍了这些资料,也给大家订出目标:我们应当努力研制出爆炸力强、使用核材料少、体积重量小的原子弹。但是,我们当今的一切努力,均以“响”为目标,只要我们能完整地制造出一个来,那么向高级发展就具备了重要条件。他的讲话,被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人们称为“朱光亚式‘交底’”。
种种艰难的条件之下,1964年10月16日15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多年之后,在家人陪同下重看原子弹爆炸资料片的时候,朱光亚还记忆犹新地说起,由于走错了方向,整个过程没有看全,还没有赶到预定的山头,原子弹就爆炸了。他回过头来看着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潸然泪下。
从第一颗原子弹的起爆,到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朱光亚都是全程参与者与领导者之一,近50年的岁月里,他的足迹,遍布在马兰、金银滩、罗布泊这些与中国核武器研制试验相关的地方。他自己曾回顾说:“我就是这样,从20世纪50年代末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到如今已经几十年了,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科技众帅之帅”
钱三强算得上朱光亚的“伯乐”。1959年7月,朱光亚调任九所担任技术负责人,就是钱三强的推荐。1960年3月,朱光亚升任副所长,在九所扩为九院之后,1964年担任副院长。为什么要推荐朱光亚?钱三强后来写道:“他(指朱光亚)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年仅三十五六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要选拔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核武器的研制是多学科的大科学工程,包括理论、设计、生产、冷热试验、测试等各个方面,需要多种专业、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在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原科技委主任郑绍唐研究员告诉本刊:“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而朱光亚在谈起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却将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二机部领导李觉曾回忆说:“每次向中央专委、向总理汇报工作,光亚几乎都要参加。在技术上他能给总理讲清楚。汇报之前,他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60年代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制规划、计划都出自光亚之手。”
昔日的同事、部下和学生对朱光亚的追忆中,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严谨”。王乃彦院士和吕敏院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说:“他善于倾听,去哪里开会,他都是先倾听,思考、思考再思考,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是严谨的、深思熟虑的,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都具有战略眼光。”总装退休干部宋炳寰曾经担任国防科委二局参谋、秘书、处长,1959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与朱光亚有多次工作接触,他强调的同样是朱光亚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为他那和蔼谦逊、平等待人、非常尊重别人劳动的优秀品德所感动。”
在儿子朱明远看来,父亲的这种沉稳和严谨,与年轻时的一段特殊经历相关。1952年4月,还在北大任教的朱光亚和钱学熙被选派到朝鲜,作为翻译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谈判,一年后朱光亚返回北京,谈判依旧没有结束。谈判总是陷入僵局,双方一言不发,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中方代表也相互递烟,以吐烟圈的方式相互较劲。双方都磨炼出了耐性和坐功,可以忍受长时间的沉默。朱光亚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财富,除了那件伴随他多年的军大衣,就是可以长时间一言不发、不轻易表态和不轻率下结论的功夫。
人生七十古来稀,但70岁的朱光亚却有了新的使命:参与筹建中国工程院。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朱光亚全票当选首任院长,同年还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了人生中另一个忙碌的10年。直到2005年正式退休,81岁的朱光亚才真正开始自己的晚年时光。他留给子女的财富,是点滴细节中的言传身教——朴素和严谨。虽然没有大量的时间陪伴家人,但他依旧是细心而体贴的,比如在连电风扇也不普及的时候,夏天全家人吃饭,围坐一桌,他只要在家,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家中的台式电风扇。电风扇转起来,他还要观察一下它摆头时是否能吹到大家,要是电风扇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而且是不厌其烦。还比如,他会精确计算少得可怜的空余时间,躲开警卫员的视线,骑自行车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挑选一些外文书籍。时间富余的话,就去书店旁边的老字号“全素斋”买上一两样素食豆制品回来,与家人一同品尝,家人说好吃,他就很高兴。
朱光亚与当年一同留学的李政道,结下了多年深厚的友谊。李政道回忆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我想,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正是光亚几十年工作和为人的写照。”在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40周年的文章里,他对朱光亚的赞誉是“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帮助,特此感谢;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宋炳寰的《记朱光亚院士的一些往事》和顾小英、朱明远所著《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并致谢) 钱三强严谨原子弹李政道帅才中国科技科技朱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