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的大先生
作者: 冯群星

“应该就是这里了。”24岁的吴良镛停在斜顶房子前,认了认门牌,“新林路8号,没错!”
这是1946年秋天。大概3个月前,梁思成把吴良镛邀到上海,向他交代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至1952年更名为营建系)建系的事。之后,林徽因又来了信,说开学在即,希望他尽快到校。
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吴良镛就赶紧从南京动身了。铁路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而中断,他搭乘一辆运煤船先到天津,再辗转到北平。报到完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林徽因。
“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太高兴了!”林徽因热情接待了吴良镛。本该静养的她在畅谈中忘记了肺部和肾脏的疼痛。两人从学生用的教室、图板谈到未来的课本、课程,还是吴良镛猛然想起林徽因需要休息,起身告辞。
很多年后,吴良镛仍记得这一天的林徽因“好像已从漫长的里程中休息过来,容光焕发”。他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前后,“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但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我妈妈老说,她的妈妈经常是幕后英雄。林徽因这个人,学建筑不在乎学位,写书不在乎署名。这是她的一种学术精神,真正不为名利,只为她的热爱。”于葵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一艘新舰”
林先生与我俩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梁思成《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
林徽因首次站上讲台时,也只有24岁。
第一次上课,她就把学生们带到沈阳故宫前。这座最早由努尔哈赤开始兴建的宫殿建筑群,分为东、中、西三路,共有古建筑114座、房间500余间。
“哪一座宫殿最能体现宫殿美学结构?”大家四散观察、感受后,林徽因提出问题。
“崇政殿。”“大政殿。”“我觉得是大清门。”
看着踊跃作答的学生们,林徽因笑意盈盈地问:“有人注意到八旗亭了吗?”
众人的目光随着她投向东路两侧呈雁翅状排列的亭子。不同于金碧辉煌、重檐攒尖的大政殿,它们没有特殊装潢,也少有精细雕刻,略显朴素和简陋。
可在林徽因看来,八旗亭同样很美。
“这些亭子单独看起来,与整个建筑毫不协调,可是你们从总体看,这飞檐斗拱的抱厦,与大殿形成了大与小、简与繁的有机整体,如果设计了四面对称的建筑,这独具的匠心也就没有了。”林徽因一路延展开去,从八旗亭讲到大清的八旗制度,最后总结,“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
年轻的林徽因,对中国建筑美学已有了独到的思考。
此时是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奉天(今沈阳)的东北大学担任建筑学系教授——如今看来颇为体面,在当时并不算主流的职业选择。
中国建筑历史悠久,但建筑之术被视为“匠学”,主要依赖师徒间口授传习。梁林归国时,包括东北大学在内,全国仅有两所大学开设了建筑系。
与梁林一起留学的同窗,如杨廷宝、朱彬等,不少人进入建筑事务所任职,一来能更好地学以致用,二来薪资可观。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也说,“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
尽管如此,面对东北大学的邀约,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是欣然前往,成为建筑学系仅有的两位老师。林徽因的心里跃动着一团火:要让学生看到西方现代建筑的成就,“但绝非取代我们自己的”。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教授丁建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梁林在课程体系上借鉴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模式,但加入了《东洋建筑史》《东洋雕塑史》《宫室史(中国)》等课程。“他们一方面对接国际前沿,将西方的‘学院派’教育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兼顾中国历史和艺术,希望培养具有中国审美的本土建筑师。”
1929年到1930年,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力邀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植、蔡方荫、童寯也先后加入东北大学。
这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通宵达旦地投入“奠基”工作,让建筑学系成为当时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个系。
林徽因也常常“开夜车”。她的精神格外振奋,身体却在东北的苦寒和终日的劳碌下提出抗议,肺病开始频频发作。生下女儿梁再冰后,她不得不回到北平养病。1931年,为照顾妻女,梁思成也离开东北大学。
对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就像另一群孩子,“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首届10名学生毕业时正在流亡途中(东北已全境沦陷,日寇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两人无法亲临祝贺,便将期许都写在了信中:
“现在你们毕业了,你们是东北大学第一班建筑学生,是‘国产’建筑师的始祖,如一艘新舰行下水典礼,你们的责任是何等重要,你们的前程是何等的远大!林先生与我俩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新舰”们不负所望。丁建华说,不只是“第一班”,由梁林指导过的东北大学建筑学系前三届学子,绝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建筑领域的顶梁柱——
刘致平,是杭州六和塔、正定隆兴寺、赵州大石桥的测绘和修复设计者,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刘鸿典,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首任系主任,参加了兵马俑二、三号坑的规划设计论证;
张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等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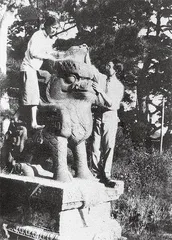
“七宝楼台”
黑夜天空上只一片渺茫;
整宇宙星斗那里闪亮,
远距离光明如无边海面,
是每小粒晶莹,给了你方向。
——林徽因《病中杂诗九首》
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位系主任,系里只有“空空的两间房子”,千头万绪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可眼下,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发来邀请函,请他去讲中国的建筑和艺术。
当时的梁思成,内心一定是万分放不下系里的。但林徽因以她的热诚和勇气,给了梁思成莫大的安全感,让他放心远行。
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都知道,“有事可以找林先生商量”。吴良镛记得,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

学生上课没有石膏像,她派人去找美院的讲师翻制;
采购绘画用品,她嘱咐去东单口永兴洋纸行,那里物美价廉;
资料室图书不够,她把自己和梁思成的藏书交给师生们传阅;
系里需要助教,她提出住在颐和园的一位中国营造学社旧友可以胜任;
北平物价飞涨,大米价格比他们刚回来时涨了近3倍,她组织一些人承接社会上的设计业务,用所得的钱购买颜料、纸张等文具,供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
吴良镛与外文系讲师合住,她知道了,感觉这样多有不便,就安排吴良镛住进金岳霖住宅的一处空房。吴良镛感慨:“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
…………
林徽因治学严谨,说话痛快。她指导第一届学生茹竟华、王其明研究清朝时的集体住宅——八旗营房,细心教两名女生查阅文献、调查访问、分析问题、找出疑点,并一再强调要深入实际。
见到论文初稿时,她直言:“怎么写的没有你们看见的那么好?”等论文修改完成,她又不吝赞美:“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是研究中国建筑传统极好的报告,亦为中国建筑史供给了贵重的资料。”
操持建筑系大小事务的同时,林徽因还要应付持久的低烧和咳喘。夜里她往往辗转难眠,一次次地咳痰、喝水、吃药……1947年12月,梁思成回国后,林徽因在他的陪同下切除了一侧肾脏。切下来的肾放在盘中,大夫划开给梁思成看,“里面病变化脓严重”。
新林院8号的门口立起了一块写着字的木牌:“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
但新林院8号的客厅还是敞开门欢迎着大家。
有时候,林徽因在客厅里给来访的师生们讲课。她的精神和劲头经常令母亲林老太太吃惊:“怎么讲起课来好像病好了?”
有时候,客厅里举办的是文化沙龙,桌子上放着家里自制的点心,大家边吃边唱边谈。林徽因通常躺在一旁的卧室里听着,但到了情绪高昂时,她会强撑起身体走到客厅里参加。
“她的到来会使当时的气氛愈加欢快……当她谈得太兴奋太激动时,她就连喘带咳,这时只有梁先生或林先生的母亲林老太太出来劝阻,扶她上床。”被誉为建筑系“四大金刚”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汪国瑜生前回忆。
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提出“人居环境学”的吴良镛,只觉得与梁林两位先生相识后,“午后茶聚”和工作上的诸多接触仿佛将他引到了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
声声回响
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
——林徽因指导常沙娜
林徽因的教育实践,从不局限在课堂内。
1951年,受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小组,以帮助景泰蓝等中国传统工艺品摆脱衰退的困境。
为了解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和生产状况,林徽因不顾病体,几次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前往南郊的工厂。
实地调研后,她很快得出结论:工人师傅手艺是高超的,但传统产品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需要创新。于是,她带组员研究中国历代建筑、青铜玉器及服饰图案,从中汲取灵感。
20岁的常沙娜也在小组里。她记得,讲到动情处,林徽因说:“我们具有如此悠久丰富的五千年历史,自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整理出版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
1952年,适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接到了礼品设计任务,常沙娜负责设计一款丝巾。

“当时林先生指导我设计,她虚弱地躺在床上,想法却非常灵活。她对我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感,马上就设计出来了。”常沙娜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
这段经历决定了常沙娜一生的事业,她后来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被誉为“永远的敦煌少女”。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那朵熠熠生辉的浮雕大花,就是她以敦煌藻井为灵感设计的。而指导她完善这一设计的,又是林徽因在东北大学的高徒张镈,此时他负责主持人民大会堂的设计。
今年,林徽因逝世70年了。曾经围拢在她身边、聆听她教诲的学生们,也都垂垂老矣甚至离开了人间。那么,在建筑学的课堂上、在年轻人的画板上,还能看到林徽因的“踪影”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珂说,林徽因和梁思成虽已远去,但他们为中国建筑师和建筑教育留下了一些传统,其中一项就是对历史和文化的重视。“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的‘建筑意’,也是试图透过外在的造型艺术,看到建筑背后的文化变迁。”
李路珂讲起一桩笑谈:“我们建筑系的很多女生,包括我本人,参加社会活动时,多多少少会跟人谈到林徽因。有时候他们会问,你是不是‘现代的林徽因’?”
新一代女性建筑师们当然拥有全新的天地和命题。但也许在某个灵光一现的时刻——对着深夜的台灯勾勒设计草图时,攀上钢结构横梁丈量空间尺度时,伏案翻阅泛黄的古建测绘手稿时,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时,她们会听到一个声音:“建筑本来是有民族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那是林徽因留下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