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作者:蒲实 主笔/蒲实
主笔/蒲实
实习记者/王鸿娇
“城”与“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刺桐城》一书里提到,泉州经历了从一个地方的、边缘性的城市转变成一个非边缘的、被纳入官方体系的过程。它大致是一个怎样的转换过程?
王铭铭:现在我们叫泉州的地方,远古生活着“百越民族”,可想而知,那时,“原住民”也有自己的中心-边缘区位体系。但从“国史”角度看,泉州区位系统的形成,与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相继导致的华夏文明中心南移是紧密相关的。泉州首先是这一转移的结果,此后,它从“越地”变成了一座华夏世界的区域性城市。一旦有了城市,就有一个以华夏为模型的区系制度。北方衣冠南渡及更多人口在唐中叶后的南迁,给南方带来财富、“社会”和文明。这大概便是我们所说的“非边缘化”的意思吧。
到了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历史变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历史,进一步地抬升了泉州的地位。按照人类学前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说法,浙江、福建和广东东部基本上属于一个经济区。南宋首都区位的转移,使着整个经济“中心化”了。泉州从中获益颇多。那时的泉州有点像南宋的一个经济特区,南宋有很多财政收入是从泉州来的,同样,泉州也受益于朝廷给它的特殊制度。南宋在泉州有皇族的一支,南外宗。他们一方面从海外贸易中收税,另一方面依赖泉州的经济收入养活自己。
泉州史接着的转变跟元帝国的兴起有关。这个帝国的粮食依靠南方,南北海上运输(漕运)对朝廷很关键,而这一运输大大仰赖泉州海船和船帮。加之元朝统治者似乎比较习惯文化多样性,对于泉州商贸和宗教的“世界性”乐见其成,这给了它新的机遇。
区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比如说几个小村庄之间需要有一个市场,不然无法互通有无,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以市镇为中心的小区域体系。再往上,市镇之间出于互通有无的需要,会形成一个更高的区域体系。但中国的区域体系有民间自然而然的发生史,也有朝廷通过建立州县建立一个更正规化的系统给予的推动。从泉州的经济区系发展史看,动力是复合多样的,它的“非边缘性”的获得,原因也是复合多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泉州又有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空间转移?
王铭铭:我自己的看法是,从明初开始,泉州城市的繁荣面貌就慢慢走向灰暗了。明以前,泉州亦儒亦商,明初,城中儒商中的“商”的气质不大受朝廷喜欢,朝廷喜欢的是“儒”。在宋元这段时间,当地尽管建立了州府,有行政区系,但还是相对自主。到了明初,朝廷很焦虑,觉得之前朝代有点以夷乱夏,外国因素太多,特别是像泉州这个地方,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很重要,夷的文明因素——如各种世界宗教因素——也很多。明初的朝廷更鼓励用儒家教化来改变这种文化上混乱的自我认同和流动性过强的局面。此时,这座城变成一座象征着华夏文化的地点,很多礼教空间得以建设,那些不大相同的因素被压抑。朝廷还有很多反对商业贸易的政策,排斥民间的商业功能。这些商业功能迁出城外。沿海出现很多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城镇,靠传统上自己善于做的那些事营生。泉州自身的海上贸易功能下降,社会治理功能上升,不再是“市”,而是“城”,代表的是“治”。
有一个短暂的阶段,地方精英努力想复兴它原有的繁荣。大概是在清初,地方上有一些人在朝廷当了大官,他们跟地方的这些派系关系比较密切,都对家乡有一种感情。他们设计的一些政策比较倾向于道教思想,重视民间社会生命力的培植,但为时已晚。后来鸦片战争给了泉州另外一个打击。此后建立五个通商口岸。泉州这座老通商口岸的地位与福州和厦门相比,在世界经济体系格局里变得次要了,可以说几乎彻底边缘化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城”的象征力量把“市”排除在外的过程中,它与泉州原本开放的历史文化力量有没有一个较量过程?
王铭铭:古代“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近代以来要和谐得多。它背后有一套宇宙观和本体论是相通的。所谓“大传统”就是士大夫、朝廷的文明。朝廷在明初系统化地重建那些朝廷的祭祀和科举空间系统,比如说城隍庙、文庙、武庙,各种山川雷神祭坛,还有科举考试的地方,都属于“大传统”。民间那些根植于生活的信仰和仪式,我们称为“小传统”。这两个传统依据的东西相互重合的地方相当多。近代以来,帝制被共和制替代,它的象征体系、仪式系统、礼教系统就不再有效,但民间的“小传统”还留着很多,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改变。它分散在生活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彻底根除。而上层建筑已经现代化,跟民间相通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比如,我们基本上是用西方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确立我们的新传统的,跟朝廷的那套不一样,也就缺少与今日仍旧存续于民间的“小传统”共通的宇宙观和本体论逻辑了。
当然两者之间历史上也是有过紧张关系的,二者毕竟旨趣不同。朝廷的旨趣是礼教,其仪式,比如祭山川、祭厉鬼、祭孔夫子、祭关老爷、祭城隍老爷,都有“宣传作用”。朝廷是排他的,认为百姓没资格来参加其祭祀。但如果说老百姓有办法去参与的话,他也是带着自己的生活关切去参与的,他们的生活关切跟朝廷想传播的那套理念,兴许是有差别的,从差别里面可以判断出不同。朝廷的礼仪需要很多经费,教育也需要很多经费,当无法维持经费时,有的空间就会衰败,给“小传统”的进入提供了条件。
比如,泉州在明初是根据前朝的社区街道和邻里的区分来设置的一套基层制度,叫铺境。志书上说,在城里头有36个铺72个境。这些地方成为“里社”,我们今天统称为“社区”,是地方管理的区位,也有官方的祭祀。按要求,老百姓也要围绕邻里形成一个共同体,每年都要跟当地的“社”汇报。“社”不见得是一个人形的东西,它往往是一块石头,是抽象化的“社”,有一定的祭祀空间。从明中后期开始,这些空间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民间信仰空间的东西。民间信仰的历史远比明初设置的那套制度要古老,其在明中叶以后返回“铺境”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从民间的祭祀活动中看到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对繁荣的渴望,对财富的渴望,对香火绵续的渴望。它们在原理上不违背朝廷的“意识形态”,但朝廷想要制造“大治”的局面,有时要与这些祭祀活动的社会生命力较量。
明初的“大传统”跟海外贸易是对立的。我提到朝廷不喜欢“儒商”的“商”,其实我还必须说,朝廷也不喜欢流民,不喜欢江湖。与朝廷不同,民间祭祀空间里的“小传统”不仅是本地居民的公共祭祀空间,而且跟商、流民、江湖有着联系。“小传统”里包含着很强的海外贸易因素,看起来虽然像是农村的地方信仰,但实际上里面有一种开放的因素。举一个例子:妈祖从宋以来朝廷就很重视,人们还以为这是一个“大传统”里的神。其实,妈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神,它的作用在于保护移民、船民的海上安全,与一个以闽南人为载体的“跨国网络”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地方庙里也被供奉和祭祀着。尽管这个信仰被“大传统”化过,但它本质还是“小传统”,而这个“小传统”里面包含着宋元时期繁华的印记,现在仍然跟从事海外贸易、海上运输和民间商业的团体结合得很紧密,而这些团体是没有国界的。明清开始就有以闽南人为中心形成的南洋世界体系,闽南话是跨国用的。无论是方言,还是跟它息息相关的“小传统”,它的文明覆盖面都很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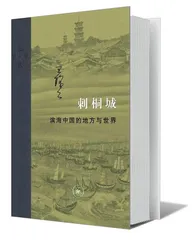 《刺桐城》 书封
《刺桐城》 书封
传统与开放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范畴的身份认同,对于更小范围的地区为单位的认同,是不是会有一个替代?或者是我们现在过于强调前者,会不会影响认同的丰富性?
王铭铭:古人的认同有复合性和丰富性。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我们面对着一个大问题,就是西方发明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使我们的认同产生了单一化的巨变。在欧洲,人们为了说自己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会说他们讲的是英语或法语,会淡化诸多欧洲语言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同源关系。欧洲民族国家当然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但它们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祖先文明谱系。到了绝对王权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代,这个谱系往往被政治家弃之不顾。我们近代以来面对的问题是,这一片面化的民族国家理想得以世界化,使不少人相信,假如我们不接受它的话,我们就是世界的弱者。曾有不少清末民国学者和政治家担心“封建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无法团结,继续分成好多方言区存在,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不利于在世界中生存。历史上的“散沙状”让一些民族主义者感到忧虑。除了其他,他们也推动了“国语运动”,想有一个全民的普遍文化语言基础。这就是传统与现代长期存在矛盾。一个“天下”的民族国家化,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其自身与其所包容的传统上的文化与语言多样性成为一种“负担”。其实,这种“负担”的感觉大可不必。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内在多元、有一体性的文明系统,我们的文化遗产很多是跟多样性有关的,这个系统不见得是一种“弱势”。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在泉州传统的延续性和现代性之间,有怎样的一种平衡的关系?
王铭铭:它的实际面貌是现代和传统并行不悖,不像我们想象的传统必须在现代之前,现代必须替代传统。一方面,泉州人很现代,会玩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也很会做买卖,开工厂;另一面,他们对家族制度、对神鬼祖先的祭祀,还是很积极。在他们很多人看来,传统甚至是现代化的保障。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是一个相当珍贵的东西。我们的理论常说传统在前、现代在后,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它完全是同时展开的,而且传统是现代化的动力。我私下常想,如果没有传统,泉州这个地方的国际化是无法展开的。它的国际化主要靠家族成员,他们去到港澳台,去到南洋,最开始它的原始积累就是靠传统家族网络。现在泉州人有经济实力以后,跟北方人交往多了,可是他们依赖的最早资源实际上就是传统:家族的缘分、跟神明关系的缘分、跟土地的缘分,这些缘分都使他们更开放,传统又给了他们这种开放性。外国投资人很多都是根据这些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泉州的宗族势力依然是比较强大的,这里面是什么原因?
王铭铭:“势力”二字好像有负面含义,我倾向于用“制度”。我认为宗族制度在东南沿海的确保留得比较典型。有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唐中叶以后,南方成为文明中心,随后,在地的一些士人会畅想社会的未来。这些士人既熟悉经史,又熟悉当地民间的情况,也会置身当地,诉诸经史,会对经书上的一些规范进行重新解释,使得有些老百姓的意愿能够被纳进来考虑,能够被杂糅在经史中,使得它成为指导朝廷组织社会的工作纲领。这些历史学家也表明,是这么些士人在做的那些工作,让宗族制度在“庶民化”中得以发展。的确,宋以前,宗族制度是“贵族化”的,老百姓不能祭祀多代先辈,处在等级高处的士大夫可以祭祀多代,皇上可以祭祀最多代的祖先。相比之下,宋以后,调子似乎降低了,宗族的组织原理也被允许老百姓遵从了。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这是出于老百姓自己需要,是出于老百姓减少税收的目的而得到发展的:你一旦祭好多代,族群就很大,古代纳税的规定又是一户纳一份,一个大家族相当于一份,省得每户都去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宗族的“庶民化”是因为古代曾有士大夫认为,让老百姓拥有一种更稳定的社会组织,既便利于治理,又有益于消除等级化,营造某种不同等级共享的“文化”。历史上泉州的宗族制度的发达,兴许与这些历史因素都是有关的。还有,严格说来,当时的泉州属于“移民社会”,兴许这种社会需要更强的组织纽带,而宗族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组织纽带。至于缘何至今不变,我看这既与20世纪以来“家”的绵续有关,也与区域社会的共同体属性的长期绵续有关。而这些都表明,对于我们理解事实,“现代化”是个不恰当的概念。
今天,泉州街上活跃的人,祭祀他们都是很熟练的,小孩子会被大人带着去祭祖敬神。它的“小传统”在全国来说是很特殊的。泉州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古老的、民间的东西。因为有这个状态,泉州文化原有的丰富性才得到了保存。这个事实对我们很有启发,它替我们指出,用理性化把事物抽象成一个单一的东西,往往是以社会生命力的减少乃至绝灭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