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州笔记》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 墨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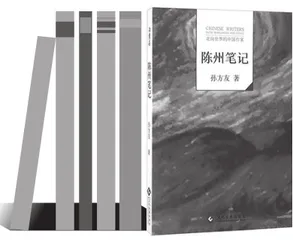
小说家孙方友为我们留下了小说全集20卷,其中包括八卷本总计280万字的新笔记小说《陈州笔记》。
孙方友从35岁开始创作《陈州笔记》,目前收集整理到的(不计残篇)共计756篇,创作历程近30年。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包括《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两个部分,写作时间同时起于1985年,止于2013年7月,其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至1998年。这一时期,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的艺术成主要体现在《陈州笔记》系列上,比如《蚊刑》《女匪》《刺客》《泥兴荷花壶》《神偷》《雅盗》《官威》《猫王》《狱卒》《旗袍》《当印》《刀笔》《天职》《神裱》《张少和》等,都是足以传世的名篇。第二阶段是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化厅下属的《传奇故事》后的1999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陈州笔记》168篇,《小镇人物》288篇,构成了孙方友新笔记小说创作总量的六成。孙方友这一时期的新笔记体小说的叙事风格日臻成熟,特别是到了晚后期,《陈州笔记》里的篇章不仅写得从容自然气运畅通,还写得出神入化,形神浑然一体。
新笔记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中能形成一种独立文体,源于对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因此,只有将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放在中国文学史中考量,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与意义。《陈州笔记》的创作不但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笔记小说、公案小说、明代白话小说的叙事精髓,而且将民间文学、评书、曲艺、戏剧等说唱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理念融入新笔记小说的叙事与故事结构,在清末民初和新中国远不止一个世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写出了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陈州笔记》以陈州文学地理为中心,立足于民间的精神立场、运用鲜明的语言风格创造出集人文历史、人物传记、社会百科为一体的不可重复的审美领域,并以非凡的想象能力塑造了上千名小说人物形象,“是继蒲松龄之后中国文学笔记小说的又一座高峰”。
《陈州笔记》无论在社会学上还是叙事学上,均完整地构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文学世界。在社会学方面,《陈州笔记》的创作成就与价值则体现在源于民间的人文历史、根植人性的百姓列传、中原文化的百科全书等诸多方面。
源于民间的人文历史
1949年9月9日,孙方友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从此他的生命就和这个镇子里所发生的事件,和这片养育他的土地血肉相连、无法分割,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都成了他《小镇人物》里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自1949年到21世纪初叶,共和国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在《小镇人物》众多的人物命运里得到印证。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陈州笔记》讲述了先后三个朝代足足百年有余的历史。
从人类的精神主体出发,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历史都具有主观性,并且残缺不全。在历史学家那里,充满血肉的细节都被忽视或遗漏,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对被遗忘的具有人性的历史与细节的打捞与重现。孙方友面对中国民间社会的秘史、野史、风物、传说、人性等,比一般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多了一把开启的钥匙,因为他不是田野作业,而就生活在田野之中。因此,《陈州笔记》里所呈现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历史,也不是哲学家眼中的历史,而是一个文学家眼中的历史。这是一部带有个人体温、具有文学特质的被浓缩了的20世纪中国民间史。这部民间史有着明确的历史观,那就是民间立场。在《陈州笔记》里,孙方友以民间的精神立场,用独立的文学家的目光,去关照被历史遗忘的人性的灵魂,去关照被忽视的具有质感的脉络,去关照最隐秘的世风民情,以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为蓝本,用民间的奇事奇人、历史传说与民情风俗来结构出完整的故事,将历史的碎片通过一篇又一篇溶解了复杂人性、温热生活与情感充沛的故事,借助众多血肉丰满经历了悲欢离合的人物描绘出一幅具有民间精神的历史画卷。
根植人性的百姓列传
尽管同《史记》里帝王诸侯列传一样,《陈州笔记》在《枣泥藕》《墓谜》《蓍草》《墨庄》《弦歌书院》《赵翰林》《寿图》等小说里写到袁世凯;在《刀笔》《买马》《花杀》《相士石梦达》里写到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泥兴荷花壶》写到官至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中声名显赫的人物,但他们多是以次要人物出现的,《陈州笔记》里众多的传记人物的主体则是底层的民众,“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大量的篇幅是人物列传,但基本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没有老百姓的。孙方友写的是‘民间版的史记’,是‘老百姓的列传’”。
在《陈州笔记》756篇新笔记小说塑造的上千个人物里,几乎涉及了人世间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物,像来自民众生活中的修风箱补锅、修车打铁、打烧饼磨豆腐等这些从事最基本生活行当的人物的身世都有涉及。在《陈州笔记》系列中,有的人物是以某种职务入传,像村长、支书、乡长、镇长、县长、书记、主任、班长、团长、参谋等;有的人物是以某种职业入传,像投递员、老师、阿訇、裁缝等;有的人物是以绰号入传,像《打手》《小上海》《朱麻子》《洋人儿》《谭老二》《杨大眼儿》《胡罗锅》等;更多的人物则是直接以名字入传,像《王洪文》《袁克文》《袁克定》《刘邦汉》《沈玉刚》《罗仰羲》《何玉灵》《罗维娜》《雷老昆》《关学亮》《毛西海》《曾庆年》《李明望》等。
在《陈州笔记》中,即使涉及相同的行当,也有不同的人物入传,比如写匪:有瘫匪、女匪、匪婆;有为恩人报仇的土匪、有开药店的匪医、有办学校的土匪、有爱好书法、爱好收藏、满腹经纶的儒匪,还有扬言等打走了日本鬼子,然后收拾八路军,再收拾国民党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匪。
比如写画家:有《范宗翰》里画《百雁图》的范宗翰、有《画家姚昊》里被称为东方毕加索自成怪派的画家姚昊、有《张广臣》里教导徒弟到自然中画竹的张广臣、有《寿图》里用屁股绘出巨荷的吕老道、有《指画》里的指画名家于天成、有《滕派蝶画》里的“滕派蝶画”传人靳儒学;同是画虎,《虎痴》里以虎为题画了《十二金钗图》的画家甘剑秋和《蒋宏岩》里一样也画虎的蒋宏岩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比如写梨园世家:《刘大昌》里写能反串旦角的武生刘昌大;《赵宝庆》里写京剧武生赵宝庆;《王满囤》里写丑角王满囤;《杨乐》里写受毒品毒害的既善须生也善武戏的杨乐;《易连升》里写生、旦、净、末、丑样样齐全戏路足宽的花脸王易连升;《余金亭》里写主攻武生的余金亭;《陈一侃》写京剧票友陈一侃;《红绣女》写越剧演员红绣女;《名优》里豫剧名角好妮子;《祭台》里写梆子戏演员钱莹;《仙舟》写唱京韵大鼓的盲妮儿;《青皮龙三》写在戏园子里当管事的龙三;《霍大道》里写黑白须生的霍大道。
比如写医生,《瑞竹堂》擅长儿科的名医刘鸿川虽然与《袁世济》里的袁世济、《天职》里的何伏山、《媚药》里的欧阳果、《陈州名医》里的罗汝汉、《恒源祥药店》里的赵汇鑫、《冷若雪》里的冷怀谷、《神医》里的陈一堂、《丁济一》里的丁济一等诸位名医的身世与命运各不相同,和《陈州笔记》里其他人物的命运一样,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在《陈州笔记》里,所有事件的展开,又都是为了塑造人物与人物情感的表达。《陈州笔记》在书写人物的内在情感时,沿用的是“以事载道”的传统技法,依赖的是故事和细节的“象外”,像《刘老克》《程老师》《黑婆婆》这样的小说写人生的酸楚与无奈,就是通过“事之象外”和他人的世界来引领读者的。《陈州笔记》的文字里蕴含着对历史与生活的补充与完善,蕴含着对记忆的唤醒与复原,蕴含着对人间是非的判断,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在冷静的叙事里展开,在不动声色之中完成;还有对人性善恶的反思与审视、对渗透我们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等这些对人类精神的深层挖掘,在《陈州笔记》里从未中断过。
《陈州笔记》在向中国传统文化本源的回归中,对现代社会始终有着审慎与批判精神,那种多向度宽领域的省察,是一种披坚执锐的追问,更是一种深情款款的坚守。正是孙方友笔下的那些根植民间文化、在数千年的风云激荡里沉淀和再生的草芥般的人物,用他们卑微却丰富的生命,为中国的沉沦和崛起作证。在《陈州笔记》里,无论是引车卖浆者,还是士绅名流甚至生活中的无赖,一旦遭遇民族危亡之际,身上便呈现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血性和朴素的品质。《陈州笔记》里由众多身份低微、精神饱满的小人物所构成的审美视野,不仅体现了孙方友对传统精神初源的向往,也体现了潜藏民间的传统文明本源的价值与魅力。
中原文化的百科全书
有评论家把《陈州笔记》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这无疑是从表现内容的近似、复杂与丰富性上获得了对照,《陈州笔记》里所描述的和《清明上河图》这幅现实主义绘画里所描绘的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这些人物在百肆杂陈、店铺林立的街道里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情景相同,二者在药房、酒肆、茶馆、肉铺、米店、庙宇这些建筑里所做的诸如望闻问切、看相算命、修面整容,聚谈闲逛、喝茶饮酒、买卖交易、推舟拉车等生活内容也很接近;同样重要的是,《清明上河图》和《陈州笔记》都为我们提供了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有关的工业、农业、商业、民俗、建筑、交通等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陈州笔记》里所涉及的金店、银号、会馆、当铺、装裱、花局、烟厂、炮铺、药房、药店、药铺、粮号、粮店、米店、商行、盐号、渔行、布店、鞋店、鞋铺、货栈、杂货店、烙花店、钟表店、白铁铺、弹花店、炕房、澡堂、浴池、染坊、剃头铺、修表铺、旧书铺、成衣店、影戏、唢呐、戏班、馍铺、酱菜店、菜行、烧饼铺、油坊、豆腐店、面铺、果铺、面条铺、茶馆、饭庄、酒馆、酒坊、酒楼等,只要是我们所处社会现在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营生与行当,《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里不仅都写到了,而且还在前面常常加上地名、姓氏与称谓,比如《陈州金店》《吕家渔行》《海氏豆腐店》《康记货栈》等;有的直接以某种行业为叙事主题,像玩猴、杂技、红案、厨师、脚行、车夫、装卸、轿夫、更夫、保镖、邮差、铁匠、油匠、刻章、师爷、私塾、兽医、算命、丐帮、盗墓、哭丧、抬棺等;有的常识因人物而引入,如《泥人王》里由王二写捏泥人、《女保镖》里由女保镖写镖局、《泥兴荷花壶》里由陈三关写烧陶器、《一笑了之》里由刽子手封丘写刑法、《赛酒》里由封家写酿制贡酒、《鬼像》里由贺七写照相、《陈州秀笔》里由书法家段象豹写书法、《尹文成》里由尹文成写书店、《麻祖师》里由麻德昌写制作毛笔、《集文斋》里由罗云长写报馆、《马石匠》里由马老大写雕塑等。
这一切我们不仅从小说的题目上就可管中窥豹 ,而且还能领会到孙方友将行业常识巧妙地融入小说叙事中的美妙,所有的常识都含在叙事里,为故事的发生和发展、为塑造人物、为人物树碑立传所用。这些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常识,在《陈州笔记》里成了故事的切入点或者是事件的核心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内容,能深入反映人生。孙方友使常识成为烘托和塑造人物的手段、把常识巧妙地融化为小说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把生活常识有机地融入小说的叙事载体,是他新笔记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今,很多遗失了的民间工艺、民俗、古物等,都被孙方友珍藏在《陈州笔记》之中,比如《商幌》里写招牌的制作,不但再现了“商幌”这种即将消亡的民间工艺的起源、演变与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孙方友在抢救那些将要消逝的民俗文化上所作出的努力。
《陈州笔记》里不仅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人物,还囊括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生活常识,堪称一部纵横百年的民俗文化志。有评论家把《陈州笔记》喻为产生于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不是没有道理,浮世绘所关注的社会时事、民间传说、历史掌故等,不但和《陈州笔记》里所关注的近似,而且孙方友和那些同是出身民间的浮世绘作者所汲取的来自佛意的“忧世”精神内涵也很接近。《陈州笔记》在满足读者阅读趣味的同时,既能做到把人文风物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又能通过对文化景物的描述来展示人文精神,如在《泥兴荷花壶》里,把陈州特产泥兴荷花壶的神奇和匠人的品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通过《袁世钧》里的袁文玉、《霍大道》里的王丫丫、《易连生》里的宋一梅、《赵宝庆》里的程蓝蓝、《刘太昌》里的宋家小姐宋青霜等这些新女性,来表现她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表现她们为追求爱情、追求自由所做出的反抗与牺牲。孙方友是一位最富有中原特色、最具广泛意义的作家,他“创造了属于他的一方文化地域,这一文化地域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陈州笔记》运用人世间的百科常识来展示市井人生的民俗风情、士农工商的悲欢离合,通过人世间芸芸众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纷繁多姿的世界,成为一部集历史、民俗、民情、民风为一体的带有明显的人文情怀与地域文化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