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双面”周文王
作者: 陈天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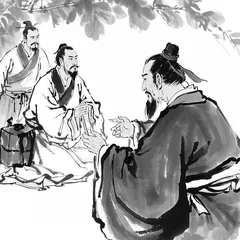
《世说新语》堪称解读魏晋时代的百科全书,其记述了这一时期六百余位人物的逸事清谈,为学界解读魏晋提供了珍贵资料。魏晋是一个人性与思想双重觉醒的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通过《世说新语》,我们便可以一窥这个时代的光华。魏晋司马氏与高门士族紧密相关,当时的虚浮风气使名教渐遭质疑,不少名士由此开始反对虚伪礼教。在儒家传统叙事中,周文王姬昌被塑造为“内圣外王”的典范。在《世说新语》中,我们能看到周文王、孔子等人物备受推崇,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书写。周文王、孔子等人在名士们的笔下呈现出了鲜明的个人特征。以周文王为例,汉代以来的传统书写将文化创造与圣王功业相融合,将周文王从历史人物转化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名士们解构周文王人物形象的创作则象征着魏晋文学的创作转向—文学开始关注创作本体性,周文王由此从文化符号开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其人物形象的变化折射出魏晋文学独特的精神特质。可见,人们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之中开始建构个性化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体系。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周文王形象
周文王姬昌是周武王之父,周武王通常被视为周朝首位君主,但诸多历史文献提及周朝圣王时,常将周文王与周武王合称为“文武二圣”。在先秦至两汉的经典体系中,周文王的形象建构始终遵循着层累叠加的阐释逻辑。周文王作为周朝实际奠基人,在先秦两汉文献里多以圣君形象示人,文王之德是诸子共识。孔子对文王之德极为敬重,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代对文王形象的塑造。
春秋时期,孔子推崇恢复周代礼乐文明,主张克己复礼,其思想以西周礼制为基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展现文王之德是孔子相关撰述中的重要内容。孟子作为儒家学说在先秦的集大成者,继承并拓展了孔子的理论核心。孔子推崇文王之德,而孟子以“仁政”为君王施政的核心:“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孟子推崇周文王为圣人,视其为施仁政、得民心、得天下的典范。
先秦时对周文王的描写多为人物行迹,汉代经学体系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符号化书写,两汉时他已成为神话性人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天将授文王……至文王,形体博长,有四乳而大足,性长于地文势。”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治国思想,周文王征伐崇地被描述为“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崇国之民方困于暴乱之君”,也即解救百姓的大义之举,其扩张行为也被描绘为因贤德招引天下归附,将其纳入了天道运行的阐释框架。总之,从先秦到两汉,周文王不断被赋予仁德贤圣标签。各种文本描写使周文王形象逐渐脱离具体历史语境,演变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图腾。
二、《世说新语》中积极的周文王形象
在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与晋朝司马氏亟须借助儒家正统思想塑造其在文学领域的权威性,故维护周文王积极的文学形象对他们具有深刻意义。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盛行清谈之风,人们在交流时常常引经据典,周文王便是其中常用的论据之一。据笔者统计,周文王在《世说新语》中作为主要人物出现达五次,且大多出现在具有前半部褒义倾向的章节之中,呈现出仁德圣君的形象,以下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言语·第二》中“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周文王第一次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是被间接提及,荀爽以周公作《文王》歌颂周文王为例,反驳袁阆君子靠亲贵成名的观点,还引用《孝经》中有关悖德悖礼的观点来增强说服力。荀爽此举表明二人受赞誉,也反映魏晋时人们重视孝道与儒家亲亲之义。这表明儒家倡导的仁义、孝等伦理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世人皆遵循的君子准则。
《言语·第二》中写道:“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常被用以阐释英雄不问出处的理念。在文中,周文王被与夜光珠、玉璧、大禹相提并论,凸显出其圣贤之品格,进而成为天下学士所追求的目标。蔡洪援引这些典故以表明自身立场,但其借周武王安置顽民之事对当地人予以讽刺,这表明了其分裂之处—英雄不问出处,但洛邑先民却是顽劣的。其言论映射出当时士人皆遵循儒家名教,却被伦理纲常所桎梏,内心充斥着迷茫。
《言语·第二》中写道:“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与谢安口中的周文王是宵衣旰食、日不暇给的。务实的王羲之对名士沉溺于清谈而荒废正事的现象持有批判态度。谢安身为太傅,以秦二世而亡的历史事件作为论据,指出导致秦朝衰亡的根本原因并非清谈。魏晋时期,名士集会与清谈之风盛行,谢安主动为清谈进行辩解。然而,由于谢安受家族利益约束不能再继续深挖这个问题,于是他只能够用一个轻飘飘的例子反驳王羲之。
《政事·第三》中写道:“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规箴·第十》中写道:“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周文王之囿与百姓共享,体现出周文王亲民爱民,广得民心。王安期借周文王之名指出为官者应为民着想。这既展现其清官抱负,也从侧面反映周文王顺民心而得天下。这也说明多数官吏深知为官之正道,《规箴·第十》多为规劝他人的记述,谢混引用周文王之子召伯典故劝桓玄勿占谢家宅子,以周文王一家仁德贤明为论据,奉劝其坚守清流。总体而言,周文王在《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圣人光辉。《世说新语》用很多实例将抽象的周文王仁政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道德实践。《世说新语》通过继续符号化书写周文王,构建了经典的、可供追溯的文化源头,这种经典书写模式具有重要的文化存续意义,也侧面体现了魏晋文人对儒家理想的坚守。
三、魏晋名士笔下另一面的周文王
魏晋时期的哲学转向为传统圣贤观的重新诠释提供了理论土壤。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提出了“崇本息末”论,他主张文人应该超越现象世界的表层符号去把握文学本体,从哲学层面动摇了汉代以来符号化书写体系的权威性。周文王与孔子这些被名教奉为先贤至尊的人物此时便遭受了很多魏晋名士的批判,因为在这种解构思潮中,作为儒家圣王典范的周文王形象理所当然是思想解构的首要对象。但在这一思潮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并非否定周文王,而是借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呼吁文学创作转向。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文人集团的典型代表,嵇康不仅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更是反抗名教的关键力量,他笔下的周文王就有着独特色彩。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明确提出“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他深知此言论必将遭受世俗礼教的批判,故而指出自己不适合出仕。这不仅是他拒绝出仕的重要依据,更是其反对异化符号书写的有力主张。这里的“周”虽未指向周文王,但当时周文王、周武王与周公旦常被称为“三圣”,故我们将周文王合而论之。在《释私论》中,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又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质疑“先王”设教的合理性,暗示周文王的圣人形象可能被过度理想化。向秀在《难养生论》中质疑:“若性命以巧拙为长短,则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他通过寿命长短的实证分析,解构了圣人与天地同寿的神秘性。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更直言:“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学之中的解构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通过祛魅实现对人物形象的价值重估,这种解构实际上是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周文王形象,肯定了周文王的个人价值。我们常言嵇康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可爱的人物,他的内心也如孩童般极为理想化、极为纯净质朴,他也只能通过批判周文王等被异化的符号来侧面抒发自己的理想感情。在《家诫》中,他教导子嗣要成为正人君子,坚守信念;临刑前,他以《广陵散》殉道,其精神内核体现了儒道思想相互交融的理想与信念。在《管蔡论》中,嵇康将周文王、周武王与周公旦并称为“三圣”,这表明他所称赞的是真实的周文王等人。
经学式微,倡导自然的玄学兴起,文人名士重归道家思想,名教与玄学、儒道激烈碰撞交融。何晏、王弼等认为玄学是名教之母,地位在名教之上;向秀倡导名教与自然合一;嵇康、阮籍等人则与名教彻底决裂,尊崇自然。在此思想纷争与文学变革中,周文王等圣人的无瑕光环渐失,趋于普通君主,文人名士开始辩证看待名教所推崇的圣人。可以说,周文王的双面形象映射着魏晋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变革。
四、“双面”周文王背后的时代意义
在魏晋时期,周文王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象征符号。司马氏与很多群众将其视为完美圣人,而文人名士们却认为他功过兼具。周文王的双重形象反映出当时的文学创作已越发关注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创作者的主体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从周文王的形象管中窥豹,曹植《与杨德祖书》提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标志着文学素材观的根本转变;挚虞《文章流别论》系统梳理文体演变,则显示出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这种双重自觉共同推动文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艺术”。至此,文学的本体性成为作者们关注的核心。
在语言层面,文学性的强化尤为显著。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呼吁作者注重作品的个人思想价值。这种转变在对周文王的书写中尤为显著,人们开始频繁借助历史人物抒发个人的理想价值。周文王形象的双面性还反映了魏晋审美范式的深刻变革。相比汉代大赋铺陈叙事的文学风格,魏晋文学更注重言外之意的营造。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这种审美追求在文王题材创作中表现为:既保留“仁政”“德治”等传统符号,又注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考。周文王形象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轨迹,构成一部微缩的思想史。从经学符号到文学意象,从普遍的道德图腾到个人的文学对象,这种转变绝非简单的形象重塑,而是整个文学范式转型的缩影。
回到周文王本身,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周文王也并非周文王本人,而是符号化的周文王形象。作为一名历史人物,无论是被异化的周文王还是文人名士们批评的普通周文王,都是由一堆冷冰冰的标签堆砌而成的符号,我们便是要通过这些不同人给予其的不同标签来解读这个人物符号,进而解读符号背后的文学意义。“双面”周文王的背后折射着魏晋时代两种思想的碰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符号两面性的主次之分,也可以看到时代思潮的趋势与文学发展的变革,这为我们的文学本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