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养与共生:来自南西伯利亚驯鹿部落的启示
作者: 王腾远“泰加林区的一个冬日,明亮的阳光让人觉得暖和,但不时吹来的寒风仍在提醒我们正身处隆冬季节,还有许多寒冷的日子等着我们。巴塔骑着他的驯鹿走在我前面,进行每天的狩猎之旅,我担心自己会做错事,吓到动物。他时不时停下来,拿着望远镜悄悄地四处张望,看看动物们可能在哪儿。从我们出发到现在已经快3个小时了,我只能看到周围茫然无际的白色。我感觉整个世界中,我们是唯一的生命,因为除了自己的心跳,我什么都听不到。”这是人类学家塞尔琴·库楚克斯特尔(Selcen Küçüküstel)进行田野调查时的日记。彼时,她正骑在驯鹿背上,跟随南西伯利亚的杜科哈人(Dukha)穿行在泰加的针叶林中寻找猎物。在库楚克斯特尔的描述中,泰加有一种荒凉寂静的美感。然而,在这表面的荒寒之下,人类与动物却有着温暖而独特的互动与共生。

作为游牧和狩猎民族,杜科哈人生活在蒙古国最北端的霍夫斯格勒省(Khovsgol)西北部,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接壤,该地区也被地理学家称为南西伯利亚。杜科哈族人口不足500,是蒙古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也是蒙古国唯一在寒带针叶林中驯养驯鹿的民族。杜科哈人与图瓦共和国的托贾人、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索尤特人以及中国东北的鄂温克人共同构成世界驯鹿牧区最南端的族群。
风景中的生命
从2012年到2016年,库楚克斯特尔在不同的季节4次造访杜科哈人的营地,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累计长达1年。基于经典人类学的实证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记录,运用生命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库楚克斯特尔在2021年将她对杜科哈人的研究整理成书《拥抱风景:南西伯利亚的驯鹿与狩猎》(Embracing Landscape: Living with Reindeer and Hunting among Spirits in South Sibe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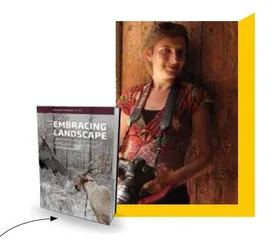
全书10个章节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呈现了杜科哈人泛灵论世界观中风景的特殊意义。他们拒绝将风景的物质性与精神意义相分离。在杜科哈人看来,祖祖辈辈生活其中的风景是有灵魂的生命,并与历史、记忆相互交织。一位杜科哈的年轻猎手感受到作者描述方位的困难之后,主动为她绘制了一张地图。于是作者才意识到,这里几乎所有的山脉、丘陵、山峰、湖泊、河流、溪流、山谷和针叶林在杜科哈语中都有自己的名字。而这些名字都与他们民族的历史、传说、记忆有关。如“Eerenli Dayga”,意思是“祖先们曾留下护身符的地方”,又如“İrool Dayga”,意指“男人/儿子”,据传说,很久以前,一位渴望孩子已久的妇女在那里产下一个儿子,于是后来凡是祈求生育的人,都会去那片森林祈祷。除了这些集体的故事,人们还会根据自己的个体记忆为山林或河流命名。对于杜科哈人,这片土地的风景就像童年相册之于我们,联结着过去的世界。
而杜科哈人想要在泰加林中生存就必须依赖驯鹿,因为驯鹿是泰加林中唯一能够驯养,并能在深深的雪地里移动迁徙的动物。它们帮助杜科哈人留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杜科哈人与驯鹿的共生与他们对风景的依恋息息相关。
超越性的关系
在第二部分,库楚克斯特尔特别关注了驯化驯鹿的过程,人与动物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启示。大约1.2万年前,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从此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也是人类对周围环境产生显著影响的开端。在狩猎采集阶段,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关系,但随着养殖和农耕的出现,关系开始出现转化,人类开始将动物视作自己的财产。然而,相比于其他蓄养动物,如牛、马、羊等,驯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独立性。野生驯鹿与蓄养驯鹿并没有形态上的明显差别。在没有人类照料的情况下,蓄养驯鹿完全可以在野生环境中生存,如若看管不当,家养驯鹿走失后就会重新变回野生驯鹿。杜科哈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充分尊重驯鹿的自主性。作者指出,比起大规模畜牧业中,人类对牛羊等动物绝对的统治关系,杜科哈人与驯鹿的关系更接近于父母与子女,库楚克斯特尔称其为“抚养控制”(nurturing control)。杜科哈人从不将驯鹿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就像母亲通常不会将孩子看作自己的财产一样,这是一种基于情感与信任的社会关系。尽管人类在这个关系中具有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处于优越地位,因为他们并非根据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需要让渡自己的权力,优先考虑驯鹿的需求,比如在某些季节,人类要遵循驯鹿的习性,跟随驯鹿长距离迁徙。
人类世(Anthropocene):
一个拟议的地质年代概念,该术语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创造。“人类世”的支持者认为,工业化、森林砍伐和化石燃料燃烧等人类活动已导致地球地质和气候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海洋酸化和大范围的物种灭绝。2024年3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投票否决了将“人类世”正式列为地质时间单位的提案,主要原因在于地质学家们尚未就其确切开始时间达成一致。一些学者将其追溯至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另一些学者则将开始时间定在20世纪中叶,特别突出了1945年7月16日,人类首次进行原子弹测试的时间。


在杜科哈人的营地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超越了二元对立。这一超越性不仅体现在人类对驯鹿的“抚养控制”,还体现在杜科哈人的狩猎活动中。以生存为目的狩猎行为一直是人类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杜科哈人的案例中,作者指出,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远非单纯的杀戮与暴力,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杜科哈人将动物看作具有人格的同等存在。而他们获取的猎物是动物自愿的献祭和神明的馈赠。他们在狩猎前、中、后都要遵守禁忌,并举行庄严的仪式,以表达对猎物的尊敬。杜科哈人在去世后实行天葬,以这种方式回馈动物,以实现平等的索取与给予。在杜科哈人看来,自然的神明只会将猎物赐予品行高尚的猎人。因此,除了遵守禁忌,杜科哈猎人会将猎物分给营地中的所有老人与孩子。狩猎在杜科哈人看来,不只是获取食物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狩猎,他们与泰加林中的神灵保持联结。
流失的精神空间
自2011年,杜科哈人生活的泰加林区被划为国家公园。2013年后,狩猎被法律严格禁止。私下打猎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将面临巨额的罚款甚至牢狱之灾。为补偿杜科哈人,政府每月为每个成年人发放65美元津贴,每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30美元。这些固定津贴的确改善了杜科哈人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社区与精神却面临解体的命运。在田野调查的4年时间里,作者目睹了整个社区发生的变化。“禁猎给杜科哈人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漫长的冬季,当驯鹿离开时,年轻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土著社区一样,杜科哈人开始出现酗酒问题,这一点显而易见。我在泰加地区的头几年很少看到有人喝酒。然而2016年我回到那里时,多次目睹人们连续3天喝个不停。在针叶林里,不能去打猎,这无疑是男人们感到无聊的原因之一。喝酒成了唯一的安慰。此外,这种时时刻刻都受到限制与监视的感觉让他们感到软弱和缺乏自决能力,他们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像被关在一个开放的监狱里。”
杜科哈人与国家公园的冲突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她认为,对于杜科哈人的社会来说,这一冲突的本质是强行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可以看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原住民世界观所造成的冲击与伤害。国家公园的设立,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加给了原住民。泰加林的风景,从承载记忆与灵魂的神圣空间渐渐成为被欣赏的客体。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