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点
作者: 赵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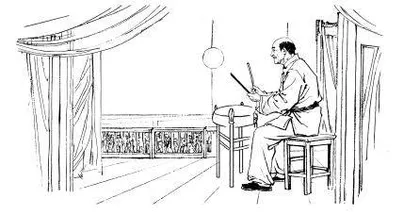
袁店河当年是戏窝子。
袁店河上下,人们热(方言,热衷,喜欢)戏,上地唱,下河唱,打柴唱,划船唱,连吆喝买卖也是戏腔。袁店河由北向南流,往南到汉口,入长江。船多。货品多。南来北往的商人,看得多,见识广。来这里的戏班子,得有真本事。台上唱,台下伴唱,谁都会那么几段。伴唱的声音往往压过了琴声,淹没了舞台上演员的行腔,如同河滩上开了大型演唱会…
热戏的人多,戏班子就来得多。各路的戏都有:二黄、秦腔、豫剧、曲子、越剧、山西梆子……戏班子来得越多,热戏的人也就越多。有一句话对于袁店河的人来说是一种骄傲:“鸡叫狗咬,都是戏腔。”还有一句话:“无君子不养艺人。”在袁店河,这句话落实得很到位。有年春会,恰逢倒春寒,下了流冰(方言,指雨雪后道路结冰),戏班子没法走。袁店河的人争着管吃喝:“走,去俺家两个!”“我要郭暖、娘娘,还有薛丁山!”……
所以,当年的袁店河是戏窝子,不是吹的。有下面几个人为证。
李小黑唱火了,火在他的笑。包拯的、唐王的、伍子胥的,他笑得都别具一格,各有特点。人们觉得,他的笑,是模板。多年后,有人再唱包拯,听到笑腔时,一些上了年纪的还说:“与李小黑相比,是戴礼帽亲嘴!”意思是差得远。有一年,就在河滩的戏台上,他饰演法海,上场哈哈一声大笑,把牲口市上的牛马惊得乱叫,尥蹶子。
马二山唱火了,火在他的功夫。他武功、功架俱佳,足蹬五寸高靴,背扎四面靠旗,头戴两只鸡翎,腰挂三尺宝剑。他做“垛子叉”——从两张桌子摞起来又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处空翻落地!接着四肢跷起来,以肚脐为中心旋转两圈,浑身上下不磕,不碰,不挂,不乱!
摆草坡唱火了,火在他的矮子功。半矮子、全矮子,以及“矮子霸”“矮子边”“矮子拳”,他都能来。他踏方步,亮靴底,左右晃,眨眼间就地打飞脚,翻抢背,上椅子,观众却看不到他的两条腿!
可是,他们的火,并没有让自己十分开心,因为陈玉山没有唱成戏,没有唱出来。他们村没有戏班,也请不起大戏班子来演出,他们就自己唱,特别是逢年过节时。锅底灰抹脸,花被单一披,围裙一裹,铜盆当锣,擀杖为梆,就在村中的碾盘上有模有样地唱起来。
戏,本是给神看的。唱戏,不是随便的玩意儿,讲究仪式感。他们决定在碾盘上唱时,也认真地进行了“轰台”仪式。那个八月十五的中午,十三岁的李小黑从家里抱来一只公鸡,念叨了一番,杀掉,将鸡头挂在碾盘附近的老榆树上。马二山放鞭炮。他胆大,把短小的挂鞭捏在手上,噼啪作响中竟然围着碾盘转了两圈!摆草坡和陈玉山接着跳上碾盘,打“闹台”,伴着嘴里的模拟音腔。他们就这样让村里也有了自己的戏班子。
慢慢地,他们唱出了名堂。李小黑唱火了。马二山唱火了。摆草坡唱火了。“要得欢,进戏班,还有吃来还有穿。”他们进了戏班,上了舞台,还南下汉口演出。
没有唱出来的陈玉山呢,就留在了村里。与当年其他人用功学唱不同,他司鼓。坐在灯光之外的他,配着舞台上的走步、腰身、行腔,精准地敲出“长锤”“凤点”等鼓点,点点到位,准确地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留在了村里的他,逢年过节便组织唱戏,司鼓。他熟悉文武场的每一种乐器,对于各种唱腔、曲牌、剧目也了如指掌。在他错落有致的鼓点引领下,整个舞台灵动而有生气。和城里的大戏院相比,陈玉山觉得村里的土坯、石头、水缸搭就的舞台一样有韵味,虽然不能挣钱。人们说,作为鼓师的陈玉山打响了小村,敲红了袁店河。
人们就说他傻,说他应该也学发小们走出去,光鲜地挣大钱。
他的老婆也说。
他说:“我要是出去了,村里的戏班子可就散了。有了这个小戏班,老少爷儿们放声一吼,尽情笑骂,多好!”
就这样,陈玉山留在了村里,司鼓,一干就是几十年。人们越来越觉得他的鼓打得好!开台铿锵有力,中间鼓点紧凑,结尾张弛有度。渐渐地,甚至有了“看唱的不如看打鼓的”这样的说法。人们说,来小村看戏,主要是看陈玉山司鼓。
春节,摆草坡回来了,马二山回来了,李小黑回来了。他们相约回到小村,为陈玉山捐建了一个“乡村大舞台”,就在他家的院子里。几个老伙计说,比较而言,陈玉山对于袁店河的贡献更大,付出更多。
那天,县文化局局长也来了。局长一手好书法,为陈玉山题词:因热爱而投入,因投入而成就,因成就而绽放!
那天,陈玉山特别高兴,端坐鼓架前,与其他伴奏者眼神交流,彼此会意后,鼓键子一举,“咚——”,鸦雀无声!大家都望着他,等他的指挥……
可是,陈玉山慢慢地低下了头……在他快要瘫下去时,他的老伴赶紧过来,抱住了他!
他的老伴——邻家闺女——当年就是看他打鼓入了迷。他们创编了几种独特的鼓点,作为当年预约见面的信号。
见他还要往下瘫,她就敲起了当年的鼓点。摆草坡、马二山、李小黑端带撩袍,齐吼一嗓跪了下来:“大哥呀!”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