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婚姻风尚看唐代的妇女地位
作者: 周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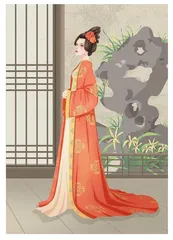
唐代社会虽然整体上以男性为尊,绝大多数妇女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但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当时妇女的地位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社会婚姻风尚如婚姻对象的选择、夫妻关系调解、家产继承、自主选择离婚、改嫁等方面来看,唐代的一些婚姻习俗、法律关注到了女性的部分权益,说明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从社会婚姻风尚角度探讨唐代妇女地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在这方面已形成多层次的研究体系,但从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唐代上层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侧重从妇女一方进行考察,缺乏夫妻双方的比较分析。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底层妇女的婚姻状况,通过对上层妇女、底层妇女、丈夫、妻子在婚姻中的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于唐代妇女地位的认识。
唐代在室女婚姻对象的选择
在室女,也就是未出嫁的女子。唐代在室女婚姻对象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要遵循婚姻律法规定的婚姻缔结程序,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倡父母主导下的包办婚姻,由父母为女儿选择婚姻对象。例如,《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表明婚姻主要由家长决定,父母对于婚姻的缔结具有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出于对女儿婚后生活状况等的考虑,在为女儿择婿时往往注重双方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等。其次,婚姻中重视门第观念,子女的婚姻需有助于家族地位的巩固或提升,强调强强结合,而在室女的自主意愿较少被考虑。这在上层在室女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唐初,“夫人姓李氏,陇西姑臧人……其清流远派,官婚礼乐之盛,冠于百氏,称为甲门……故秦为晋正,德必归仁,以是全美,嫔于我金吾府君,斯相宜也。”李氏与郑府君结合,就是典型的以家事门第为重,强强结合。
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婚姻观念有所进步,以往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世门第等观念有所淡化,在室女在择偶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例如,《户婚律》中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这表明子女需要遵循父母的意愿成婚,但自行缔结婚约成婚的,也受法律认可、保护。这种情况仅限于已经建立婚姻关系的,没有建立婚姻关系的在室女仍需要遵循父母的意愿,如果没有遵循就会受到处罚。这一法令表明,包括在室女在内的未婚男女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能够自主选择婚姻对象。例如,《离魂记》中,倩娘同王宙情投意合却被父亲许配他人,二人不得不相约私奔,反映出倩娘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故事的最后倩娘的父亲最终接受了二人的婚姻,这反映了唐代社会封建礼教逐渐宽松的一面。
总的来说,从婚姻对象的选择来看,在室女的自主性较低,不能自己做主,但是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婚姻观念的进步,无论是在室女本人还是其父母等,都有了一定的女性可以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观念,在特定情况下女性也能够自主追求爱情。
唐代婚姻中的性别差异
为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唐代婚姻法律对夫妻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在具体的限制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户婚律》中提到“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反映了在婚姻中妻子需要服从丈夫,体现了妻子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户婚律》对妻子的贞洁也有严格的要求,“妻有淫佚之行,夫得休之”,妻子的贞洁是维系婚姻的重要条件,妻子一旦失贞,丈夫有权休妻。而对于丈夫,《户婚律》虽然承认“一夫一妻,不刊之制”,但是丈夫纳妾的行为在实际上被默许且不受法律惩罚,这表明,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婚姻中享有更多的自由。除此之外,唐代律法对夫妻之间相互侵害的行为也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唐律疏议》中提道:“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诸妻殴夫……加凡斗伤三等”,对丈夫的暴力行为较为宽容,对妻子则严加惩处。这体现了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女性权益被忽视的现实状况。
婚姻关系中的家庭财产关系,涉及夫妻二人对财产的占有与管理。唐代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共有,但实际上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其中,男性家长对家庭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拥有更大的权利(关于家长的定义有多种划分,文章中主要指丈夫)。例如,《唐律疏议》规定:“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家长在家庭财产处分方面的权利比家庭其他成员要高。而妻子对于家庭财产的占有与管理主要包含从娘家带来的奁产陪嫁以及夫家的财产。奁产陪嫁理应是妻子的私有财产,然而唐天宝年间,犍为参军费子玉死后见到妻子,妻子要他还钱,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子竟然无以应对。可见,这一部分财产,虽然不纳入大家庭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归妻子与其丈夫这个小家庭所有,且以夫为主,妻子对从娘家带来的这部分财产的占有权是不完整的,仍然受到丈夫的限制。妻子对夫家财产也享有一定继承权的,但是这部分权利也是受限制的,一方面妻子在丈夫死后守节不改嫁,并且承担起亡夫所尽的义务才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这是受法律所保护和认可的;另一方面,“诸寡妇无子孙,擅典卖田宅者,杖一百。”妻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家产的管理,但是这依赖夫妻之间的感情,如主事的丈夫在做财产决定前事先询问妻子的意见。妻子的这部分管理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本质上仍是丈夫等家长管理家产。
总的来说,在婚姻关系中,妻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家财,但这部分家财是极其有限的。相关法律条文体现了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礼制原则,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妻子对陪嫁财产的相对支配权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等,这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提供了一份法律保障。
唐代妇女的离婚与再嫁
唐代夫妻解除婚姻关系主要采用“七出”“义绝”“和离”三种方式。《唐律疏议》规定:“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七出”使丈夫拥有了单方面休妻的权利,夫家只要指认妻子存在这些行为,就可以单方面休妻。例如,第三条不事舅姑、第四条口舌,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丈夫往往会随意捏造使其成为休妻的凭借。虽然丈夫在夫妻离婚中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但是也不能滥用。如果说“七出”是对男性利益的维护,那么“三不去”就是传统的封建礼法对女性权益的维护。“三不去”主要指:“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杖一百。并追还合。”“三不去”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的婚姻,限制了男性任意休妻。“义绝”是一种法定的强制离婚,夫妻双方不论哪一方犯了义绝都必须强制解除婚姻关系。“义绝”的范围包括丈夫对妻子亲属犯罪、妻子犯罪于丈夫或夫家亲属、夫妻双方的亲属间犯罪等。“义绝”的具体规定也存在性别差异。例如,“妻子与丈夫缌麻以上亲属通奸即为义绝,而丈夫与妻子母亲通奸才算义绝,如妻欲杀夫即为义绝,夫欲杀妻则没有规定。”“和离”是指双方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即夫妻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解除婚姻关系。这种方式比较温和,属于双方自愿商定离婚,赋予了妇女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使妇女有了一定的离婚自由。《云溪友议》记载杨志坚妻子主动和离,处理的官员因不理解杨志坚妻子的做法而罚其二十大板,但二人的婚姻关系最终还是解除,可见妻子主动和离在法律条件下是允许的,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并不常见,在小说、史书中多作为反面例子,但也有正面例子,如《放妻书》记载:“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丈夫在解除婚姻关系时给予妻子美好的祝愿,这是夫妻二人和平离婚的代表。
唐代允许妇女离婚改嫁或丈夫死后再嫁,对改嫁和再嫁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丧夫再嫁要求妻子守三年丧期,否则会遭受刑事上的处罚;改嫁则额外规定了即使女子改嫁,与前夫直系亲属的关系依旧存在。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中记载:“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这为妻子在丈夫丧期过后自行决定是否改嫁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保障妻子在作出改嫁决定后不会受到束缚和谴责。
总体而言,在离婚与再嫁方面,唐代法律给予了女性部分选择的权利,女性在婚后生活不顺时或者遭受重大变故后,能自行选择今后的道路。虽然离婚、再嫁对女子的要求较男子更为严苛,体现了男女身份的不平等性,但是仍给予女性部分选择的权利,并且拥有法律上的保障,体现了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有所提升,妇女权利逐渐受到重视。
唐代社会继承封建礼制,整体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虽然依旧遵循着“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的社会原则,且贯穿于婚姻关系中,如夫妻二人在婚内的部分权益中存在性别差异、在离婚、再嫁等方面夫妻所受限制、待遇不同等。但是相较于前代,此时女性的权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和进步,在婚姻中女性权益也得到部分维护。这说明女性的婚姻自由在唐代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