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保护
作者: 新提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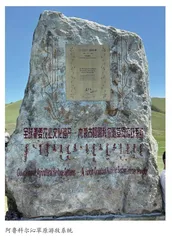
农业文化遗产(GIAHS)作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化的活态系统,其保护不仅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存续,更是对全球生态安全与文化多样性的战略回应。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于2022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其“牧民—牲畜—草原”三元共生模式,展现了游牧文明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智慧。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系统正面临生态退化、文化断代与生计转型的三重危机。文章以批判性视角重构其核心价值,结合生态韧性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及全球经验,提出多维保护框架,试图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新范式。
阿鲁科尔沁游牧系统的深层价值解构
生态韧性:动态适应的科学逻辑。“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整体范围包括阿鲁科尔沁旗全境,阿鲁科尔沁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赤峰市东北部,大兴安岭南麓向西辽河平原过渡的连接地带。东与扎鲁特旗为邻,南与开鲁县毗连,西与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毗连,北与西乌珠穆沁旗接壤。其农业文化遗产地核心保护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最北部的巴彦温都尔苏木,该地区为中山地区,可利用草场面积约25万公顷。该地区林草交错,土质肥沃,水网密集,丘陵高燥的气候特点和生物多样的生态优势,为游牧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及生产生活必需品。游牧核心区与扎鲁特旗和东乌珠穆沁旗接壤,地区特点是雨热同期,即牧草生长期、旺盛期恰在雨季,充足的雨水保证牧草良好生长,为草原游牧畜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受地势影响,降水南北差异较大而且年际变化率大,此气候特点造就了该地区草原植被多样性,多种牧草营养成分互相补充。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传统游牧以蒙古族传统的“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特征,一直保持着牧民、牲畜、草原(河流)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农耕化浪潮和现代农牧业技术兴起之前,对于处在东北温带湿润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过渡区的科尔沁草原来说,传统游牧业的核心策略体现为依托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的适应性生产方式。该生产模式的核心机理在于构建基于生态承载能力的动态平衡系统,具体表现为——人与牲畜不断地迁徙和流动。这种迁徙一方面通过草场资源的时序性利用保障畜牧生产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采用资源循环利用策略维持草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周期,从而有效规避因定点放牧而引发的草场资源过度消耗问题,确保草地生态系统的资源再生能力始终维持在可持续阈值范围内,从而避免破坏草地资源。在阿鲁科尔沁草原,传统游牧文化的静态标识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牧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中。
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与生态学中的“中度干扰假说”(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不谋而合,即适度放牧可促进草原植被多样性。数据显示,核心区草场植物种类达200余种,其中紫花苜蓿等豆科植物占比30%,显著提升了土壤固氮能力。
文化资本:非遗技艺的社会嵌入性。传统的界定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直到现在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习惯。而传统游牧方式指的是牧民群体生产生活长期依赖牲畜和自然资源,即通过季节性的草场变化采取定期迁徙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适应。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以牧民生产活动为主体,同时由草场、牲畜及所需要的生产设施等各种条件组成。阿鲁科尔沁的蒙古族牧民不仅能放牧,而且深刻理解为什么游牧和如何游牧。
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实践通过代际传递形成社会认同。阿鲁科尔沁的非遗项目(如勒勒车、马鞍制作)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族群记忆的载体。勒勒车的榫卯结构无需金属连接,适应草原地形颠簸,其制作技艺蕴含蒙古族“简约实用”的生存哲学。奶制品的发酵与分离技术基于微生物学原理,酸酪干的药用价值已被证实,含丰富益生菌。
这些技艺的传承依赖于社区内部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而非制度化的教育体系,凸显文化资本的地方性特征。
经济理性:低熵系统的可持续性。与传统农业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不同,游牧经济遵循“低熵法则”,即通过最小化资源消耗维持系统稳定。例如,能量循环:牲畜粪便直接还田,减少外部肥料依赖;资源利用:奶、肉、毛、皮的全产业链开发,实现零浪费;风险分散:多畜种(牛、羊、马、骆驼)混养降低疫病风险。研究表明,传统游牧系统的碳足迹仅为集约化牧业的五分之一,其生态效率为现代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结构性矛盾与权力博弈
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断代。在全球化浪潮中,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转向。调查显示,阿鲁科尔沁18~35岁牧民中仅12%的牧民掌握四季轮牧知识,80%的牧民倾向于定居养畜。机械化挤奶机替代手工制酪,GPS定位取代星象导航,传统知识因“去技能化”而面临消亡危机。在传统游牧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这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更是对未来文化多样性的期许。牧民、牲畜与草原(河流)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非遗项目,共同构筑了游牧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让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延续并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更为严谨的动态性展望与实践。首先,保护与传承是游牧文化发展的基石。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和习俗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我们需要加大对游牧文化的保护力度,通过制定更为细致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展更为广泛的教育普及活动,确保游牧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以完整保留。同时,要鼓励牧民们积极参与文化传承活动,通过口传心授、技艺展示等方式,让年轻一代深入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为游牧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在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积极探索游牧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而是在保留游牧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适度的创新。例如,可以将游牧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游牧生活,感受草原的广阔与壮美。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网络化等,对游牧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展示,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最后,在推动游牧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游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形态,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规划放牧路线,合理控制牲畜数量,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确保游牧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以及游牧文化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社会宣传也是推动游牧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再生产的目的是文化实践,为此要对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传播,以便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实践中来。例如,阿鲁科尔沁人民政府举办“纯净草原,游牧记忆”2024年阿鲁科尔沁旗草原游牧系统服务牧民转场暨绿色旅游活动,增进了人们对游牧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互鉴。
生态政策的双重悖论。政府推行的草场承包制与禁牧政策,虽意图遏制荒漠化,但与游牧的流动性本质冲突。例如,围栏效应:固定草场边界阻碍转场,导致局部过牧;补贴偏差:生态补偿金按草场面积发放,变相激励牧民扩大畜群规模。这种“保护性破坏”暴露了政策设计中的生态认知局限。
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突破
勒勒车的创造性转化。巴彦查干团队将传统勒勒车改造为“太阳能移动民宿”,车顶铺设光伏板供电,车厢内部集成生态厕所与文化展示屏。该项目获202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绿色创新奖”,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带动周边牧户增收30%。
生态银行的草场修复试验。政府与牧民签订协议:若连续三年草场植被覆盖率提升至60%,可获得“生态积分”兑换贷款优惠。试点区退化草场恢复率达85%,碳汇量增加12万吨/年。
数字孪生系统的文化传播。北京大学团队构建“虚拟游牧系统”,用户可通过VR参与四季转场,AI模拟极端气候下的决策挑战。该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遗产”最佳实践,全球访问量破千万。
迈向一种新的文明范式
阿鲁科尔沁的保护实践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绝非简单的“博物馆化”,而是需要构建“生态—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这一过程既是技术赋能的创新试验,更是对工业文明单一增长逻辑的深刻反思。唯有将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普遍经验,方能实现“诗意的栖居”与“可持续的繁荣”的终极统一。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