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根记”
作者: 罗朝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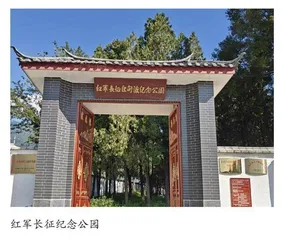
巨甸镇是云贵高原上的一个坝子,居住着汉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等族人民,长久以来,当地各个民族热衷于“打老根”,“老根”则是好朋友的意思。基于田野调查,文章认为“打老根”是一种社会资本,有力地把一定范围内各个民族凝结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铸牢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应当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费孝通曾指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即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影响着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格局。尹绍亭在研究云南民族关系时指出:“要从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去梳理云南民族分布的多元性,交流交往交融的多样性。”近年来,马建雄、寸云激等组成的高原坝子社会研究团队提出“坝子社会”的概念,希望借此深入探讨坝子的地理形态与民族关系、地方文化和社会特征之间的时空联系。“以坝子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因为坝子有着特别的地貌特征,而且在于坝子以及坝子体系所联结的西南山区社会,既是历代中央政府长期经略的国家体制的政治边疆,也是不同社群长期实践其社会建构和持续的文化变迁的具体单元”。“山坝结构下的地理环境既深刻地塑造了西南边疆区域性的社会文化面貌,同时对民族共生空间格局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是云贵高原的一个坝子,当地各个民族热衷于“打老根”。文章以巨甸镇“打老根”为例,探讨坝子社会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个案参考。
“老根”关系的建构
巨甸镇位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西北,距离县城118.5千米,是典型的高原河谷坝子,下辖巨甸、金河、德良、古渡、武侯等村民委员会,居住着彝族、汉族、纳西族、白族、藏族、傈僳族、普米族等族人民。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打老根”的习俗,“老根”是好朋友的意思。
“打老根”主要见于住在高海拔山区的各个民族和住在坝子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同时也见于山区和山区、坝区和坝区的各个民族之间。当地各个民族打老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随意性老根,即关系好的朋友可以互称老根。第二,找老根,即找来的老根。一般而言,家中孩子多病的家庭需要找老根来保佑子女。具体的办法是,在人们经常来往的河流处搭一座桥,把路过此处的第一个人找来打老根(随机型);或者直接到对方家里提出打老根的请求,并告知打老根的日期(请求型)。为了防止辈分关系的混乱,当地各个民族一直坚持同辈打老根的原则。
老根关系的建构伴随相应的仪式。在随机找老根型中,主动的一方要把准备好的线香、黄纸、鸡等献在桥头,并让找来的老根抱着体弱多病的孩子在桥上来回走三遍。在请求找老根型中,打老根当日被请求的一方要提前到达请求一方家中,一同前去选取搭桥的位置并参与搭桥,把线香、黄纸、鸡等献在桥头后,抱着孩子来回走三遍。仪式结束后,老根关系就正式确立。老根关系确立后,接下来每年的大年初一或初二,主动的一方要准备鸡、线香、黄纸及礼品等,到对方家拜年,当地人称为拜老根。三年之后,则不必再拜老根。
从巨甸镇的实际情况来看,老根关系是一种超越朋友的关系,不同于血缘和姻缘的地缘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拉市坝村民苏爷爷(76岁,汉族)称:“自己有三个老根,一个纳西族、一个汉族、一个傈僳族。目前常来往的老根有一个,其他两个来往得很少。”当互称老根的当事人和配偶过世后,这段关系就算结束了。
“老根”社会资本的形成
从巨甸镇来看,当老根关系确立后,老根是以社会资本的形式而存在的。“社会资本是关于社会组织具体形式、质态和特征的范畴,包括相应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能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同时,“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促成了信息的流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社会关系行动,可影响决策者对于行动者施加关键性影响;可以强化社会信用的认同;可以加强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认同”。
“老根”社会资本的形成通过相应的聚会和仪式来实现。打老根当日,主动的一方要搭一座桥并杀一只鸡献桥,找来的老根要抱着孩子在桥上走三遍,仪式结束后要一起吃一顿饭。每年拜老根时,也有相应的仪式和聚会,即主动的一方要带上鸡、线香、黄纸等到对方家里献给对方的祖先,并一起吃饭。一般而言,仪式结束后他们会说“仪式做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老根了,做老根是要认真做的,要叫老根呢。”总体来讲,打老根当日的聚会是主动一方的亲人认识新打的老根,拜老根时的聚会是被动一方的亲人认识新打的老根。
老根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有着相应的规范和信用。老根要相互走动,孝敬对方的父母,关心对方的子女。因老根社会资本的规范性,巨甸镇各民族在打老根时非常谨慎。当地各个民族在打老根时讲究门当户对,即家境较好的不太愿意跟家境差的打老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家境有差异的两家才会打老根。因此,很多人都会拒绝打老根,常见的理由如“我很愿意跟你打老根,但是我前段时间才跟人家打过,现在再打个老根不太好”,又如“不得了,我之前跟他们打老根大病一场,不能保佑你的子女了”。他们认为,老根的家境和社会地位比较高,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当老根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时,能够有效整合两个家庭的社会关系,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如家住拉市坝的和先生与其“老根”是在做川乌附子生意时认识的,他们还一起做野生菌生意,共享发展机遇。
“老根”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巨甸镇,老根是一种社会资本。特纳的研究指出:“所有的人类社会(或明显、或暗地)都遵循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诚然,要理解巨甸镇各民族之间为什么热衷打“老根”,还得从巨甸镇各民族接触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把握。
巨甸镇呈现山区和坝区二元对立统一。山区海拔较高,土层较浅,主要从事山地耕牧业、采集等生产活动。坝区海拔相对较低,土层深厚,水利设施发达,主要从事以稻作为核心的灌溉农业。从居民分布来看,汉族主要居住在坝区,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山区。生活在巨甸山区的彝、傈僳、纳西等民族主要从事山地耕牧和采集,既种植玉米、川乌附子、果树,又养牲畜、采摘各种菌子。生活在巨甸坝子的汉族、白族、纳西族等主要从事灌溉农业,种植水稻、玉米、烤烟、附子等,同时经营服装店、饭店、宾馆等。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巨甸镇各民族热衷于“打老根”,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坝区和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各个民族的生产活动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为了解决这种困境,山区和坝区需要定期进行物资交换。对巨甸镇来说,长久以来坝区和山区的交通不便利,物资交换依靠人背马驮来实现,一个来回要花很长时间,各民族形象地称之为“两头黑”。为了方便物资的交换,各个民族会通过“打老根”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困难。生活在巨甸镇拉市坝的和爷爷说:“街天头一天老根就会到他家来过夜,街天卖了东西再回去”。生活在巨甸的各民族,外出时会通过背老根的方式获得他人的接纳。而当下,山区和坝区的老根会互通消息,共享发展机会。从巨甸的例子来看,基于老根构建起来的社会资本,使人们在陌生社会中获得接纳和包容,利于物质财富的交换,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有力地将巨甸镇坝子和山区的各个民族铸成民族共同体。
在巨甸镇,打老根是一种文化现象。老根社会资本建立之后,各个民族更进一步认识到各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正是因为打老根在各个民族中具有共同性,巨甸各民族才热衷于打老根,并基于老根关系,进一步构建姻缘关系,铸牢各民族文化共同体。例如,2023年12月15日,巨甸镇乡村春晚在巨甸镇双碑广场举行;巨甸镇每年都会举办火把节打跳、重阳节聚会等。
同时,更应承认“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巨甸镇,并在当地各族人民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培育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观念。这种政治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各民族“打老根”中。在称谓上,各民族逐渐减少歧视性称呼,如“罗罗老根”等。而生活在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建设淹没区的各民族老根党员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服从大局,建设美好家园。从巨甸镇来看,老根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把各个民族凝结成政治共同体。
巨甸镇是典型的云贵高原坝子社会,四周高中间低,下辖8个村民委员会,居住着汉族、白族、彝族、傈僳族等民族。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山上,汉族主要居住在坝区,各个民族之间热衷于打老根。“老根”是好朋友的意思,是一种不同于血缘和姻缘的地缘关系。打老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称谓性的打老根;另一种是找来的老根。老根关系需要不时地走动来维护,打老根当事人双方及配偶去世之后,老根关系才算结束。在当地,老根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老根社会资本的形成要通过相应的聚会和仪式来实现。当地各个民族倾向于家境相当的家庭之间打老根,并认为老根家境或地位较高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打老根,是当地各个民族在既定的、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族际互动模式。巨甸镇的坝区,土层深厚,交通便利,水利设施齐全,灌溉农业和商业发达。巨甸镇的山区,土层浅,畜牧业和采集业发达。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让生活在山区和坝区的人民为了满足各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必须进行贸易。为了解决山区和坝区贸易活动存在不便的问题,打老根就成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反过来讲,打老根社会资本使得坝区和山区的各个民族更加有力地凝结成为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金项目: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科研项目“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拉市坝村为例”(2023xy15)。
(作者单位: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