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与视觉探索
作者: 刘雨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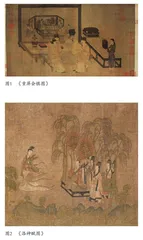
“元绘画”,作为艺术自我反思与视觉形式探索的交汇点,其概念随着艺术史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清晰,并逐渐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关键途径。通过对中国“元绘画”作品的深入探讨,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画家如何通过绘画进行自我对话和自我超越,还能够认识到绘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反映了人类对艺术认知和自我表达的不懈追求。
“元绘画”的概念和溯源
艺术史家维克托·I.斯托伊奇塔在阐述16、17世纪欧洲北部的“画中画”现象时,采用了“元绘画”的概念。从斯托伊奇塔的“元绘画”概念来看,尽管“画中画”和“元绘画”本质上表达了相同的含义,且“元绘画”概念确实基于“画中画”,但“画中画”是对现象的描述,“元绘画”倾向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由此看来,斯托伊奇塔的论述不仅限于“画中画”或“图中图”这类绘画形式的表面解析,而是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换言之,“元绘画”包含“画中画”,“画中画”是“元绘画”的直观视觉呈现。
美国漫画家索尔·斯坦伯格提出“元绘画”概念,他的作品《螺旋》是“元绘画”概念的例证。此作品中,斯坦伯格描绘了一位艺术家正在创作的场景,画中不仅包括了他所画的风景,还巧妙地融入了他正在绘画这一行为事实。随后,美国视觉研究领域的杰出理论家W.J.T.米歇尔认为斯坦伯格的画作就是一种“元图像”。所谓“元图像”,其核心理念在于图像能否展现自身的“元语言”,即能否生成一种二级话语,也就是“图像再现的语言再现”。换句话说,米歇尔认为“元图像”是具有自我参照的图像形式,它不再依赖语言系统来解释自身,而是利用图像自身构建起一种理论性的表达。米歇尔在其著作《图像理论》中列举了多个例子,进一步解读“元图像”的概念,其中包括斯坦伯格的作品《螺旋》,他认为这是关于图像的图像,代表自我参照的图画。斯坦伯格的作品内容描绘了自己创作的过程,使得画家本人也成为这个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此方法消解了绘画的内在空间和外在空间的界限。从这一角度来看,“元绘画”就是关于绘画的绘画,指在一幅画作中描绘绘画行为本身,或在画作中嵌入另一幅画作,这种形式包含了自我指涉、艺术自觉以及互文关系等特征,形成“画里有画”的视觉效果。当然,“元绘画”不能等同于“元图像”,“元绘画”的表现形式为绘画作品,关注点集中在绘画本质、创作过程及艺术史问题,“元图像”的表现媒介涵盖范围则更广。
画里有画的视觉结构
米歇尔在其著作《元图像:图像及其理论话语》中将“元图像”定义为“关于图像的图像”,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图像形式和图像的集合,即图像不仅描绘现实世界,而且反映和探讨图像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换言之,“元图像”在其内容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或反映自身,它们通过这种指向性来阐释图像的本质和意义。这种图像类型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有所体现,也在视觉文化和理论话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理解和分析图像提供了更为深刻的视角。当然,“元绘画”并不仅仅是图像,还涵盖了形式、视觉等其他要素,“元绘画”中的“元”指的是一种后继的、超越性的、更高层次的逻辑形式。毋宁说,“元绘画”具有“画里有画”的视觉特征,“元绘画”注重绘画的理论层面,“画里有画”强调绘画的感知层面,涉及绘画现象的视觉框架构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周文矩所绘《重屏会棋图》是中国“元绘画”的典型,画面巧妙设置“画中画”和“屏中屏”。《重屏会棋图》刻画了李璟与其弟会棋的场景。李璟和李景遂的背后摆放了一扇屏风,屏风里又有一扇绘有山水画的屏风,形成“画中画”的视觉语言。从《重屏会棋图》中我们可以窥见,屏风上常绘有妙笔丹青,中国古人常在室内用屏风进行装饰,屏风上绘制的梅兰竹菊、古玩珍品既是文人士大夫身份的标志,也是文人精神追求的象征,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元绘画”利用“画中画”结构间接投射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屏风既可以分割画面空间,又能扩展画面空间的深度,《重屏会棋图》就巧妙利用屏风实现空间层次的表现张力。画中人物背后的屏风内容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偶眠》语境所绘。一位老翁悠闲地斜躺在床榻之上,其妻子正立于其后,细心地照料着他。另外三位侍女则忙碌于床榻之旁,精心整理着床上的被褥。在老者的床榻后,矗立着一扇三折式的屏风,上面绘有精美的山水画作。画家通过“屏中屏”和“画中画”的设置在平面上构建出三个连续的空间。在中国绘画史上,这类典型的“元绘画”作品屡见不鲜,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同样采用“画中画”的构思。
多元参照的互文关系
自古迄今,中国绘画一直延续着“书画同脉”和“崇尚古法”的传统,笔墨图像原本就存在互相参照的迹象,“互文性”则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普遍现象。“元绘画”的“画中画”视觉特征必然产生互文关系,《重屏会棋图》中屏风上的涂绘内容参照白居易的《偶眠》诗作,形成互文关系。更确切地说,“互文性”导致原本孤立存在的两个文本相融合又形成一层文本,并带有旧文本的痕迹。东晋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也是“元绘画”的典型。《洛神赋图》使用了引用、吸收、戏拟、重写、延长、转换等修辞手法,与曹植的《洛神赋》呈现出互文关系。
《洛神赋图》中的洛神形象取材于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文学作品中的洛神形象必然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发、转化和注解,追根溯源,洛神形象来源于民间传说或远古神话。曹植的《洛神赋》是有感于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显然,曹植对此前的“屈骚”传统是有所承袭的。但其与前代作品的互文关系并不是简单模仿,曹植将自己的政治情怀、人生境遇、兄弟情谊等融入其中,洛神形象与特殊心境之间同样形成了互文关系。曹植内心情感的多样性使得对洛神形象的描绘充满了多重情感。换言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绝非简单地对《洛神赋》进行复制和再现,而是有画家审美旨趣的参与,蕴含着画家的审美感知和审美理解。“元绘画”中洛神的形象反映出顾恺之践行“传神写照”,并赋予洛神个性化的艺术诠释,“有意味的形式”得到间接而深刻的传达。正是画家采用引用、吸收、转换等手法,才使得“元绘画”中的洛神形象逐步丰富并完善。《洛神赋》直接借鉴并吸收了前代洛神形象的元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超越,与前代作品形成了第一层的互文关系。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基于《洛神赋》里的洛神文本进行再次改造,与《洛神赋》构成了第二层的互文关系。因此,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的洛神形象既是单一层面的互文,也体现了复合层面的互文,从而创造了一种“互文的递进”。中国古代“元绘画”作品共同显现出历代文人在前代的文化意象和水墨图像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文本诠释,导致这些作品在主题选择、笔触技巧和艺术意境上形成多元参照。伴随着朝代更迭,作品上除了作者本人的题跋和印章外,还遍布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题识与印记,这些文字与绘画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一种多维度的互文性关系。
自我意识的艺术觉醒
斯托伊奇塔曾根据绘画的自我意识进行探讨,他指出,创作主体在绘画中常采用“嵌入法”“互文性”和“视幻觉”等技法来实现自我意识的传达,形成了早期的现代“元绘画”。可见,“元绘画”的“嵌入法”“互文性”以及“视幻觉”形式,是艺术家自我意识的外化。
“元绘画”蕴含着对绘画的反思,一种是反思其他绘画,即“相互参照”;另一种是反思自己,即“自我参照”。“相互参照”指“元绘画”通过与其他绘画作品的比较或对话来实现意义的构建,这种参照可以是横向的,涉及不同作品间的相互关系。而“自我参照”则意味着“元绘画”在创作过程中对自身的艺术形式、内容或创作过程进行内省和反思,这种参照是纵向的,关注的是作品本身与创作背景、创作意图或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元绘画”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与其他艺术作品的互动性,二是对自身艺术实践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例如,苏轼所绘一系列“枯木怪石”题材,充分展现了“元绘画”的特点。“枯木竹石”题材早在宋代苏轼之前就已然出现,苏轼另创新貌,形成独树一帜的“枯木怪石”风格,与先辈的“枯木竹石”形成跨越时空的互动。“枯木竹石”是苏轼遭贬谪期间最为钟爱的绘画题材,从米芾的《画史》中可以得到佐证,苏轼的“枯木怪石”是其胸中盘郁的表象。由此可知,苏轼的坎坷仕途致使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内心苦闷无处抒发,故而将满腔情感寄托于“枯木竹石”之中。因此,其所绘“枯木怪石”形象并不是客观的再现,而是主客观的融合,旨在融入他的自我情感,他将书画作为自我意识表达媒介,所以以“怪”的面貌呈现。苏轼作画贵在独抒性灵,画中所绘“枯木怪石”的美学价值在于其所体现的自我意识。西方“元绘画”的代表作品《宫娥》以直白的“镜中画”隐晦表达委拉斯贵支与国王夫妇权力关系的互相转换,只在画面背景的小镜子里交代了国王夫妇的形象。位高权重的国王夫妇在艺术创作中也受画家摆布,这是委拉斯贵支作为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体现。与西方绘画《宫娥》以“镜中画”形式直接表明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不同,中国古代传统“元绘画”作品致力于自我意识的含蓄表达。苏轼的“枯木怪石”画作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水墨画,即便没有直观的绘画嵌入,也同样展现了“元绘画”的维度。
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绘画”典型与西方的“元绘画”代表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是因为东西方的底层文化逻辑不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画中画”形式更含蓄,具有情感抒发和政治影射的作用。这意味着,观众在进行中国传统绘画的鉴赏时,不仅需要审美感知,还要具备审美经验,对作品有一定的审美认知。中国传统绘画里的图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被历代文人画家反复临摹、品评,观众的认知不断丰富绘画的视觉层次,文化的积淀也不断深入这种层次,构建出超越时空的文化价值。因此,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不仅是“元绘画”,更是体现“元认知”的图像。
(作者单位:福州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