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交流:“言”与“意”的探索
作者: 彭李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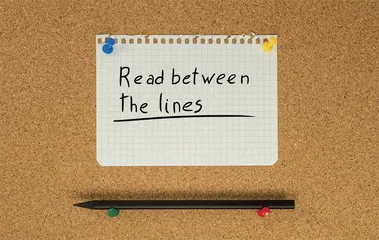
阿西夫·安格(Asif Agha)在大部分人类学家眼中,本质上是个科学家。虽然他的田野调查一流,但即便放在硬核语言学家群体中,他也显得非常“理科”,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分析可以看作数学递归。然而他的理性为人类学家们理解语言使用在交流中起作用的机制增添了许多微妙的层次,从而在社会学甚至哲学层面推动了关于人类交流如何实现的思考,进而扩宽了我们对语言的定义。安格也因此成为广受尊敬的理论拓展者,他的成就是人类学能够对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发展作出推动的证明。
安格的理论如果一一细数,会比较艰深和枯燥,所以我简单讲两个方向。二十世纪以来的几代欧美语言人类学家们都会把牛津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的思想作为研究的起点,思考语言在传递字面意思(具体信息)之外的效力和象征意义。安格的研究把奥斯汀没能深入探讨的语言效力起作用的机制分析得比较深入和让人信服。他最重要的田野调查资料(关于藏语中的敬语)和关于世界上许多语言中敬语的研究是他在这个方向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一个方向是大尺度社会交流活动(large-scale social interactions,包括长期重复进行的仪式或是有计划进行的大型政治活动等)的语言使用模式分析。安格在其中引入了对时间和社会阶层的思考。每一次大型社会交流看似是实时发生的,但其实每一次交流能生效都包含了对过往已经发生过的仪式和事件的认识,以及对参与的所有人的社会阶层的认识。比如哪个阶层的人可以决定哪一种用语在特定时间点出现,是完全按照说话人的身份来讲,还是可以临时改变“剧本”,作为邀请其他参与者进入对话的姿态。对研究者来说,是把这些交流活动看作一个系列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不同活动,还是同一个活动在历史演进中的重复出现?
敬语和语言结构中的言外之意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敬语使用的例子和一个定冠词性别属性的例子。安格自己关于藏语敬语的研究非常复杂,但他引别人的例子说事的时候倒是通俗易懂。比如引用托尔斯泰的小说,这一段小说情节是一位年轻的沙俄高级贵族(伯爵级别)与皇室年长的远房公主的对话。按照贵族等级划分,他们属于同一级别的贵族。然而因为公主年长,所以她应该对年轻伯爵使用次一级的敬语。在那段对话中,她却使用了同一级别的敬语,于是整段对话的所有意义都变了。虽然他们之间商量的是很有信息量的具体事务,但由于公主故意使用了高一级别的敬语,年轻伯爵马上知道了公主在对他冷嘲热讽。这不仅包含了年长的公主对自身地位不满的宣泄,同时也包含了专门针对伯爵本人的警告。于是,伯爵立即小心翼翼,所有的回复都隐藏了一层尽量让意义模糊化,似是而非的意愿。整段对话的具体交流的信息和事件到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话语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角力才成了重点。

第二个例子是德语定冠词,同样是安格借来的例子。阳性定冠词+“男人”一词,组成的短语意思是“那位男士”。中性定冠词+“男人”一词(语法并不正确),组成的短语的意思是“那个娘炮”。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字面语意,还是短语构成的结构,两者都是完全相同的。但使用这两个短语引发的效应却天差地别。前者是日常的话语,后者根据短语使用的语境则是明处有意的挑衅或是暗处的嘲讽。类似的例子在德语中随手一抓一箩筐,都是安格让我们看到怎样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之内实现对社会规则的固化或挑战或重新定义的可能性。
大型社会交流活动如何定义群体
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型社会交流活动给了人类学家们什么灵感。一次仪式自然是一个盛大的交流活动,它有直接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甚至法律意义。在交流的层面,随后会发生的一百次仪式都因为这一次仪式才得以产生效力,因为它们需要参照这一次仪式的范式、社会等级的固化和语言的展演。那么后面那一百次仪式,是同一次仪式的重复,还是一百次不同的新的仪式呢?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每次发生的都是同一个仪式,期待产生的效力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你看重的是由固化的仪式语言指向的意义对一个群体的规范作用。在其中语言人类学家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怎样在一个复杂多向的交流活动中把涉及语言使用的各项行为归类。其中一些被归类为常规琐碎的事情,另外一些却是敏感重要和能够定义或巩固一个群体的价值观的事情。安格很善于分析实际发生的对话和描述,让我们看到交流活动是如何造就和定义了我们的。然而,如果你认为每次发生的都是不同的仪式,那么你看重的是一个群体如何有创意地反复重新定义属于自身所在的群体内部的资源和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于意义(政治、宗教、血缘、阶层等)的理解如何随时间变化。
我们同样来看看安格怎样用他借来的例子阐释他的思考。下面这一段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描述爪哇仪式用语和指涉的社会阶层的两段话。这两段话本身就是非常优美的人类学写作范例:
“Alus的意思是纯洁、精致、空灵、微妙、开明、流畅。一个能说完美的高级爪哇语的人是优秀的,高级爪哇语本身也是如此。一块画有复杂、微妙图案的布就是alus。一首演奏精美的音乐或优美精致的舞步也是alus。一块光滑的石头、一只被抚摸的狗、一个牵强的笑话或一个巧妙的诗意想法也是。当然,上帝是alus(就像所有看不见的有灵性的东西一样),对他的神秘体验也是alus。当一个人在情感上理解存在的终极结构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和性格就有了意义。一个人的行为和行动是由复杂的宫廷礼仪规范的,所以是alus。Kasar 恰恰相反:不礼貌、粗鲁、不文明;一首糟糕的音乐,一个愚蠢的笑话,一块廉价的布都可以叫Kasar。在两极之间,prijaji(即贵族阶级的成员)安排着从农民到国王的所有人(的生活和交流)。”
“通过让rasatom同时表示‘感觉’和‘意义’,prijaji贵族阶层已经能够对主观体验进行分析,其他一切都可以和它联系起来。一个人的情感成了一个人首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一切才能最终合理化。因此,情感的平静,即情感的某种平淡,是一种珍贵的心理状态,是真正优秀性格的标志。正如生命所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从动物群体的无序粗暴,到稍微优雅的农民,到超级优雅的prijaji。最后,通过神圣的国王,到看不见的、无形的、不可感知的,自给自足的上帝存在,因此感觉的形式各不相同,从基本激情的粗俗现实,到真正的prijaji的精神化平静,再到终极的rasa,其中的感觉只不过是意义而已。”

安格借了格尔茨这个例子来诠释他对语言与意义的关联方式的想法。“alus”和“kasar”这两个术语的符号学解读可以很宽泛,在经验中的一系列不同方面之间产生了标志性的相似和对立。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安格的著名理论探索之一)思考方式还为解读字面外意义提供了一个框架:如果分类中的行为符号是人所表现或执行的,那么事物的分类就为人的分类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些分类是高度定位的。正如格尔茨所说,它们是由传统贵族阶层 priyayi 制定的。它们在形而上学、诗歌和宗教的传统中会得到进一步阐述,其中,例如抽象名词 rasa,“感觉”“意义”将“真正的优秀品格”的表现与沉着、平静、控制情绪的精神联系起来,这些精神现在被视为“优雅”本身的基本属性,因此也是那些在特定场合被识别为“优雅”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
“言外之意”在世界上各个文化中都是有趣的现象,然而安格却持之以恒、兴致勃勃地研究它到底是怎样通过人类之间的交流起作用的。也许最终,我们都会发现安格探索的“言”与“意”这两个古老的母题,对我们的文明和社会的滋养。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