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文本:何为现实主义风格?
作者: 彭李菁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康斯坦汀·那卡西斯(Constantine Nakassis)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绅士。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所以只会在国际会议上见面。但因为语言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圈子小,每年也常碰上几次。如果是网上会议,会后他会发邮件感谢所有读他的书和文章并问他问题的人,不是群发是单独发(我就收到过好几次)。如果是线下会议,他是唯一一个每次发现有同分会学者没有在晚餐时出现便会问起的人。而且他每次都会让座给学生,为大家点菜分菜,抢着为学生们付钱。有一回,从分会场到就餐点的路上下雨了,他把雨伞递给了我。我跟另外一个学者聊一个问题太过入神,无意识地接过雨伞,完全忘了他就在旁边淋雨。我其实还穿着防水的外套,到了餐厅他那身非常漂亮的定制西装全部淋湿了。即便如此,他仍然忽略我的道歉,坚持让出主位给我(因为我在那群人之中最年轻),还在一旁为我分菜(是他的家乡菜希腊菜)。见惯了美国名校生态圈那些学阀教授们牢牢占据C位、众星捧月、学生抢着买酒的场面,康斯坦茨(那卡西斯教授坚持让大家都用昵称叫他)一直让人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可爱的存在。
对印度现实主义电影的研究
我特别说起康斯坦茨的为人是因为这与他治学的方式是分不开的。在二十多年来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田野调查中,他非常重视让本地人拥有自己的叙事权力。而在他掌握叙事的部分,他完全将其贡献给了政治哲学和人类学理论的推进,而几乎不带任何个人价值判断在其中。他没有划出一个田野调查点或推出一个理论定义,然后宣称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使得他的写作非常特别,一反几乎所有人类学写作传统。而他近五年来最专注去做的是关于“图像文本”(image text)这个概念的理论推演。除了发表在人类学期刊上的理论史梳理,他在《荧幕上/荧幕下》(Onscreen/Offscreen)一书中把关于图像文本的思考融合进了他对印度现实主义电影的思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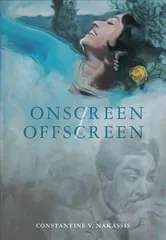
知识卡
康斯坦汀·那卡西斯虽然在多个场合说过希望把所有关于图像的讨论限定在语言人类学的学术框架内,以避免被拖进视觉人类学这个他自己并没有把握进入的领域。但其实他从来没有被拖进过视觉人类学,却被认为通过多年对图像的语言人类学的解读极大促成了语言人类学向符号学(尤其是传统中认为是欧洲主导的巴黎符号学传统)的开放。
康斯坦茨的目标是从对泰米尔纳德邦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研究中探索图像文本的本质,以用于更大规模的语域生成过程研究。具体来说,就是研究不同形式的言语/文本被一群语言使用者认可(指认)为说话者/作品属性的过程。安格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详细讨论了这些过程,认为语域不是关于语言的静态事实,而是语言使用的交互生成模型,通过交流过程沿着社会空间中可识别的轨迹传播。
“指意文本”与“交互文本”
康斯坦茨是语言人类学家阿西夫·安格(Asif Agha)的学生,所以他的学术训练包括许多在实时交流中如何实现生成语域(enregisterment)的思考。安格对语言人类学的贡献很大程度是帮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是怎样层层递进和交互指射的。如果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语言的,那么它绝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的。每一个指示符号都被某种意识形态框架影响,并被赋予意义和效力,而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与其他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从而与其他符号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理解任何事件和情境的方式都是通过实时生成的一种综合性的背景。
康斯坦茨把实时交流的时候发生的由语言和非语言事件共同写就的“剧本”称为“交互文本”(interactional text)。在一个交流过程中,如果“指意文本”(denotational text)是说出来的话和可观察到的行为,“交互文本”就是促使我们理解这些话和这些行为的即时情境。如果用《荧幕上/荧幕下》这本书中的田野调查例子来说,指意文本是一部部具体的电影和一段段具体的荧幕下的对话,交互文本则是拍摄过程、影片流通过程和受众观看和接受影片的过程。那么图像文本则是电影的风格,包括视觉效果风格和叙事逻辑风格(康斯坦茨一直强调图像文本不一定是视觉层面的)。对图像文本的研究包括了这些风格本身形成的社会历史,也包括了电影制作人和受众对这些风格的解读。
康斯坦茨非常热爱哲学,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这三位写的著作都极其难啃,康斯坦茨写的东西受偶像影响也时时晦涩艰深。有一次我忍不住向他抱怨他写的句子太长,每一句都塞进太多内容。他笑着说他也觉得自己的思考总是跑得太远,同时跑向太多方向,所以真正写下来的时候跟自己想的总有差距,所以对他自己来说也很晦涩。让我试着总结一下他对我解释的关于图像文本的思考:
图像文本是仅仅基于感性特质出现的符号,是人们对看到或想象中的图像的共鸣。这些符号可以形象化某些东西,可以是视觉的,就像一幅画,但它也可以是一首诗(正如雅各布森所说,诗学功能促成了“声音中的形象”),它可以是触觉的,可以是空间的,可以是气味。图像文本在皮尔斯哲学的意义上是一种通过类比表现的另一事物中的关系。交互文本是一种基于非指意的即时生成的语境;指意文本是指具体所说的、所叙述的、所提及的和所预测的。这些并不是真正不同“种类”的文本,而是同一个文本的不同的维度。毕竟,每一次叙事都是一个综合的事件或行为,而每一种行为都具有一种感性的诗意。反之亦然。
“诗意的想象”
在《荧幕上/荧幕下》这本书中,康斯坦茨讨论了作为一种已经被解读的风格存在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声称要表现世界(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虚构电影中,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种外延性主张。但它们的主张不是建立在现实中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培养对那个世界的感觉上,因此也是一种表现风格,也是美学和感性的。然而,不同的现实主义对这两个维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现实主义注重外延细节的忠实,有些注重可信度或合理性,有些涉及具有线性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外延文本的问题。但同样,每个外延文本都有一种美学。在这里,不同的现实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美学:幻觉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镜头眩光、摇晃的相机、自由间接的文学性言语等符号被常规化了。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所独有的,但它们可以被化为其风格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解释都缺少一个部分,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实用性是什么?它们起什么作用?被典型化为现实主义的文本是如何投射到互动事件中的?它们涉及哪些类型的社会指示性?这就是解读和接受的问题。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叙事或美学问题,它们具有实用性和政治性。
我曾经问过康斯坦茨,是什么赋予了符号“力量”。康斯坦茨说他不认为他能给出一个具体的公式,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在仪式、表演性演讲或引人入胜的艺术中,极其强大的符号似乎经常涉及这三个文本层次之间的校准。例如,表演性文本的符号意义叙述了交互文本的属性;但此外,表演性几乎总是发生在复杂的仪式空间中;仪式空间则组织在包罗万象的符号意义文本中(我们通过预设的神话来识别它们)和我们可以称之为仪式图像文本的诗学中。在法庭上,服装符号、空间布置、音景(法官面前的沉默、法槌等)是另一种图像文本可能产生力量的例子。在这些时刻,我们发现,在指意的、互动的和美学/图像性的文本之间存在共鸣,其中叙述的内容被付诸实践,被感知,而感性被卷入务实的当下,进入永恒的神话,等等。

安格的目的不是回顾这些讨论,而是详细阐述这些交互生成过程的一个方面:在任何社会传播过程中,语域模型都会经历各种形式的重新评价、重新类型化和变化。康斯坦茨的研究试图融入安格的探索,询问图像文本在遇到语域以及语域值随时间推移的维护和转变中扮演什么角色?安格认为如果不关注互动中语域使用的微观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语域的宏观变化。用康斯坦茨的话来说,我们一直在诗意地想象图像文本以调整我们自身,去对齐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世界。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