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视阈下刍议箪食瓢饮的颜回之乐与现实意义
作者: 陈怡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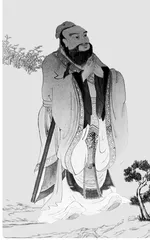
孔子善讲“乐”。《论语·雍也》篇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句话是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评价,他赞叹颜回“贫穷却不改其乐”,真是贤能。关于孔子提到的“贫而乐”,历代的儒家学者各有见解,后世对颜回之乐的研究和解读也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学者们对颜回之乐的看法和我对颜回人物形象的分析,简要谈谈我对颜回箪食瓢饮却不改其乐的“乐”的解读,颜回之乐乐在何处?有何可乐?以及颜回之乐放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一、历代儒家学者谈颜回之乐
关于孔子说颜回“贫而乐”的注解,历代学者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二。一说“乐”即为“乐道”。部分《论语》版本写作“贫而乐道”,汉唐儒学者也多把“贫而乐”的“乐”视作“乐道”,并为清儒所采纳;直至现代,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释义“贫而乐”即“虽贫穷却乐于道”,钱穆也在《论语新解》中提出“贫而能乐道”的观点。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颜回之乐在于“自乐”。这种观点的代表二程认为,颜回之乐不能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他们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据《河南程氏遗书》中载:“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矣。”程颐认为“以道为乐”也是一种功利,这是看低了颜回,真正的颜子之乐是一种自然行为,已经达到了人道合一的境界。另外,南宋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也将颜回“贫而不改其乐”的“乐”解读为“超乎贫富之外”的“自乐”。
对于颜回之乐究竟是“乐道”还是“自乐”的争论,接下来,我且谈谈自己的想法。
二、颜回之乐是否真正超然物外
首先,在分析颜回究竟乐在何处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颜回之乐是否真的超脱物质条件之外。不难发现,不论是“乐道”还是“自乐”,持不同说法的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便是颜回之乐不在于物质,而是精神层面甚至高于精神层面的。尽管处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颜回却不改内心的快乐,似乎他的乐确实与物欲无关。但进一步细想,颜回之乐真的全然超脱世俗之外吗?我觉得并非如此。其实孔子早已道出了颜回之乐的物质基础,那便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什么意思?“箪”是装食物的容器,“瓢”是装水的容器,意思是颜回吃得简单,住得简陋,人们从这个描述里感受到他生活的艰苦。但反过来想,箪食瓢饮正好能让颜回填饱肚子,居于陋巷能给他一个栖身之所,也就是说,颜回拥有的物质条件是能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所需的。
另外,我们从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中也能佐证这一观点。孔子谓颜回:“回,来!家贫局卑,胡不仕乎?”颜回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意思是孔子问颜回,你家境贫寒,为什么不做官。颜回回答说,城外的几亩地足够供给粮食,城内的几亩地足够种麻养蚕,每天拨动琴弦和学习先生传授的知识就足够快乐,因此不愿做官。由此可见,颜回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差到这么过分的地步。从另外的文献记载来看,颜回也并非人们想象的贫穷,他不仅有田、有闲、有书读,还有家、有室、有妻儿。试问一个人若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活下去都有困难,又怎么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问和道义呢?颜回是生活得比一般人清贫,跟财大气粗的子贡等人相比生活更是寒碜,但吃饱穿暖还是不成问题。所以不管是俗人还是圣人,不管“乐”的境界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甚至是齐物,没有任何人任何“乐”是可以完全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圣人也做不到不食人间烟火,最起码要拥有基础的生存条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满足生理需求,先谋生而后修身,否则再高深的精神理想也是空谈。
三、“乐”的几重境界与颜回之乐究竟乐在何处?
要搞明白“颜回之乐”乐在何处,首先要弄清楚“乐”分为哪几种,对应哪层境界。世人的追求不同,快乐也就不同。第一种境界的快乐是拥有物质条件的快乐,即对钱财名利的向往。世人忙忙碌碌大多或为钱财,或为名利,人们追求提高衣食住行的质量,从而获得满足物质生活后的优越感与满足口腹之欲后的幸福感。这种快乐也是最低级、最普通的快乐。第二种境界的快乐是比较与竞争式的快乐,分为与他人比较和与自己比较两种情况。在生活中,人们会不自觉地与他人进行对比,如攀比生活条件、学习成绩、生活质量等等,在和他人的竞争中胜出时的优越感会给人带来快乐。而与自己的比较则是成长型的快乐,就是当我在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地进步,相比于昨天的我得到了成长与收获的时候,就得到了另一种充实的快乐。第三种境界的快乐是精神层面的满足。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后,就会有更多精神上的理想与追求,会开始产生对人生、世界和自我价值的思考。我们会因为读到一本好书而欣然,因为获得他人的认同而快乐,因为实现了自我价值而充实,因为对生命的深度思考而感到满足。人们不再把目光局限于身体感官的享受,而建立了精神的信仰与追求信仰、寻觅真理的“乐”。学者们的第一种观点,把颜回之乐视作“安贫乐道”就属于这个境界,“乐道”即为追求道义而感到快乐,也属于是精神层面的追求。那么第四层境界也就是快乐的最高境界,无条件的快乐。前面三种快乐都是需要条件的,要依托于物质或精神的追求才得以存在,这种快乐真正做到了“心外无物”,快乐本身就存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论何时何地都呈现快乐的状态。因此这种无条件的“乐”也被称作“至乐”,二程所说的颜回之乐便是这种“人道合一”的至乐境界。他们认为道就在颜回心中,颜回之乐是与道合一后的自然流露。谈“乐”的四种境界,让我想到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论人生四境界,颇有趣味。他将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重。每个人生下来是自然孕育的产物,是顺应天性无社会意义的存在。随着人逐渐成长产生社会意识,融入社会的角色当中,开始认识自己和他人,产生功利的追求。再接着随着人受到知识教化、德育启蒙,在美好的道德与价值体系的作用下开始追求精神的愉悦、信仰的支撑,人与社会有了更好的融合。最后,极少部分人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达到了与宇宙天地共生的状态,除却对自我、社会、道德的认识,能做到顺应宇宙,自我觉察。我认为,“乐”的境界和人生四境界一样,也就是从自我到无我、超我的过程。
那么,我们再回过来看颜回“贫而不改其乐”的乐又是哪个境界呢?首先排除前两种情况,颜回之乐肯定不是“穷乐”,因为贫穷而快乐。颜回对生活条件诚然没有很高的追求,但贫穷本身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好事,这种清贫艰苦的环境也是他别无选择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条件。而颜回的贤能就体现在他处于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依然保持本心的快乐。《论语》中也有记载,子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如果富贵合乎道义就去追求,就算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可见孔子并不赞扬“贫穷”本身,赞扬的是颜回在面对困厄环境时的态度。因此,我们就排除了前两种物质层面的“乐”。再来看乐的第三种境界,儒学者们认为颜回的乐是“乐道”,即思想上对道义和“仁”的追求。他们认为颜回超脱了俗世“爱富贵”的境界,而把追求儒家最高的道义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他始终坚持力行孔子之道不辍,以精神的信仰和学问的求索为乐,忽视了生活贫富和物质享受。而二程为代表的“自乐”说驳斥了这种看法。程颐认为“若说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讲的是“圣贤之心与道为一”,反对把“道”视作一物。如果心与道为二,那就算不得颜回之乐。
这两种存在争议的说法,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孔子赞叹颜回“不改其乐”,真算得上贤能,可见孔子的乐与颜回的乐是相通的。对他们来说,“道”已经不是外在的追求了,而是内心的修养,忘记本体存在而与天道同一,便能怡然自得。正因为颜回达到了这种人道合一的状态,才能做到“三月不违仁”。这也和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同样的境界,因为道即本心,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约束。不过按照这种说法,由于“圣贤之心与道为一”,那么“自乐”也就相当于“乐道”,二者就没有了区别,所以可以说颜回之乐既是“自乐”,也是“乐道”。同时,二程的这个说法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待商榷的,比如他们的思想是完全的主观唯心主义,只关注到了绝对精神和天理,但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分析了颜回之乐也并非完全脱离物质条件而存在。
四、颜回之乐的现实意义
最后,讨论了从古至今学者们关于“颜回之乐”的争论,再来看看颜回之乐在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相反,谈颜回之乐的现实意义不用再深究颜回到底在乐什么,既然世上没有那么多境界高深的圣人,那么我们就概括出一些俗人看得懂、用得上的道理。“颜回之乐”最适用于大多数人的道理就是身处困境、逆境时要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牢记艰苦奋斗,用精神的投入、情感的寄托和理想的追求来面对生命遭遇的种种困厄。
现代人的“安贫”并非“乐贫”“守贫”,不是拒绝富贵,慵懒懈怠,做所谓的“躺平青年”,而是在已经身处恶劣的环境时能恪守非义莫为的道德底线,甘于寂寞、磨炼意志、修身养性,不屈服、不言弃。现代人的“乐道”则是热爱和坚守自己从事的学业或工作,不断领悟,不断渗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归根结底,“颜回之乐”对当今社会来说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信念,一种处世智慧。另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使得中国人形成了独有的价值体系。“安贫乐道”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涵养公民道德素养,促进人民精神富足,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弘扬和践行“安贫乐道”的思想,对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