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性角度解读现代诗教学
作者: 李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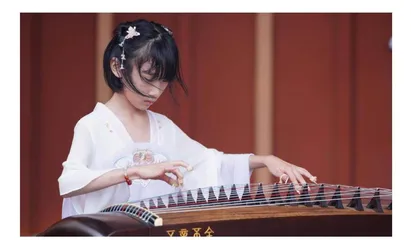
现代诗也叫“白话诗”,其创作有意打破古诗在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范式。这就使现代诗难以像古诗那样鲜明地体现音乐美。那么,教师教学现代诗时还要关注诗的音乐性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音乐性是现代诗重要的“生命体征”。本文从音乐性角度解读现代诗教学。
一、如何认识现代诗的音乐性
虽然现代诗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旧诗,但现代诗、旧诗作为诗的本质是相通的。闻一多在现代诗三美原则中首先强调的便是“音乐美”,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再别康桥》《雨巷》更是突出体现了音乐美。谢冕在《诗歌三题》中提出诗区别于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的基本点如下:一是它是从情感出发的文体,二是它是与音乐性有关的文体。他将情感性与音乐性视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标志。可见,音乐性是现代诗重要的“生命体征”,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深入认识现代诗的音乐性。
教师可以在课前导学单中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音乐性的基本概念。导学单可以设置三个学习任务。一是查一查诗歌的音乐性包含哪些要素。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发现诗歌的音乐性包含节奏、旋律和韵式三要素,与音乐三要素(节奏、旋律和调式)相似。二是说一说诗的节奏、旋律和韵式。通过教师引导,大部分学生能理解:节奏指自然、社会和人的活动中一种与韵律结伴而行的有规律的突变,在音乐或诗歌中指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这种现象是诗歌音乐性的主要体现;旋律在诗歌中指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若干诗节,是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运动,如诗人内在情感的起伏;韵式指词的平仄押韵情况,整体上具有不规则性,用韵没有固定的位置。三是想一想诗歌的音乐性我们要如何感受和捕捉。经过教师引导,大部分学生认识到,现代诗的音乐性可以从词句入手分析。比如,现代诗作品通常会对每个词的音节和韵律进行精确的编排,通过选择具有特定的音节结构和韵律规律的字、词,突出整首诗篇的韵律感;现代诗诗人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和要表达的内容,灵活地控制句子的长度和整体的节奏感;现代诗还常常采用一定的修辞手段,让诗句充满节奏感和旋律美等。
二、如何把握现代诗的音乐性
找一找诗的韵脚。现代诗不必像绝句、律诗那样偶句必须押尾韵,也不必押通韵或句句押韵,而是随着诗节的推进有意识地进行自由押韵,或押尾韵,或押中间韵,这样朗诵或吟唱起来会朗朗上口,自有音乐美感。如学习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第一节诗时,教师引导学生找出诗的押韵情况,学生基本能发现第一、二行的“车”“歌”押尾韵。教师提问:倒数第二行“勒进你的肩膊”,为什么不写成“勒进你的肩”?学生通过诵读发现,“膊”既与本节诗第三行的“索”押相近的音韵,又与第二节中的“朵”、第三节中的“脱”“涡”“薄”、第四节中的“和”以及全篇的“我”押同音韵或近音韵,也与每一节中“祖国”的“国”呼应(“国”并非都是句尾字)。这样,整首诗读起来一脉贯通、一气呵成,将舒婷对祖国炽热而深沉的爱喷薄为血脉里的歌。?
读一读词的音韵。叠词和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本身就具有音乐美,将其运用在现代诗创作中自然能增添诗的美感,还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诗人的情思。比如,学习戴望舒的《雨巷》,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找出“彷徨”“惆怅”等叠韵词和“彳亍”“凄清”等双声词,这些词语通过重复和回环强化了诗人内心的情感,表达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和忧愁?。学习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找出“轻轻”“油油”“悄悄”等叠词,感受韵律与诗意相合,并且“轻轻”“悄悄”都是第一声,重叠音读起来更轻、更柔,轻柔的音调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心中对康桥的这种柔情。还有,学习沈尹默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音乐性角度鉴赏,从富有音韵的词语入手分析这首诗。第一、二行中“呼呼”“明明”叠词成韵,“呼呼”突出风大、风猛、风肆意,“明明”突出月光明亮,更与上一句的“霜”照应。诗人不说“寒风”说“霜风”,使风因月光而有了颜色,将视觉与触觉融合在一起,凸显出天地间寒气逼人的景象。第一、二行的句式相似,暗示其表意的整体性。每一句最后一词结构相同,“吹着”“照着”“立着”“靠着”,读来朗朗上口,一行一个画面且具有蒙太奇的手法。
品一品句式的律动。我们可以从句式特点和修辞手法两个角度感受和品味诗歌句式的律动。诗人经常在运用多样化句式,既让读者感觉到形式上的视觉美,又让读者感受到音顿的节奏美,如参差错落的长短句,以及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倒装句等句式,这些句子与诗的情感律动相呼应,体现诗歌内外音乐性的融合。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叙事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都善于运用设问句和感叹句表达感情。外国诗也讲究音乐性,如华兹华斯的《致云雀》用“带我上,云雀!带我上云霄!”“快乐的生灵啊,快乐的生灵!”“你因它充满忧愁而鄙弃人间?”“地上露巢仍牵系你的心和眼?”等不同句式与情感呼应,流淌成一首炽热的歌。
现代诗诗人擅长用高超的修辞手法增强诗句的律动感。如,现代诗中顶针手法的运用使诗歌气韵贯通、衔接自然。如戴望舒的《雨巷》中“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等顶针的运用,使情感更具有黏合性,情绪一波未落,一波又起,密密织织,如一张细密的网将人笼罩其间。这种语言上的重复、复沓,听起来悦耳、和谐,加重了诗的抒情色彩。对偶或对比手法的运用形成前后照应,使诗歌浑然一体。如沈尹默的《月夜》,前两行属于对偶,“月光明明的照着”应与上一句“霜风呼呼的吹着”结合起来理解,体现月光如霜,突出寒意,而非月光皎皎就带给人喜悦。反复手法的运用构成一唱三叹、回环复沓,这有利于诗歌音乐性的呈现。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中“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反复手法的运用,让不舍与依恋之情回旋其中;海子在《面朝大海》中反复运用“从明天起”体现憧憬,引人深思;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每一节结束都落在主旋律最强音“祖国啊”身上,非常具有感染性。
教师引导学生感受和捕捉现代诗的音乐性,自然不止以上几种路径,比如现代诗内容的跳跃性是否表现了一种音乐的断章?如果我们把顶针、对偶与反复看作音乐连续性的体现,那么跳跃则是诗句与诗句之间、诗节与诗节之间的有意断裂、荡开,一如打击乐一样声断音连,由此实现字断意连或隔节情合,体现如音乐一般变化的旋律。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其实,一首诗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外在声韵与内在情感流动是相呼应的,但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感受诗人的情思和诗句的美好,我们才从技法上分析、阐释。
(作者单位:应城市开发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