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心灵
作者: 夏成 闻静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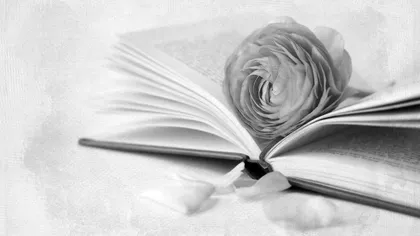
2023年12月20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要求各类、各级学校,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这是继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之后,我国发布的关于美育工作的又一重要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准确揭示了美育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对美育的实施范围和方法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深刻体现了美育在当下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文件特别强调了艺术教育在美育中的作用。的确,艺术教育在美育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注意的是,美育不仅仅是对艺术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在技能的学习中,发挥艺术对心灵的净化与提升作用。这一点在实践中常常容易被人忽视。 2023年的教育部文件特别强调,以浸润为美育工作的目标和路径,潜移默化地彰显育人实效。这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美育工作的开展方向,同时也为美育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的融合开拓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美育与语文教育结合的基础
《康熙字典》释“浸”,有三层意义,没也,渐也,润也;释“润”,也有三层意义,泽也,滋也,益也。结合在一起讲,浸润,就是让水缓缓地、温柔地包围生命体,进入到生命体的内部,以滋养生命体,促进生命体的成长。“浸润”这个词,非常好地表现出美育对于人的成长的功用和意义。以美育浸润学生,是让教育在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精神与身心,使他们的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马克思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
马克思的话深刻说明了艺术对人的塑造作用。在劳动的过程中,人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不仅得到了改变,精神世界也随之而改变。艺术劳动同样如此,艺术品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但是伴随着艺术品的创造过程,人的心灵得到丰富和提升;同时,艺术品在被创造出来之后,又不断反作用于人,培养具有懂得美、欣赏美的能力,心灵更为丰富的人。艺术对人的这种塑造实际上就是美育。
美育对人的塑造是独特的。有学者指出,人的素质提高需借助法律、道德和美育这三个必要的途径,法律是外在的行为规范,道德是内在的行为规范,二者都有强制性,而美育作为情感教育是一种内在的情感需求,是一种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自觉自愿的情感追求,具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力量。[2]潜移默化,浸润人心,这正是美育的独特性所在。
语文教育与美育关系密切。语文教育的材料以文学为主体。文学是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也被称为语言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创造形象、编织情节、创设意境,建构起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也具有天然的联系,“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3],这段文字生动地指出,从源头上讲,诗歌、音乐、舞蹈是一体的。先民和着音乐,边歌边舞。这一点与人类学家对澳洲和非洲原始部落的记载一致。在这些原始部落中,部落成员或和着音乐,或伴着节拍,以歌舞表达收获的喜悦和对神灵的感谢。上古的艺术不仅结合了诗、乐、舞,也结合了绘画与雕塑等艺术形式,场地的布置,歌舞者脸上的彩饰、身上的纹身,正是这一点的体现。为什么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同源性,根本原因是在于艺术的创造者、参与者在艺术中获得一种“审美冲动”,或者说“审美情感”。《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这生动描绘出审美情感在审美主体身上的萌发、发展直至完全显现的过程。“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等诗句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文学对人审美情感的激发。这种蓬勃的审美情感是一切艺术发生的起因和动力。
苏轼评价王维的诗与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现象屡见不鲜。小提琴曲《梁祝》是依托于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谱写的,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取材自史诗《埃达》和《尼伯龙根之歌》,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洛神赋》创作了《洛神赋图》,鲁本斯根据希腊神话创作了油画《普罗米修斯》。
另外,艺术体验最终要诉诸于语言进行阐释、交流才得以全面完成;在语言阐述艺术的同时,艺术赋予语言直观的形象和直接的体验。所以说,语言和艺术间具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得之于文学和艺术的密切关系,语文教育与艺术教育一样,具有美育功能。
美育与艺术教育密切相关,但是美育不是艺术知识教育,也不是艺术技能教育,虽然美育也须借助一定的艺术知识和技能,但美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是培育身心全面发展、健康完整的人,归根结底,它是要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因此,美育与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具有一致性。语文教育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历时长、分量重,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美育功能,不仅可以使美育事半功倍,也可以使语文教育的育人目的得到落实。
二、美育与语文教育结合的途径
曾繁仁认为:“美育可借助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的各种途径。”[5]自然、社会与艺术,这三种途径都可统一在语文教育中。
(一)由语文亲近自然
文学,特别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古典文学,与自然存在着水乳交融的联系。《诗经》中鸣叫的蛐蛐与雎鸠,《楚辞》中江离与辟芷,唐诗中的渡口、闪耀的月光乃至无声的青苔,宋词中的花、雾,明清小说中的江、湖和山林;无不昭示着大自然的魅力。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亲自然倾向。孔子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生命取向的欣赏,庄子对“天籁”的倾听,禅宗对“挑水砍柴”的认同,无不显现出人与自然的同生共构关系。
语文课程,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出发,将学生引入到真实的自然之中,让学生在真实、日常的自然中去体验月出日没、蝉鸣蛙唱、水流风逝、花开叶落中的诗意,形成与自然之间的审美联系;使学生的物理生命和精神生命在自然中共同成长,去塑造出一种优美、舒展的生命形态。在语文课程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的优美篇章,三峡的清峻(郦道元《三峡》),黄河的壮阔(梁衡《壶口瀑布》),庭院的清幽(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山川的秀美(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令人心随神往。即便是关于自然的一些片断,也让人心动不已。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被按住背脊就会放屁的斑蝥、人吃了可以成仙的何首乌、酸酸甜甜的覆盆子……不仅让儿时的鲁迅先生感到无限的乐趣,也让今天的读者产生深深的向往。在鲁迅先生对百草园的描写中,所显现的不仅是鲁迅先生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更是鲁迅先生对自然万物的亲近和热爱之情。鲁迅先生认识菜园中的种种植物、动物,能称呼它们各自的名字,也了解他们各自的特性,所以对它们的描绘非常准确。更重要的是,鲁迅并非仅仅出于获取新知的目的去观察事物的,他看重的,是一种“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的精神,[6]在这些平凡的事物中,鲁迅先生发现了美和趣味,这是文字的诗,更是生活的诗。这诗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共鸣,引导读者从文字中的自然走向真正的自然。在对自然的欣赏与融入中,人的生命会变得更加丰富、博大而浑厚。
(二)由语文亲近艺术
艺术等待着语言的阐释,也意味着语言常以艺术为言说的对象。艺术的门类众多,即便是在单独的造型艺术领域,也包括了绘画、雕塑、装置等多样的门类;而在绘画一个门类中,也包括了水墨和油彩、古典与现代等多样的形式与风格。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艺术形式。但是除了直接去欣赏艺术之外,文字也可以拉近我们与艺术的距离。虽然担心言不尽意,但关于艺术,人们还是写下了无数文字,去表现艺术动人的美。我们可以在诗文中听书、赏乐、观画、奕棋。在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表现艺术动人魅力的诗文。比如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凭箜篌引》、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张岱《柳敬亭说书》等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些关于音乐、舞蹈的诗文,不仅生动、形象而又简洁、准确地表现了艺术的动人魅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展现出了言说艺术的一种方式,即以艺术的方式去言说艺术。从对艺术的感观印象到理性思考再到艺术地表达,这实际上已经属于艺术鉴赏的领域。又如课文《月光曲》中,皮鞋匠兄妹聆听贝多芬的演奏,作者这样描写道: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这段文字不仅是描写鞋匠兄妹聆听贝多芬演奏时的感受和艺术所能达到的境界,而且它表现出了语言文字对艺术的显现功用。当语言艺术形诸于文字时,艺术所创造的世界才完全被看见。
(三)由语文亲近社会
中国文学一向有“诗言志”以及“文以载道”的传统,西方文学思想中,“模仿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些都反映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不是直接的,而是一种艺术的再加工创造,也因此,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对人的审美情感的激发而实现的。就义之前,林觉民写信给自己的妻子,阐明自己“以天下人为念,牺牲自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理念。林觉民说,天下不应该与家人分别,但是却不得不分别的人很多;他殉身于革命事业,正是为了更多的人可以与家人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信的结尾处,林觉民对妻子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林觉民《与妻书》),读到此处,怎能不让人眼含泪水?语文课程,向学生展示出广阔的世界和不同的人生选择。因为李陵之祸,司马迁面临着残酷的刑罚。死,对司马迁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活下来则意味着要忍受巨大的屈辱。但是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人生有限,只有将生命融入到更加宏大的事业中,才能让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地活着,并将自己的心血融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最终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人生,体现出了生命所能达到的恢宏与壮烈,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正是在这种对情感的激发中,语文课程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学生的心灵世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
文学与艺术具有同源共生的关系,二者有共通性,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在美育中,语文教育不能替代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也不能排斥语文教育。以美育为导向,让语文教育与艺术教育摆脱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的狭窄视野,让学生在艺术体验中领会艺术的情感、生命的价值,才能真正将美育落到实处,这对于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培养完整的、全面的人,实现美育的根本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2][5]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107页。
[3](战国)吕不韦编、(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本文系江西农业大学教改项目“新农科背景下农林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美育研究”(编号:2020B2ZZ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