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情境·素养
作者: 左高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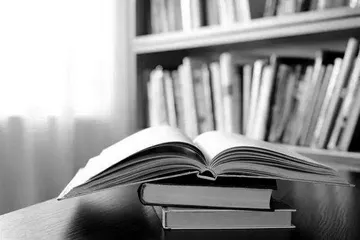
崔允漷教授曾指出,大单元不是内容单元而是学习单元,它是为改变知识点、能力点碎片化的教学现状而提出的,是一种有利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达成的新的教学理念。因此,大单元教学是教学理念,单篇教学是教学形态,二者并不排斥,单篇教学完全可以落实和贯彻大单元的教学理念。从教材编写体例和教师教学惯性角度看,单篇教学恰是实现大单元教学最常态、最适切的一种课堂教学形态。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颁布以来,基于统编教材的大单元教学实践已经广泛展开,然而,由于对大单元教学的认知存在偏差,大单元背景下的单篇教学存在一些实践上的误区。
一、大单元背景下单篇教学的三个误区
第一,脱离文本,另搞一套。许多大单元下的单篇教学轻视甚至忽视单篇文本的教学价值,只把单篇文本做一个背景甚至引子或幌子,虚晃一枪,将教学引向别处。比如,讲《江城子·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时,有的老师抛开文本研读,让学生进行话剧表演,模拟苏轼与亡妻见面的场景,二人互诉衷肠,相互吐露心声;学生表演很卖力,内容富有想象力,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整堂课气氛融洽,学生参与度很高。但是这样的课堂是否恰当?课堂教学内容与文本的关联有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课堂只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背景,整堂课所呈现的内容都与文本的原生价值无关也与教材“学习提示”蕴含的教材价值无关,更与诗歌文体的教学价值无关。
第二,虚设情境,远离课堂。大单元教学是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素养的达成需要“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的介入,然而,情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不能为情境而情境,也不能只为“真实”不为“有意义”,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的前提不是“真实”而是“有意义”,只有情境“有意义”,“真实”才会有效。例如,有教师在教授鲁迅的作品时,要求学生对鲁迅的作品作美学点评并汇集印刷成册。这个情境的创设确是真实,但是否有意义呢?不用说是高中生,即使是汉语言文学毕业的本科生,能否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情境任务?
第三,泛语文、非语文化倾向严重,语用素养指向性不明。当下大单元教学的课堂情境味十足,语文味不够。文本教学的语文课堂要上出语文味,其标志就是课堂教学的目标指向为语用素养。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素养,思维素养、审美素养和文化素养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语用素养的基础之上。[1]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思维素养、审美素养和文化素养都“姓语”。举例来说,同样是训练学生的思维素养,语文学科和数学学科所借助的载体就不一样,语文需要借助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来实现,数学则需要借助数学的逻辑和推理来实现。
第四,忽视大单元的目标统领性。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大单元背景下的单篇教学必须立足文本,并创设恰切的课堂情境,最终指向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尤其是语用素养的有效达成。只有这样来设计课堂,才能不辜负新课改的本意和初心。
二、大单元背景下单篇教学的三个要素
(一)文本
教材是以文本的形式来呈现的。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课一文,也有一课多文等不同的编选方式。但不管是哪种编选方式,文本都是我们进行课堂教学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载体;也不管把文本处理成定篇还是样本抑或例文、用件,教学中文本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因此,在文本教学中,尤其是单篇文本的教学中,要紧扣文本的文体特点来创设课堂教学情境,以此来实现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高效达成。
文本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制约下,基于作者的认知语境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篇语境,课堂教学就是在这种语篇语境中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所进行的一种言语对话。由此可见,在文本教学中,与其另辟蹊径创设课堂情境,不如紧贴文本,将文本的语篇语境还原或转换为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以《江城子·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教学为例,诗歌通常是借助个性鲜明的意象来表达作者内在情思的文本体裁,我们在教学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意象”这个语篇语境教学点,将其转化为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在该词中,“孤坟”和“明月”变异化特点鲜明、情感张力十足。因此,我们可以以“‘孤坟”和‘明月’描写的真实性”为话题开展“课堂教学辩论赛”,引导学生探究诗歌作品中意象与情感的关系,让学生学会“据象透意”的诗歌解读技巧,并初步达成用诗性语言表情达意的语用素养。笔者在教授此文时,就创设了这样一个紧贴文本特点的“辩论赛情境”,在辩论中,甲方代表认为“孤坟”和“明月”都是实写,亡妻之坟远隔千里(此时苏轼在山东密州),可谓是形单影只;正月十六月最明,想必正月二十的月亮也是明月。而乙方则认为,苏轼悼念亡妻之时,亡妻的坟旁早就有了苏轼父母的坟墓,三个亲人的坟墓是紧紧挨在一起的,并不是孤坟;从月历上看,正月二十是残月而非明月。从甲乙双方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边各执一词且各有道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辩论双方已经在无意识中思考诗中的“意象”和现实中“形象”的区别和联系了。如果在此时,教师能够顺势引导学生思考意象与形象的区别和联系,那么学生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据象透意”的问题。在笔者的引导下,学生们逐步意识到了诗中的意象是诗人情感对客观形象变异化的塑造,它并不一定现实物象的真实但一定映射情感的真实。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学生们便可以将此知识和能力迁移运用,比如,他们明白了“感时花溅泪”中流泪的并不是花而是作者,也明白了苏轼笔下“羽扇纶巾”的儒将周瑜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周瑜,他只是苏轼内心深处的一种英雄情结……甚至他们也读懂了郁达夫的秋为何是那样衰颓那样苍凉。学生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便可以带着这样的理解运用到自己的语言表达中去。比如,学完该文后,笔者布置了一个课后小练笔“用诗性的语言写自己眼中的一个景物”,有个学生写到了乌鸦,她是这样写的:“乌鸦通体散发着迷人的黑,黑色珍珠般的眼睛点亮了黑夜的光,他俯视着这片静谧的大地,偶尔一两句不掺杂一点取悦别人的叫声,那么自然而不加粉饰,那么堂堂正正地响彻在黑色的夜空中……”通常情况下,乌鸦的形象和声音都是不美好的,但是这位同学却写出来自己情感映射下的乌鸦,这是一个堂堂正正、不会敷衍谄媚的乌鸦,这正是学生精神追求的表现,也是学习诗歌文本后语言运用的真实表现。笔者认为这样设计的课堂才是真正体现了大单元教学理念的课堂,它紧贴文本创设语境,实现了学生科学素养的真实达成。
要之,大单元背景下的单篇文本的课堂教学一定要贴近文本,从文本的文体特点出发,既要教出“这一类”文本的共性又要教出“这一篇”文本的个性,抓住教学的主问题,既要做到“依体而教”又要做到“依体而设”,设计出贴近文本和课堂的教学情境,以此实现学生学科素养的达成和提升。
(二)情境
大单元教学与以往教学在实施教学的载体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境达成”,让学生在真实的有意义的语言运用情境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能力继而达成素养。虽然课堂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但是有些教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创设相应的真实的生活情境,以此来培养和提升学生将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素养。然而,情境的创设绝不可以忽略学情,创设一些远离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无意义的情境。基于此种理解,笔者认为,大单元背景下的课堂情境的创设一定要做到“以学定境”,也就是说要创设一些靠近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有意义的课堂情境。如果情境无意义,那么,再真实的情境也都是无效的。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学说中一条重要的信条便是“搭建脚手架”这一理念。儿童依靠成人的帮助搭建起自己伸伸手、踮踮脚就能够得着的学习支架,这对儿童的认知与心理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最近发展区”与“搭建脚手架”之间的关系在支架式教学这一教学模式中得到了最为真切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情境在大单元背景下的课堂教学中起到的就是脚手架的作用。由此可见,我们在创设课堂情境时一定要切合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避免所创情境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可望而不可即。
以《琵琶行》的教学为例。由教材“学习提示”可知,“赏析音乐描写和景物描写的妙处”应该是本文的教授重点,尤其是课文第二段正面描写“琵琶曲”的部分。有老师为讲授此段创设这样一个课堂情境:“琵琶女沦落风尘数年,忽然回心转意,打算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如果你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你在听完她的演奏之后,你会录用她吗?请你从专业角度给出你的理由!”此任务情境创设得十分新颖,估计该老师是想通过此情境来引导学生对这段音乐的描写作细致鉴赏分析。然而,此情境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琵琶曲的音乐造诣并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重点,我们是语文课,我们要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白居易描写音乐的妙处,而不是去分析音乐的妙处。第二就是,学生没有专业的音乐素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评价音乐,同时,学生的认知水平与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相距甚远,再说录取学生需要考量的因素有很多,这些都是远超学生实际认知背景的。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此任务情境的创设都远离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是学生伸伸手和踮踮脚都够不到的无意义的情境。
其实,学习《琵琶行》音乐描写的妙处,我们完全可以创设这样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琵琶行》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首正面描写音乐的诗歌,请你以‘《琵琶行》正面描写音乐的奥秘’为题写一篇推介词,学校语文组会择优选出若干份在校园广播站宣读。”此任务情境的创设既立足文本又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学生踮踮脚就可以够得着的,同时也是在落实教材“学习提示”的编者意图,是一举三得的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从实操效果来看,学生们普遍认为该段“叠音词”和“拟声词”的运用别具风格,与琵琶乐曲的缠绵悱恻丝丝入扣;诗歌韵律的变化与琵琶曲调的变化也达到了同声共韵的境界;音乐形象的塑造也独具特色,将无形的音乐以语言的具体化、立体化和可视化;甚至有的同学写到“此时无声胜有声”达到了“无理而妙”的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音乐是以声音为载体表情达意的,作为听众的我们欣赏音乐就是欣赏其优美的音律。因此,在一般生活常规之下,有声是胜过无声的;从生活实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无声的音乐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然而从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越是无声则越是有趣,越是无理则越是有情,也正因此,此句才能妇孺皆知、流传千古。
(三)素养
褚树荣老师在《探索与发现:实用性阅读与交流的津梁——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三单元学习任务设计(上)》一文中曾提出情境任务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素养旨归。[2]由此可推知,大单元教学与以往教学的根本不同就是目标指向的不同。新课标之前的单篇课堂教学主要指向知识点和能力点的训练,而大单元教学则是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达成和全面提升。新课标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即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和创造,文化的传承和理解。在这四大核心素养中,语言的建构和运用(以下称“语用素养”)是语文学科独自具有的一种素养,也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用素养应该是新课标背景下语文课堂教学最为主要的价值追求。然而,当下许多尝试大单元教学的课堂,经常是只见任务不见语文,空有情境不见语用,语文课变成了生命健康课、旅游管理课、影视训练课、道德教育课等等。
以《荷塘月色》教学为例。许多老师采用让学生绘制路线图的形式来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很明显这样的课堂教学不是以提升学生的语用素养为指向的。绘制路线图不是建立在语用素养基础之上的一种教学手段,它更多的是指向于思维素养和审美素养,因此,这不应该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主旋律。还有老师以组织朗诵比赛的形式引导学生对《荷塘月色》中优美语段进行美读品鉴,当然,这样的课堂是有语文味的课堂,但是在大单元教学的背景下,这样的课堂教学还是略显浅薄的。“语言的建构和运用”贵在“运用”二字,美读品鉴侧重于语言的建构而不是运用。基于以上理解,笔者认为,大单元背景下的教学尤其是单篇教学,应该在“语言的运用”上下足功夫。笔者在教授此文时,曾创设过这样一个课堂情境:“《荷塘月色》自发表以来,学界对其解读颇多,早期有叶圣陶先生在《朱佩弦先生》中的‘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不得那么自然,’后来有王瑶先生的‘早期散文的代表作,这些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再后来有余光中等人的否定看法。当然,不同学者由于其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荷塘月色》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你支持谁的观点?请你在叶圣陶和王瑶两位先生中任选一位作为你的写信对象,给他写一封信来表达你对《荷塘月色》的解读观点。”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福楼先生在《在语用中塑造“语文人”——基于“新课标”“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探索》一文中认为笔者在这里客观构建起一个话题讨论的语境,让学生与两位语文大家——叶圣陶与王瑶先生展开争鸣,从而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又以书信形式把读、写、思三者统合起来,引导学生在读写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凸显出语文学习的实践性。[3]
要之,大单元教学的目标指向为素养的达成,大单元背景下的语文教学尤其是单篇教学,其目标指向应该是语用素养基础上的综合素养的有效达成。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管是创设情境,还是专题教学,都要紧扣语用素养,坚持在语用中塑造“语文人”。
注释:
[1]左高超:《文体·学情·语用——高中语文情境任务创设的三个维度》,《语文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3期,第20页。
[2]褚树荣:《探索与发现:实用性阅读与交流的津梁——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三单元学习任务设计(上)》,《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2021年第5期,第42页。
[3]赵福楼:《在语用中塑造“语文人”——基于“新课标”“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探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3年第5期,第59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