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章开沅在求学路上厚植革命情怀
作者: 孙守让章开沅(1926—2021),安徽芜湖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1985年至1991年,他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一职,在学术上创立了章氏学派,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学术界称之为“章门弟子”。他的学术著作如《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在学术界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漂泊西南,锻造坚韧性格
章开沅祖上经营有产业,但是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道中落。家中长辈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章开沅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私塾教育,旧学功底非常扎实。他自小就喜欢读书,早早接触新学,阅读了不少报刊和书籍,如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丰子恺、谢冰心的散文,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等。
1937年,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章开沅一家为了躲避战火,历经艰辛的长途跋涉,是年初冬西迁到重庆。1938年秋,12岁的章开沅和他的姐姐、三哥一起进入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今重庆市江津区)的国立九中读书。国立九中专门招收外省流亡到四川的学生,以安徽籍学生为主。学校设立在村庄的祠堂里,办学条件比较差,但是师资力量雄厚,很多老师都是当时安徽中等教育的精英,有的还曾经在国立安徽大学执教。
1941年春,章开沅从国立九中初中部毕业,经过甄别考试,进入该校高一年级学习。老师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要求每周交一篇不限制主题和题材的周记,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章开沅向来喜欢写作,尤其喜欢摹仿鲁迅的笔法写作半调侃半讽刺的杂文,其间,他写了一篇题为《鸽铃》的周记,描绘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一些绅士手舞竹竿追赶鸽子,但这群鸽子依然自由自在翱翔高空。这是一篇随意率性的文章,体现年轻人喜欢幻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并喜欢把自己的理想、愿望通过文字表述出来,并没有考虑有什么政治寓意或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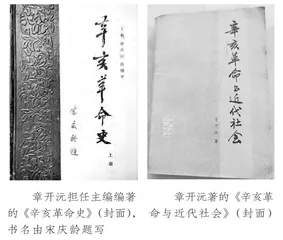
当时和章开沅一起读书的王姓班长是班主任魏老师的助手,协助管理班级,兼任国文课代表。按照一般程序,国文课代表将同学们的周记收集起来后直接交给班主任魏老师,魏教师看到章开沅的周记常常会夸奖他文笔好。但这一次国文课代表没有按照程序先将章开沅的周记交给魏老师,而是直接交给管制学生思想的训育处。训育处老师深文周纳,觉得章开沅的文章思想不纯,有政治问题,就将他的周记交给魏老师责令处理。魏老师审阅文章后大为光火,厉声呵斥章开沅:“你要自由吗?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并且号召全班同学揭发批判他。章开沅当时只有17岁,对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不了解,老师们强加给他莫须有的罪名令他十分不解。
到了暑假,很多同学都回家了,由于父母已经离开重庆到江西谋生,章开沅无家可归,只能留在学校宿舍里,却因周记事件被学校勒令退学,无处安身,只得去重庆投奔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读书的大哥章开平。章开沅后来报考几所大学都没有结果,他的大哥便设法请托一位有点地位的亲友长辈为他办理一张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证明,让他报考沦陷区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办的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救济流亡学生,让他们能够顺利就业,章开沅最终被该校录取。在学习期间,章开沅认真学习学校的专业课程,在课余大量阅读与专业相关的会计学、统计学和银行学等方面的书籍,并注重培养自身的人文素养。章开沅喜欢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里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等。章开沅在阅读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人道主义的了解,明晰了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
当时正处于全民抗战时期,中小学都有军训教官。计政专修班有两位军训教官,专门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平时的组织纪律。杨姓教官和章开沅关系不错,但他以权谋私欺负女学生,激起同学们强烈不满。有一次晨练站队,杨姓教官和章开沅因站立姿势引发争执,杨姓教官被揭发贪色老底。因为此事,杨姓教官怀恨在心,嫁祸栽赃针对章开沅,不久学校开除章开沅学籍。他再次陷入无学可上的境地,同学们体恤他的不幸,纷纷捐款,帮助他渡过难关。
章开沅离开学校后,因高中和专业学校都没有毕业,重考大学和就业都困难重重。在同学的推荐下,章开沅当过川江的纤夫、仓库的抄写员。在底层生活,章开沅体验到普通人生存的艰辛,也感受到底层人民的淳朴与善良,增长了社会见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金陵求学,追求光明未来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贵州独山,“西南门户”沦陷,贵阳危急,重庆形势也非常严峻。是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一寸山河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许多青年都积极参加青年远征军。章开沅和他的弟弟章开永一起加入青年军。不久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章开沅渴望上战场杀敌、血洒疆场的愿望未能实现,感到非常失落。1946年6月,他正式退伍。为解决青年军退伍后的出路问题,国民政府分别在若干地区创办青年军大学进修班,章开沅顺利进入进修班学习,并在一个月后领到结业证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还颁布了《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规定青年军在退伍之后,凡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可以免试上大学,上哪所学校,可以自主选择。
章开沅思量后选择了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一方面南京离家乡安徽比较近,回家探望父母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他热爱农业经济这个专业,而金陵大学这个专业比较强,加之他曾经在计政专修班学习过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有基础。但结果令他意外,最终接到的竟是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了解,他被历史系录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入学笔试的国文成绩非常优秀,写作功底扎实,在所有学生中特别突出。
金陵大学历史系建立于1924年,最有名的教授是贝德士,他是一位美国人,曾经在牛津和哈佛受过教育,熟悉欧洲、美国史和东亚史。他在校开设的课程有俄国史、西洋古代史、美国文化研究等3门课程,选修及旁听的学生很多。他的学生陈恭禄、王绳祖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陈恭禄擅长中国近代史,王绳祖擅长世界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和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近代欧洲外交史》均是深有影响的史学著作。金陵大学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倾向于近代史,形成自己的特色,即崇实考证、强调史料、史观多元、视野开放、关注近世的史学风格,章开沅一生的史学研究也大致承袭这种风格。
当时金陵大学仿照西方大学的体制实行导师制,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思想、行为方面进行具体指导,对这些情况详细记载并作出评价。陈恭禄是章开沅的导师,对章开沅的管束比较宽松,完全遵从他的个人偏好,只是告诫他,作为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听课的范围尽可能宽一点,不限听历史方面课程。章开沅遵照导师教导,不仅聆听本系老师的授课,如贝德士的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还聆听文学院导师倪青原的逻辑学、女子学院导师刘恩兰的地质学等。多方听课,提高了学习知识的兴趣,扩大了学术视野,让章开沅受益终身。

贝德士教授对教学非常严格,经常布置学生阅读参考书和撰写读书报告,常常利用周末举行家庭茶叙,轮流邀请学生参加,亲切地和学生讨论历史学方面的问题。他还利用这样的场合进行英语交流,锻炼和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当时章开沅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文学很感兴趣,但是苦于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难以深入钻研。贝德士对他的探求精神大为赞赏,设法办理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借阅证,帮他借阅书籍。
金陵大学经常举办一些高端讲座,担任主讲人都是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有一段时间在金陵大学兼课,他的讲课经常以讲座的形式进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著名学者梁漱溟、马寅初都来校举行过讲座,他们的讲座大多对时局有所评价;艺术方面有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到校举行讲座。章开沅都积极参加,深受影响。
章开沅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国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的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治,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满,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有光明未来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暗流涌动,金陵大学学生成立了一些进步组织,有些同学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团结进步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此时,章开沅经历诸多社会境况,认知不断深化,已经由一个自发的反抗者变成一个自觉的反抗者。他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在学习生活中,他勇于对现实作出批判,爱写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当时政治环境险恶,进步学生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后转送特种刑庭遭受虐待的可能,他决定离开金陵大学。
在紧张的形势中,部分学生中途辍学,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正当章开沅决定跟随进步学生奔赴前线之时,一位罗姓同学告知,他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希望和章开沅一起前往解放区。1948年11月,章开沅一行数人悄悄离开金陵大学,在南京下关乘船逆流而上,到达武汉。
中原大学,坚定理想信念
在武汉短暂停留之后,章开沅一行风餐露宿,冒着危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1948年底到达已经解放的河南许昌。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劝说他们不要急于参加革命工作,应该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们在开封有一所大学叫中原大学,校长是范文澜,他们可以先在这所大学学习,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情况后再参加革命工作。范文澜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不仅在解放区有很高的声誉,在白区也非常受欢迎。章开沅曾经购买和阅读过这部著作,对范文澜非常了解和崇敬。听说是范文澜担任校长,章开沅自然非常高兴,特别想跟范文澜先生学习历史,便欣然前往中原大学学习。
1948年5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进驻河南宝丰。当时,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校内分为左右两派,其中左派师生在范文澜的带领下前往宝丰,投奔解放区。为给新接管的解放区培养更多人才,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以从河南大学分出来的400多名师生为基础,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中原大学,并报请中央批准。是年,在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刘伯承宣布中原大学成立。

当时的中原大学是一所“抗大”式的短期培训学校,还不是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中原大学设置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党史基本知识、党的基本政策、社会发展史等,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培训,学员要养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了解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各项政策。章开沅入校就读时,中原大学已从宝丰迁到开封,办学条件艰苦简陋,住的是前清贡院破败的马棚,吃的是颜色发黑已霉变被学员戏称为“铁塔”的窝窝头。生活条件尽管艰苦,但是学员们革命热情高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情绪乐观,学习劲头十足。与章开沅一同来的4个人被编入第一分部第二十队,章开沅担任学习小组组长,负责组织组员学习和讨论。他们的学习培训只有4个月时间,每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他们除了上课、学习、讨论,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当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他们都会参加祝捷大会,下基层向民众宣传我军的胜利战况和我党的方针政策。由于章开沅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好的文笔,新成立的学生会宣传部聘请他担任墙报编辑。
章开沅在金陵大学时曾接触马列主义著作,对马列主义较有了解。当时大部分学员没有系统地学习甚至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不熟悉甚至完全陌生。第二十队队长牟政找到他,请他办一期墙报,向学员们宣传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正确地认识马列主义。章开沅根据队长的要求,自己撰稿和设计,办了一期生动活泼的墙报,受到大家的热情赞誉,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学校领导给予充分肯定。

1949年4月,在他们即将结业之际,中原大学副教务长梁维直为学员们作了一次政治报告。在报告会上,梁维直提问:“你们现在脑子里最想的是什么?”坐在第一排的章开沅脱口而出:“打过长江,解放南京!”梁维直哈哈一笑,看了眼瘦弱的章开沅说:“你一个人过江,恐怕蒋介石正好抓你。”这一句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他继续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以后你们不一定都要上前线了。中大的毕业生不会全部分配到部队,也要为经济、文化战线输送干部。”对于未能上战场的遗憾,到了晚年,章开沅还感慨道:“我是曾经受过系统化军事训练的,我当时3枪能打28环。”“你们说我这辈子怎么就成了历史教员,我其实是想打仗的啊。”结业典礼结束后不久,一部分学生被分配到部队,担任部队的文化教员,一部分学生被安排到部队机关担任行政工作。出乎意料的是,章开沅和一名叫王元圣的学生被作为储备教师留校,分配到政治教研室当实习教员,他们一边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边担任教学工作。
5月至8月中旬,中原大学分批南迁武汉,章开沅被分配到教育学院历史系教书。1951年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将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组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章开沅正式走上大学讲坛,为历史系、政治系和教育系学生讲授公共课程中国革命史,后来为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史。1953年10月,华中大学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又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作为一位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这所学校工作几十年,直到生命的终点,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当今学界的英才。在任期间,章开沅在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者,他身体力行,努力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彰显了一代大家的学术自信、文化自信和文化使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