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人生中的五次突围
作者: 刘中才鲁迅(1881—1936),以笔为戈,一生战斗,被称为“文化斗士”,他笔下作品的字里行间,总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走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鲁迅《幸福的家庭》)“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之中。”(鲁迅《且介亭杂文》)这些出自鲁迅笔下的言语有力地描绘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展现出他作为“文化斗士”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人格魅力和精气神。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不懈突围,为人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年少失怙与命运转折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鲁迅是以作家身份名载史册,而鲜少注重到,鲁迅还以思想家闻名,他因具有深刻而前卫的思想并强烈表达出对民族自强的渴望被誉为“民族魂”。鲁迅深邃的思想伟力,就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流年旧事,就像课桌上那个永远也擦不掉的“早”字,自民国迄今已经影响了几代人。
在成为20世纪民族文化战线上伟大英勇的旗手前,鲁迅同许多无所适从者一样,出场并不夺目。家庭的变故以及面对人生选择的两难境地,给青年鲁迅以精神重创,但同时也坚定了他终其一生摇旗呐喊的终极信仰。面对困境,鲁迅非但没有因噎废食,反而是一次次突破世俗的重围,终浴火涅槃。
年少时,鲁迅原本拥有一个优渥的家庭,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曾经做过江西省金溪县知事。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鲁迅自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祖父周福清为帮助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步入仕途,铤而走险行贿科场考官殷如璋(时任浙江恩科乡试主考),最终因为东窗事发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死缓),被打入死牢。父亲周伯宜也没能功成名就,反而在精神的打击之下很快病入膏肓,1896年抱憾而逝。这一年,鲁迅的母亲38岁,她的3个儿子(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均未成年。
家道的败落、生活的拮据以及外人的冷眼嘲讽,让鲁迅一家陷入困顿不堪的生活境遇,未成年的鲁迅陷入迷茫之中。所幸,鲁迅的母亲鲁瑞深知,沦为穷苦阶层的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倾其所有供鲁迅三兄弟继续读书。
初入江南水师
1898年4月,17岁的鲁迅经过多方了解,最终选择离开绍兴老家,前往江南水师学堂求学,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突围。
1890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在南京创办江南水师学堂,是一所专门培养海军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学堂制度参照天津水师学堂的办学理念,专业下设驾驶、管轮、鱼雷3科,课程分为堂课、船课,同时配备鱼雷厂、机器厂、翻砂厂、打靶场等多个实训基地。鲁迅看重江南水师学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录用的考生可以免费入学,在读期间优等生每月还有少量补给。这对于家道中落的鲁迅来说显得极为重要,毕竟免收学费可以解决鲁迅在物质生活上的焦虑,安心学习。二是鲁迅的叔祖周庆蕃是江南水师学堂的教习。有熟人照应,让在异乡年少的鲁迅遇事有依靠。

入学后,鲁迅被分配到轮机班,每日学习原版英文教材,同时练习轮船桅杆攀爬技术。这个专业并不符合鲁迅的期许。学堂的课程每周有4天是英文教学,对于英语几乎是零基础的鲁迅而言,根本无法适应,学习效果甚微。每天都要练习桅杆攀爬技术,对于当时身材矮小又身体羸弱的鲁迅并不好胜任。江南水师学堂的学习生活给鲁迅的印象并不好,他曾说道:“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
学校的环境与思想氛围更让鲁迅难以接受。比如,江南水师学堂的办学初衷是为国家培养高技能海军人才,但学校却因为有两个学生在水池训练时意外溺亡而把所有的水池都填埋起来,并在水池上面建起关帝庙,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邀请和尚行法事以求平安。这种混杂着科学与迷信的怪异思想环境,令鲁迅深恶痛绝。又如,学校里有些教员水平不高却大做派。让鲁迅最不可思议和愤慨的教学事件是:有个教授汉文的老师,竟然在课堂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还有的老师不知何为“社会”。
这种教学上出现的低级错误,让鲁迅无法建立起学习的信心。5个月后,鲁迅不堪忍受学校乌烟瘴气的教学环境,以退学的方式中断在江南水师学堂的求学之路。鲁迅初始的求索新知的愿望就此破灭,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以失败告终。
辗转矿路学堂
离开江南水师学堂后,鲁迅并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选择。凑巧的是,其时的江南矿务铁路学堂(以下简称“矿路学堂”)正在招生,这给迷茫中的鲁迅带来新的希望。矿路学堂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一所学校,由于矿路学堂新办不久,学校考虑到生源不足,招生设定的入学门槛相对较低。鲁迅初次应试便顺利通过,1898年10月正式进入矿路学堂地质班学习。
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是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培养将才为目的而设立的官办公学,福利好,学制短,毕业后的月薪最低可达16两。矿路学堂也遵从其例,待遇普遍优于其他官办学校,这些待遇强烈地吸引着鲁迅。
鲁迅所在的地质班开设的课程除了地质学,还包括外文、化学、算学、绘图等多门学科,学校有德籍和日籍外文教员,学习环境方面优于江南水师学堂。
在文化氛围相对浓厚的矿路学堂,鲁迅的学习势头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西方现代思想,外语水平也日益精进。矿务学堂的教材兼有德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3种版别,鲁迅此前在江南水师学堂有过近半年的英语学习基础,粗略掌握外文学习的基本方法,经过短期的系统学习后,他的外文水平进步极快,德文和日文可以做到熟练应答。在专业课的学习中,鲁迅对探矿、采矿、修路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地学和矿物学2门课程,学习热情一直不减,日后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开设的博物学课程,即与此有关。
鲁迅在矿路学堂的学业很顺利。据鲁迅同学张协和回忆,学校规定每星期作文1次,第一名赏三等银牌1块,每月月考1次,名列榜首者奖三等银牌1块。4块三等银牌可换1块二等银牌,4块二等银牌可换1块三等金牌。3年读书生涯里,鲁迅在矿路学堂的学习成绩相当出彩,首批入学的35名学生中只有他换得金牌。
鲁迅历经3年的勤学苦读,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破冰突围,1901年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在考试环节,矿路学堂采取10分制,从学校颁发给学生的“执照”(成绩单)上看,鲁迅的7门主干课程绩点均在8.5分以上,而且没有出现偏科的现象。鲁迅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广泛涉猎书画艺术,积极参加户外实践,为他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东渡日本留学
鲁迅在矿路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成功实现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突围。他本可以成为地矿领域的一名专业技术人才,假以时日,未来的中国地学史上或许会留下周树人这个名字。20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之风甚浓,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获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加之不安于现状的渴求之心,考虑再三,他并未踏上实业救国的道路,而是选择继续深造,就此开启他人生道路的第三次突围。
1902年3月,在江南督练公所的筹划下,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鲁迅等人东渡日本,以期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实现国富民强的强国夙愿。在同行的6人中,除了鲁迅,还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后来历任浙江、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教育家伍崇学等。
东渡日本后,鲁迅先是在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即日语学习速成班)补习日语。其间,他结识了后来与其相伴一生的文学挚友许寿裳。半年之后,鲁迅日语水平大有长进,正式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仙台医专”)学习医学。

然而,留学并未让鲁迅收到预期的结果。鲁迅因性格之由,更因恶劣的学习环境,他的做派不同于其他留学生,这使他常常陷入自我沉默而无法静心学习做事,导致学习成效不理想。从鲁迅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后来公布的课业成绩看,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境况的确不尽如人意,多数课程成绩都在60分左右,其中最重要的解剖学只有57.3分。
在日本苦熬4年后,鲁迅最终放弃在仙台医专的求学之路。1906年6月,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前往留日学生聚集地东京,将学籍转入东京独逸语协会下设的德语学校。
当时仙台医专施行4~5年学制,鲁迅因未在规定学年内完成学业,无法拿到仙台医专的毕业证,没有行医资格。至此,鲁迅人生中的第三次突围没有给他带来所谓惊喜,反而突围陷入困局。
对传统婚姻的温和反叛
鲁迅到矿路学堂求学不久,二弟周作人也随之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读书。鲁迅东渡日本之时,只有三弟周建人留在老家陪伴母亲鲁瑞。彼时鲁迅已经25岁,独自一人远在异国过着单身生活。
作为家中长子,母亲鲁瑞高度关注鲁迅,对他的个人问题深感焦虑。为让儿子回到身边,鲁瑞不断托人给鲁迅张罗婚事,在事情敲定后以身患重病为幌子,一纸书信将鲁迅从日本骗回浙江绍兴。
这门带有欺骗性的婚事对鲁迅而言是心存不甘的。鲁迅作为较早接受新潮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婚姻上崇尚自主选择。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鲁迅最终只能遵从母亲心愿,违心地与传统女子朱安完成名义上的仪式结亲,实际上两人毫无瓜葛,结亲仪式后各自回归本来的生活状态。
据周家的长工王鹤照回忆,鲁迅结婚当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是在书房里睡,印花被子的靛青把他的脸都染青了。对于这段婚姻,鲁迅曾向好友许寿裳倾诉,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他只能好好地供养。
违心结亲,让鲁迅心里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考虑到朱安的处境,终其一生,鲁迅未与之离婚,但内心坚守着对现代婚姻自由的新式观念,两地而居,各自生活。这算是鲁迅以温和的方式对抗他人生中的第四次突围,他从未放弃为自己呐喊。
最后的勇士
当鲁迅的终身大事尘埃落地后,他旧梦重拾,再度离开绍兴老家东渡日本深造。其间,鲁迅一边自学,一边校对书稿赚取稿费用以补贴生活所需。然而,零星的翻译和文稿校对费时费力,稿酬却十分有限。1906年,二弟周作人也赴日本留学。190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但收益一般。
同年4月,曾在日本一起留学的好友许寿裳学成回国,旋即前往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4个月后,许寿裳给尚在日本东京聊以度日的鲁迅寄去信函,邀请他回国赴浙任教。
对鲁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外游历7年之久的鲁迅经过再三思忖,同意许寿裳的盛情邀约回国,入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成为一名生物化学课程教员。自此,28岁的鲁迅拥有了平生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也是他在学业和婚姻上共经历4次遭遇瓶颈后的涅槃突围。
1910年,鲁迅的祖母溘然长逝,家中境况更是日渐式微。10月,鲁迅因不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夏震武尊孔复古的教学思想,愤而辞去教员一职,复回绍兴老家,出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课教员。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工作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委任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相继设立陆军、海军、内务、外交、财政、司法、交通、教育、实业等9个部门。教育上,孙中山力邀章太炎拔冗出任总长,后因章太炎婉言拒绝转而由蔡元培代替。蔡元培上任伊始便开诚布公广罗人才,许寿裳、陈衡恪均被蔡元培揽入麾下,许寿裳任教育部佥事。当蔡元培从许寿裳处得知鲁迅是自己的老乡,又与陈衡恪等人同是留日回国的学生,便邀请他北上任职。鲁迅在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工作不到1年,就辗转南京、北京两地,进入教育部任职。这一次,31岁的鲁迅在人生之道上再次成功突围。
历经5次突围,鲁迅的人生彻底逆转。1912年春至1926年秋,在14年的教育生涯里,鲁迅的收入逐年攀升,工资由最初的每月60块大洋涨到360块大洋。生活步入正轨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进一套三进式四合院,实现了家人团聚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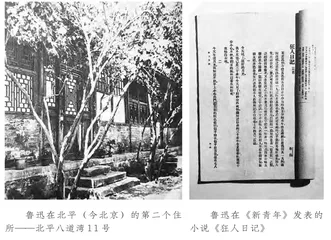
鲁迅在教授生涯及文学创作上双开花。1920年至1926年的6年时间里,鲁迅先后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8所学校的兼职教授。
1918年5月15日,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在北京《新青年》杂志第四卷5号发表,近代白话文学之先河自此开启。《彷徨》《呐喊》相继出版,收录在《三闲集》和《二心集》的文稿陆续公开问世。在大师辈出、众星云集的民国时期,鲁迅犹如一束耀眼的亮光,照彻大地。他的文词犀利尖锐,思想深刻卓远,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直插人心让人痛醒。
1926年底,因政治风波和遭人排挤,已在北京生活、任职14年之久的鲁迅决意离京南下。他先赴广州,后又颠沛抵达厦门,几经辗转最终落脚上海。其间,鲁迅或是教书育人,或是著书立说,在漫漫长夜里,他以笔为枪,针砭时弊,谱写着以文载道的时代华章。
1936年,积劳成疾的鲁迅带着未竟的心愿与世长辞。在与命运抗争的55年里,鲁迅始终以中国文人墨客的风骨一次次突破自我,成为集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于一身的“文化斗士”,直面人生的种种困境。犹如他自己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