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刻本俗字释例
作者: 彭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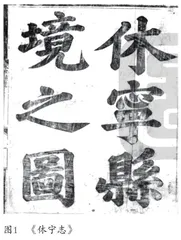
一般俗字能够在字书中或者通过字形直接判断出其正字。还有一些隐形的俗字,它们虽然在各种字书中都有相关解释,但是往往难以统一,而且这种俗字与其正字的联系较远,字音字义已经出现了分化,不利于判断该俗体的正字。人们不知道这些隐形的俗体字由哪些正字变化而来,且字书中的释义并不完善。文章选取明弘治县志刻本中五例隐形俗字进行溯源分析,以助完善相关字书释义,帮助阅读明代相关文献。
文字具有生命。从甲骨文到如今的汉字,文字的发展从未停歇,文字是“活”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其发展速度不同。到明代,汉字形体已完全成熟,但成熟的汉字中仍然存在大量俗字,俗字的存在可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字现象,尤其是碑刻、刻本之类,可完整保留当时文字面貌。有些俗字与正字之间的关系明显,使用者能够准确判断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使用相应的字形,但是有些俗字与正字之间的联系较弱,使用者不能快速准确地识别,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用法,阻碍阅读,而对俗字进行溯源分析有助于了解字际关系,清扫阅读障碍。文章选取了明弘治年间的刻本,俗字释例主要集中在《休宁志》《汀州府志》《崑山县志》中(如图1~图3所示)。方志记载的是一地之史,对于了解当时风俗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文字记录语言,刻本更能凸显明代用字现象,其中一些不能直接辨认的俗字阻碍了阅读,故对此俗字进行溯源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刻本,掌握当时文字发展情况。下面对明弘治刻本中出现的五例隐形俗字进行溯源分析。
一是,:“自黄太史表其俗之可悦,遂得专江西,至今争诵其赋,以鼓舞其国风。”(《休宁志·卷一》)
《正字通·女部》:“媺,与‘美’同,从女,从。”《集韵·上声·旨韵》:“媺,善也。通作美。”
按:《说文解字》和《篆隶万象名义》中均未收录“”字,“”应是“媺”的讹字,而“媺”则由“媄”字发展而来。“媺(媄)”本义指“色好”,如《九歌·少司命》:“望媺人兮未徕。”后因字音字义相近而与“美”相混,《说文·羊部》:“美,甘也。”故“媄”也可用于表“味好”之义,后代字书也将“媺”释为“与‘美’同”。然而对于字书的解释,我们不易将“媺”与“美”的形、音、义联系起来,“媺”作为“美”理解的构形理据亦不显,释“媺”与“美”同,盖后世混用所致。实际上,“媺”是“媄”的俗字,汉字发展既有简化,又不乏繁化之例。《说文·女部》:“媄,色好也。”《说文》认为“媄”中的部件“美”兼表义,“媄”亦可看作“美”的后起分化字,为突出其含义而增加义符“女”。《篆隶万象名义·女部》:“媄,妄几反。善也,色好也。”此处“媄”包含了“美”的义项。《新撰字镜·女部》:“媺媄妍,三字同。”因“媄”作为“美”的后起分化字与“美”混,导致与“媄”同的“媺”也与“美”同,三者之间“媄”与“媺”的联系更紧密直接。“媺”是后世用“”代替了声符兼义符的部件“美”作声符,“”的初文是“微”,属明纽、微部,“美”属明纽、脂部,同属明纽且微部与脂部都属于阴声韵[-i]韵尾,二者具备作声符的条件,故而出现“媺”字形,“媺”应为从女,声的形声字,从“媺”到“”则为构件变异而成。故“媄”到“”的变化路径应为:媄—媺—。
二是,:“辛丑郡守布伯廉等,勉请儒力整葺齐舍,朱震雷独建文公祠。”(《休宁志·卷一》)
《集韵·平声·豪韵》:“襃,博毛切,《说文》:‘衣博裾也’或作褒、。”
按:“”作为“褒”的俗体存在,义为“衣襟宽大”,但“”形中构件“”的音义不明显,且在后世的演变中“”变为“臼”,更不能联系其字音字义。《汉语大字典·衣部》:“裒,注音pou,阳平,义为聚集。又注音bao,阴平,与‘襃’同,义为衣襟宽大。”然《汉语大字典》收录“裒”字作为“襃”的俗体,未能说明其构形理据。“襃”的最初字形应为“”,《正字通·衣部》:“,襃本字。”后世可能为字形整体美观将其改写为“”(襃/褒),将上部的“手”形移到左边,《增广字学举隅·卷二·正譌》:“,襃帖,褒,非。承作。襃,报平声,扬美也。”“”因字形相近而误写作“襃”或“”,“褒”应释为“从衣,保声”,从“”到“襃”或“褒”,既存在因形体相近而误写的情况,又存在强调其声符的意味。《干禄字书·平声》:“褒,并正,多用下字。”从“”到“裒”的变化则属形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褒”与“”之间的演变关系,以及“裒”在《汉语大字典》中的释义原因,从“”到“裒”的变化路径应为:“—(襃/褒)———裒”。
三是,蕊:“大块流耸而为山水,化工发荣而为花蕋(蕊),是两间自然之侈。”(《休宁志·卷二》)
《新撰字镜·艸部》:“蕊,如藟反,草木实莭(节)生也。”
按:“蕊”字并不是其初文,“蕊”不见于《说文》,《篆隶万象名义》中作“”。在《说文》中可以找到与“蕊”相近的字为“惢”,《说文·心部》:“惢,心疑也,从三心,读若‘琐’。”“惢”属于会意字,义为心怀疑虑,在后世《字汇》中释“惢”为“从三心象形别做甤,繠通,俗作蘂蕊橤。”因“惢”别作“甤”,音rui,其音与“繠”相同,故二者相通。从字书中的释义可见“惢”的义项增加了,既表“心疑”又可表示“花蕊”,可将“惢”视为“蕊”的初文。后为了与表“心疑”的“惢”区分,将表“花蕊”的“惢”增加了义符“艸”或“木”,《集韵·上声·纸韵》:“蘂,艸木花或作蘂,通作橤。”增加“木”作义符的“橤”“蘂”字,在字形上常与表“下垂”的“繠”字相混,以致后世常将“繠”用作表“花蕊”义。“繠”字甚至为了强调此义项而增加义符“艸”,写作“”。《字汇补·艸部》:“,如水切,音蕊,花须也,又垂貌。”然“繠”最初是表“下垂”义,《说文·心部》:“垂也。从惢糸声。”“繠”不是“蕊”的初文,“繠”从糸声,与“蕊”的音有所不同,“繠”后产生“花蕊”义应为形误。“蘂”字产生后因其表义部件繁多又减省为“蕊”,故“蕊”字变化路径应为:惢—橤/繠—蘂/—蕊。
四是,觔:“蓝靛九百九十二觔八两。”(《崑山县志·卷一》)
《正字通·角部》:“觔,与筋同,后人讹以为斤两之斤。”
按:在《说文解字》和《篆隶万象名义》中皆未见“觔”字。“觔”应为“筋”的俗字,在后世使用过程中,因其字音与“斤”相同,从而借来表量词“斤”,如例句所用。“筋”应为“觔”的本字,而作量词的“觔”则是其假借义。然从“筋”到“觔”,其中间亦存在一个过程,现“觔”字的构意不明显,不论是作“肉之力”还是作“量词”来使用,皆需要对“觔”的形体来源进行分析。《说文·筋部》:“筋,肉之力也。”古代汉字中“月”与“肉”的形体常混用,在近现代从肉者多作“月”旁,如“胖”“胃”等,故由“筋”产生了“”这一俗体。《类篇·部》:“,肉之力也。”“”字中的部件“肉”在书写上讹为“角”,故“”字也作“䈥”,《干禄字书·平声》:“䈥,上通下正。”“筋”属于会意字,其构件皆表义,于“筋”从竹,许慎认为“竹为多筋之物”,然对此种说法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筋是附着在关节上的,而竹子是多节之物,故“筋”从竹。这种说法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且不论“筋”从竹的来源为何,对于“筋”本身的形体来说,其表义构件过多且从竹之义不显,而“筋”已有多个义符,为了书写更加方便,故将“竹”部省略,“䈥”也写作“觔”,《字学三正》:“筋,俗作觔。”“觔”与“斤”同属见纽欣韵,在某些情况下,“觔”则借用同音的“斤”字字义,表示“斤两”,如例句。《新九经字样·月部》:“筋,音斤,也作䈥讹。”《字鉴·平声·歆韵》:“筋,举欣切。”此为“觔”表“斤”之来源,故“觔”的字形演变路径可为:筋——䈥—觔—斤(假借)。
五是,砦:“集结愈众,诸砦不能禦,晏乃因黄牛山傍自为一砦。”(《汀州府志·卷二》)
《字汇·宀部》:“寨,与砦同。”
按:“砦”的本字应为表示“用于防卫的篱笆或栅栏”的“柴”,后因砦(柴)在字音字义上与“寨”相近而混。《说文·木部》:“柴,小木散材。从木此声。”“柴”的本义是“枯枝”,属崇纽佳韵,音读平声,后引申为“篱笆或栅栏”义,在字音字义上与“寨”相近,同属崇纽,表示“篱笆或栅栏”义,故读平声的“柴”误读为去声的“寨”,在此字义上,“柴”可作“寨”的俗体。《说文解字注·木部》:“柴,师行野次,竖散木为区落,名曰柴篱。后人语讹,转为去声,又别作‘寨’字。”后表示“篱笆或栅栏”义的“柴”为了与“寨”区分,增加了义符“土”或“石”,起到增强字义的作用,写作“”或“”。《五音集韵·床纽》:“,藩落也。”《集韵·去声》:“柴砦,藩落也。”义符的增加让“”具有两个义符,后为简省且与“寨”区分,分化出“砦”形。《类篇·石部》:“砦,仕懈切,藩落之。”《正字通·土部》:“,俗‘砦’字。”同书石部:“,俗砦字。”“砦”字作为“柴”的后起分化字,义为“栅栏”,与“寨”同,故字书常以“寨”释“砦”,后“砦”受到“寨”的影响引申为“寨子”“营垒”,如例句。“砦”作“寨”理解,从字形与构造上看二者联系并不紧密,若对其进行溯源分析,则能看出此义的来源。“砦”的演变路径可为:柴—/——砦—寨。
文章对出现在明弘治刻本中的“、、蕊、觔、砦”五例汉字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字书中对这五个字都有记载,但是各本字书的释义并不相同,存在释义不充分的情况。字形变化会导致后起俗字或异体字不易辨认、构形理据丧失会导致汉字辨认困难,但有些汉字则可以通过溯源分析来找出其所失去的构意。当俗字字形与其正字的形体差异较大时,往往不能准确联系,需结合上下文对该俗字字形追根溯源,若字形之间不能正确对应,则在阅读古文献资料时亦会受阻,有时查找字书也不能即刻分辨其关系,因此俗字分析工作实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