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视角的“大一统”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承异性
作者: 唐宇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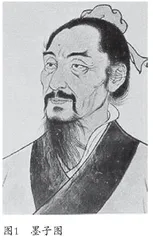
“大一统”研究大多以中原为中心进行理论建构,文章采用复线历史分析方法中承异的思想框架,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视角切入,找寻主线历史之外的历史碎片,并对历史碎片背后的意义进行解构,在分析和研判基础上,找出在历史碎片中对于“大一统”体系的话语叙述。这些话语体系中有着内在的联系和源流,对推进“大一统”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现今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整体结构是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中逐步构建起来的。如果单从“大一统”理论出发来看待历史,实则更多的是考察“大一统”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与整合性,用其来分析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理论框架难免过大。因此,遵循历史的单线进程固然重要,但主线以外的历史碎片也同样不容忽视,对其加以论证更加具有说明性和学理性。
何为“大一统”话语体系的承异性
从历史中找寻研究材料,遵循主线历史行径,不难发现历史结构性叙事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性。杜赞奇指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作认知的透明媒介,而不是将之看作一种话语。”朝代的更替,帝国的崛起与覆灭,一个又一个周期性的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封建王朝,这种历史周期律既造成了历史的相似性,又造成了朝代更迭所带来的断裂性。而复线的历史结构分析法,就是为了排除断裂性给历史造成的影响。为了将历史的碎片从散落的空间中抽离出来,杜赞奇创造了历史的“承异”概念,“承”是指传承,“异”是指异见。他把这种承异的叙述结构带入文化材料的分析中,看重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之外被消灭掉的或是被加以利用的叙述结构以及散失在空间中的历史印记是如何被用来构建成为线性历史的。
如果在复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北方各民族在日常与中原互动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话语体系中有被压抑或是被替代的关于“大一统”的话语体系,以及这些话语体系所展现出的目的性与连续性在“大一统”过程中产生相似的历史作用,那么无疑能够证明“大一统”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演进
关于“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和概念,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与吸收的理论体系,“大一统”的思想可以向秦以前,一直追溯至五帝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其思想中已经衍生出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观念,这种“大一统”的权力结构性框架,是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的。春秋时期出现了“中”的概念,谓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学界普遍认为“大一统”观念作为一个正式的理论体系是在董仲舒时期提出的,他将242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至此,“大一统”中关于华夷一体的思想体系就在此时日趋走向成熟。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划分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结构与现代民族识别后的结构差异较大,按照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的划分,主要的少数民族有十一支源流,其中大多数族裔在历史长河中已经不断地分化和融合成为我们现阶段看见的各个少数民族,以汉族居中的格局为基础,几大少数民族又分为南部派与北部派。北派诸族有匈奴、鲜卑、丁令、貉以及肃慎。居北部的少数民族大多以游牧为生。
对北方诸族关于“大一统”话语体系的探究
在北方几大少数民族中,匈奴与中原地区发生关系较早,并且来往交流最多,匈奴人较早被称为“荤粥”,《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在与汉人互动的过程中,除战争袭扰边疆之外,匈奴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和亲”。刘玉堂站在西汉的角度,认为和亲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的历史过程,其始终以和亲双方的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尺度。当把和亲政策作为一种双方话语体系的建构时,站在西汉的角度看,其成立初期,国力衰微,与匈奴和亲是为了求边界太平,当然这只是和亲的表象。其实和亲是西汉的一种进攻性的同化政策,实际上达到的目的是兵无一战以渐匈奴。而从匈奴的角度来看,虽然其表象也是以和为目的,但是匈奴并没有放弃对汉朝边民的骚扰和掠夺。
在匈奴入主中原之后,刘渊建立起的第一个匈奴国是汉赵帝国,此时对于和亲的话语体系就明显有着朝政治合法性以及匈奴与汉人的统一性、平等性上靠拢的趋势。冯世民指出,此时的匈奴在中原建社稷和宗庙时,希望不断在血缘关系上与汉室正统发生联系。由此可以看出和亲政策背后,实际上是具有一定姻亲关系的话语体系,而匈奴正是借着这样一种叙事来打起恢复汉室的旗号,进而入主中原企图完成“大一统”。从以上这些历史碎片中,我们已经能够隐约地感知到匈奴与汉人之间的文化边界伴随着政治权力的运作,实际上已经慢慢地不再清晰,匈奴没有抗拒汉人的文化叙事,而是不断地继承前人的叙事方式,又使之运用到自己的身上来构成新的话语体系,这本质上就是对于匈奴和中原文化碰撞融合的一种传承与赋新。
鲜卑,作为北方又一大民族源流,在三次西进和南迁的过程中,和匈奴有过一次较大的融合,1世纪末期,南匈奴南下,北匈奴向北迁徙,此时的鲜卑与匈奴发生了融合,“匈奴留者十余万落,悉自号鲜卑”。鲜卑就在今河套地区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在族源上,鲜卑人同样也把自身的身世托在三黄五帝之中,“黄帝以土为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样的一种话语体系,为和汉人的族源相联系来证明正统性的表达方式,在鲜卑以下的各分支尤为明显,同样《周书》中把宇文氏部落的族源托在炎帝之下,且契丹一直被视为宇文后人。各族在构建“大一统”秩序的时候必须对族源的正统性加以论述。其中,也有类似于感生神话的色彩,“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在鲜卑人建立政权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国号的变更这一历史叙事对于两种文化的整合起到了推进作用,鲜卑人最早以“代”为国号,源自“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入主中原以后,将国号“代”改为“魏”。何德彰在论述北魏国号与正统一文中,解释了改国号的意义所在,即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已让与北朝,北朝文化逐步成为正统体系。当然这种做法北魏并非首例,如刘邦打的旗号就是“兴复汉室”。这就是一种对于“大一统”话语建构中承异性的体现,高度相似的历史在某一时段会被人们再次提起并运用,从这些散落在主线外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其中的关联。
丁令,这一古老的民族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的时间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该民族鼎盛时期是在南北朝、隋、唐之间,其在当时被称为“突厥”。
突厥与隋、唐之间基本上是以附庸关系为主的一种统治。在630年,唐太宗遣李靖破突厥后,就有了“天可汗”的称号。古霁光就指出“皇帝”与“天可汗”这两种称呼实则已经表明了唐代统治的二元性。《通典》载:“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站在突厥人的角度上,尊称唐王朝的统治者为天可汗,实则更多的是一种寄人篱下的委屈求全,因为西迁的突厥人对于天可汗的称号并不认同。在维系这种关系的情况之下,话语体系从“舅甥”关系变成了一种“父子”关系。唐朝将中原王朝“子育万民”的概念引入权威的建构中,在与周边国家的父子关系中,唐朝作为父亲一方,体现其主导地位。事实上,这种父子关系是否有着真实的血缘关系并非重要,而是一种政治关系的象征,唐朝对于突厥可汗的称呼也相应地变为“儿突厥可汗”。在唐与突厥的互动中,这种发展为“父子”关系的建立,已经有囊括四海之意,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够体现出作为政治中心的唐王朝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的。
肃慎。一般认为肃慎的发展史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但郭孟秀指出这种单线的演进不能看出肃慎在发展过程中实则是由小到大,从离散到整合的过程,靺鞨建立渤海政权、女真人建大金政权、满族建立清政权。
将金朝建立时的历史话语体系与清朝建立时的话语体系相对比,在金建立初期,金人特别强调“一统天下”的政治理念,在打击渤海政权时曾讲道:“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从这里可以看出金人在建立政权时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由此,金人也赢得了各民族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从而建立起自身的政治基础。到了清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时,满族人开始特别强调自身作为女真人后代的正统性。女真人在冲击辽的统治过程中,曾经历民族的大融合,但现在满族人不断抹除女真人与别族建立的联系,命史学家对族源进行重新的选择和改造,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起对自身统治有利的叙述体系。究其原因,清朝实际上是回到了前几个朝代中对于周边民族的“君臣”思想的建构中,这种建构方式要求满族人必须拔高自己的民族中心化的属性,进而把自身的权威建立在不可挑战的地位来实现统一,也就是说到清朝的时候,实际上的话语体系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溯。
这些游离于主线历史外,散落在历史时空中的印记,看似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富有价值的线索,但当把它们一个一个作为历史的话语体系解构以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进行整合的,是如何走向“大一统”的叙事结构的。
复线的历史进程往往跳脱于这些中心主义,向我们传达出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来自对历史的继承与赋新,所有的解构都力求寻找其源头的叙事,这种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追至中华民族的源头“三皇五帝”的时代,但所有的话语体系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们会被不断地裁剪和包装赋予新的历史含义和使命。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外这些历史碎片呈现出来的小的话语体系相糅合,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努力朝着“大一统”的方向迈进,不断继承、不断革新,直至民族“大一统”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像这种散落于时空中的碎片化历史还有很多,正等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