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山
作者: 魏文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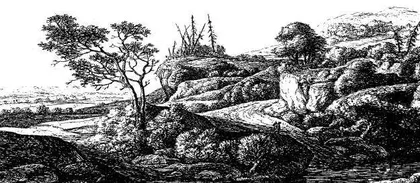
我们村庄的南侧有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穿村庄,流经的区域是大片大片的田野,一年四季颜色分明。
与这片美丽的田野极不相称的是短命山,它位于村子的东头,与隔壁的浙江的山相连。它其实是座荒山,山体光秃秃的,不长植被,白色的沙石长年暴露于空中,可谓人迹罕至。短命山的唯一用途是用作墓地,不过,不是普通的墓地,而是用于安葬村里那些十几二十岁的死者。
发比我大几岁,个子高大,长得一表人才,英姿飒爽,是村里的大帅哥,而且口才好,很能讲。所以初中毕业后,他十五六岁时就当上了生产队的民兵连长,早上常带着年轻的民兵出操。我们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但常遭驱逐。他们操练的一个经典而重复的动作就是,手持扁担或木棍当作枪支。当连长下令“往前刺、肚子刺”,他们会整齐地将木棒的尖端用力地往前推进,做出一个行刺的动作,然后齐声地高喊“杀”。
早操结束了,他们就解散,各自回家吃饭,这就是他们常说的早工。当然,吃过早饭后他们还要和年长的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儿,这时民兵连长职责就消失了,大家都得听生产队长统一指挥。发干活儿是一把好手,而且初中毕业,这在村子里可算是很有文化的青年。大家都认为他是很有前途的,对他说话也恭敬几分,认为他肯定能像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有朝一日跳出农门当干部。
他后来和相邻的浙江的一个女孩儿结婚了。结婚后不久,据说发的妻子要求分家。农村的新人婚后,大都和公婆及兄弟姐妹一家同吃同住,但时间一长估计新儿媳会觉得不自由,生活多有不便,大都会提出分家。其实分家只是另砌一个灶台,小两口独立吃住,经济独立核算,但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分家的过程有时并不简单。先是小媳妇和丈夫嘀咕甚至抱怨生活有诸多不便,开始吹着枕边风。丈夫听后有点儿犯难,觉得刚结婚才半年一年,闹分家心里过意不去,父母会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做儿子的会有娶了媳妇忘了娘的顾虑。奈何枕边风越刮越猛,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父母商量。父母开始时大都不同意,甚至大发雷霆,把儿子臭骂一顿。儿子又缩回去,和媳妇商量着再将就一段时间再说。
过了一阵又听说家庭吵架了,小两口和父母明火执仗,公开叫板。小媳妇和婆婆都常常边诉委屈边落泪,儿子和老子都会在最前线大声争吵。
经过这么一两次争吵倒也有效,父母受不了了,终于同意分家了。
接着他们要商量着如何分配这几间房子,要是家里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的话,这就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小两口通常能分到一个房间和一个柴火间,白手起家,觉得太难。父母觉得需要多留一点儿给其他还没有结婚的孩子。这种拉锯战的谈判,伴随着争吵会持续好几年。
后来,发终于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了。但没过几个月悲剧发生了,发上吊自尽了。一家人在厅堂里哭成一团,其惨状目不忍睹。尤其是发的妻子还身怀有孕,挺着一个大肚子悲痛欲绝。门前的天空也一片昏暗,乌云笼罩。
发后来就葬于短命山上。
类似的结婚,合住,不适,闹独立和分家的过程同样发生在桂的身上。
桂长得美如天仙,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在村里大家都珍爱有加。一日听说她出嫁到数十里外的远方。那时村与村之间的交往没有汽车,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交通完全靠步行。不几日桂回娘家了,还是那么漂亮,只是两只眼睛通红。后来听说她不愿去公家,她妈妈含着泪把她送去了。一两个月后,她又回娘家了,她依旧那么美丽,两只眼睛还是通红的,面上多了几分忧郁。在娘家待了几天后,她再次被家人劝回婆家去了。大约半年后的某天,听说她也自杀了。她的身体被送回娘家,她依然那么美丽,但眼睛是紧闭的,脸色苍白。她的家人和村人都哭成一团,整个村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哀中。
村子里失去了一位美丽的女儿,她也被葬于短命山上。
枝是我的堂妹,个子不算高,长得也不算漂亮,但她爱笑,能讲,乐观,最大的优点是能干,无论是插秧,割稻,砍柴,样样做得好,动作十分麻利。而我虽大她好几岁,除了读书比她好,事事不如她。我父亲羡慕嫉妒伯父有这么能干的女儿,恨不得用我去换伯父家的女儿。
也不知道哪年回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堂妹投水库自尽了。我十分震惊,像她那么乐观开朗的人,如何会自寻短见?她当时也就是20 岁左右的花季少女,她还没成家,估计与失恋有关。伯父伯母悲痛不已,含泪将枝葬于短命山。
农村孩子婚恋都比较早,他们都没有准备好,就作为成年人承受了家庭的重担,心智还稚嫩,面对突然的压力,不知所措。
唯一例外的是一个曾经下放到村里的老教授,年年会来短命山看望女儿。他当年带着一个十来岁如花似玉的女儿霞。他极其宠爱她,不幸的是霞后来生病死了,葬于短命山。
他孤独地在村子里生活了好多年,后来回到省城教书去了。但每年清明他都会来村里为女儿扫墓,寄宿在村民家多日后再回省城去。
短命有他们的错,再苦再难,坚持和家人一起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也有我们的过,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关爱不够,让他们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他们那么年轻,那么脆弱,如何能坚强渡过那么多的难关?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