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语境与“当代文学”的第三次生成
作者: 罗雅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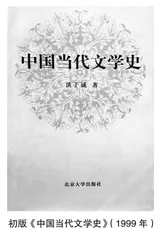
关键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多元性
“当代文学”概念的三次生成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版于1999年,其雏形《中国当代文学概说》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说,从动念到完成,这部书生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之中。2002年,李杨为该书致信洪子诚,开头便提到,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都与“80年代占主导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有潜在对话。洪子诚在回信中表示,自己需要对话的是“两个不同的文学史系列,两种思想文学评价系统”:
一是50年代开始确立的文学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它把现代文学史讲述为左翼文学史,并把“当代文学”看作是比“现代文学”更高一级的文学形态。另一种出现在80年代,它不断削弱“左翼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在“多元”和“文学性”的框架中,来凸显被原先的“激进叙事”所掩盖的部分。
这里谈到了两种“文学史叙事”:“50—70年代文学史叙事”和“80年代文学史叙事”。在这两种叙事中,“当代文学”的定位和定义都存在差异。在50年代,在社会进化与文学进化的框架下,“当代文学”被确立为一种比“现代文学”更高一级的文学形态,这是“当代文学”概念的第一次生成;而在8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翻转过来,“现代文学”被视为比“当代文学”更具思想启蒙性、多元包容性和复杂文学性的文学,而“当代文学”则被视为次一级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概念的第二次生成。
80年代所形成的这一“现代文学”高于“当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意气之争,而是说,“现代文学”构成了当时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基础。以下四种现象是其例证:
第一,“现代文学”在50—70年代指称着从新文化运动到40年代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文学,而在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被视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由此,在80年代社会呼唤现代化、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整体氛围中,“现代文学”被视为文学与思想的理想典范乃至于判断标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前言”提出,“现代文学”既是时间概念,更是“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b。后一层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共识,而前一层面只是为了将那些“现代性”属性不明的对象(如通俗文学)纳入研究的权宜之计。随着“现代文学”被等同于“现代性”本身,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则因其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特征而受到质疑,被视为不具有现代性(或不够现代)的次一等文学。
第二,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思想文化议题,频繁地需要以现代文学作为喻体才能获得合法性。最典型的说法,当属将80年代称为“第二个五四”并呼唤“新启蒙”的到来;再比如,新时期文学对于风格流派的构建、对于现代主义技巧的介绍、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讨论,均以现代文学中的相关现象作为论证支撑;到了90年代,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到新兴的都市文化,都仍要以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作为比喻。
第三,作为80年代文学史思潮中最重要成果之一,“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可被视为一种由“现代文学”知识所主导的学科范式。这一概念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学科边界的打通,其实是以现代文学的标准来整合和评价当代文学;它最终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则是以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以左翼文学、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为主线之外的变异。一个例子是,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其核心特质的前两条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初版中,绪论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历史位置”便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世界文学的纵横联系”;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其他特征,如“悲凉”的现代美感和“艺术思维的现代化”,也主要以现代文学作品来举例。可以说,80年代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特质,几乎就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来界定的。
第四,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未能被列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而是被吸收进了由“中国现代文学”扩充而成的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并因被视为缺乏“学术性”而处于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弱势地位。在80年代以来的第一部学科专业目录《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1983年版)中,仅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到了1990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该专业扩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只是该专业之下的一个方向,未能被列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而且这一格局长久地延续下来。在2005年出版的具有重要学科建设意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虽然强调现代、当代的区分无太大必要,希望将二者尽量融合,但实际结果仍然是以“现代文学”为全书主要内容,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史和现状的论述只占少数。
综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概念的第二次生成也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危机,也即:“当代文学”可能会被融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之中,并以“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文学典范和评价标准。在当时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心中,这是普遍的学科焦虑。无论是表示“当代文学”概念必将消逝,还是自谦当代文学批评算不上学术研究,都是这一学科焦虑或显或隐的反映。2000年前后,诞生了三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洪本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陈本文学史”),还有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董本文学史”)。这三部文学史后来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的主流教材,影响力较广,也常被加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三部文学史都在开头处表示“当代文学”的概念必将被“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但三者也最终仍选择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书名。三部著作的作者们都在思考同一个学科难题:如何恰当地理解“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在“50—70年代文学史叙事”中,“当代文学”成了“现代文学”的尺度,定义着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在“80年代文学史叙事”中,“现代文学”则成了“当代文学”的尺度,同时也成了未来文学发展必须效仿的标杆和旗帜。那么,在90年代语境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代文学”能否有自己的尺度?“当代文学”的主干部分(50—70年代)能否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有效资源?洪本、陈本、董本文学史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以上问题,并让“当代文学”概念不同程度地从“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笼罩之下重获合法性和生长性。可以说,它们共同推动了“当代文学”概念的第三次生成。
当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20世纪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中,“五四”被视为“第一个辉煌的高潮”,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原点;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另一广泛代称,便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因此,在处理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位置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当代文学与“五四”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出版的洪本、陈本、董本文学史在绪论部分都重点讨论了这一内容,但三者的处理方式有较大不同。
先看出版最晚的董本文学史。该书绪论首先提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定位,需要将之“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其“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而这三者“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绪论还直接表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时,“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五四’传统,还是背离、消解这一传统”。这便明确提醒读者,要以五四精神作为判断20世纪中国文学品质的标准。总体而言,在该著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遵循着一个“出发—背离—复归”的路线图,也即:从“五四”启蒙精神出发,经历曲折与偏移,但又始终寻求启蒙精神复归。
再看陈本文学史。该书开头写道:
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陈本同样将“五四”视为整个20世纪文学历程的原点,“几经曲折几遭摧残”的表述暗示了和董本同样的文学史发展路线图。绪论的后文进一步表示,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生机勃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有关;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是“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的结果;而对于艺术技巧、小说形式、文学主体性等“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也是“复苏的‘五四’传统”中的一脉。因此,该绪论格外关注“五四”一代老作家在“文革”后所重新焕发的写作热情。可见,陈本同样以“五四”作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头与主线,这一点与董本是一致的——虽然,在“五四”精神是否已臻完美这一点上,两本书的看法存在差异。
陈本和董本均以“出发—背离—复归”的基本路线图,来描述“五四”以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种论述有其道理。如前所述,“五四”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在80年代的复归、经历过“五四”的老作家们在80年代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确实是当时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会得出80年代与“五四”的对应关系。洪子诚在1986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开头也同样写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破坏了‘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这种多样和丰富的程度,在30年代以后也在不断削弱)而走向狭窄和单一”h。这里所呈现的“五四”以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路线图,与陈本、董本基本一致。
但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却将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视为“五四”文学中某一倾向的实现而非背离。他认为:
“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洪子诚在此处将“一体化”的开端追溯到了“五四”。董本文学史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在绪论中专门就这句话提出不同意见,表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是解放区文学的“一体化”倾向的全面实现,“解放区文学的‘一体化’并不等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体化’”。不过,洪本文学史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论述左翼文学如何经历改造而“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因此暂时偏离了“五四”这一讨论对象。而在同时期写作的多篇文章中,洪子诚将“五四”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表述得更为鲜明。
在1996年发表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洪子诚明确表示,对于许多“五四”作家而言:
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洪子诚看来,“左翼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是五四新文学之启蒙精神产生变异的结果,而是五四新文学中本就包含的那种对“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展开“挤压、剥夺”的冲动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其后,在1999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中,洪子诚将作为“50—70年代文学史叙事”代表的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史与“80年代文学史叙事”的集大成者《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观后提出:
拒绝为着文学“纯粹化”而进行不断的等级划分的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是否意味着也要反省“五四”激进力量对待知识的态度?而这通常被我们作为文学“理想”的源头(《三十年》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段话有着委婉的深意:当“五四”启蒙精神被视为一种“理想”时,是否也包含着一种对“不理想”的他者予以坚决排除的态度?这里批评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不如说是现实中在“五四”启蒙的旗帜下、重新为文学排定座次、对某些与“五四”精神不符者加以过激批判的研究者和批评家们。在“为着文学‘纯粹化’而进行不断的等级划分的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这一点上,80年代“五四”启蒙话语的使用者们是否和他们所批判的“50—70年代文学史叙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