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问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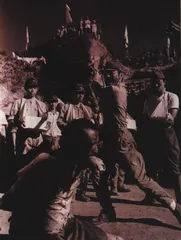
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长城脚下一个附近有日军驻守的村子里。一天晚上,有人把两个俘虏押送到一个村民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一个是翻译官。约好了5天后来取人,但此后音讯全无,两个俘虏在村子里一关就是半年。
村民,日本兵,翻译官,三方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精神与个性。在想尽了办法处理两个俘虏但最终没有结果的时候,在村民们感到最无奈,而俘虏也感觉最绝望的时候,他们达成了一个绝对令人意想不到的协定,导致整个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谈论《鬼子来了》,最终必然会落脚在世界观上
记者:这部长达2小时40分钟的影片(尽管目前仍是半成品)在观看时让人非常着迷,又紧张,又可乐,但看完之后感觉有一种压抑感,你觉得这种压抑感从何而来?
姜文:你至少承认它不是观赏效果上的压抑。它像打了一针,药性开始起作用了,看完后至少一个小时会有点犯懵,但过后大家会有各种东西往外掏。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悲剧不是让人流眼泪的东西,它是一种震撼。
记:它无疑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但它为什么带来压抑感,我想是不是因为:一边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小国寡民、天人合一的境界,另一边是当时日本人的野蛮的、攻击性的文化,这种碰撞形成一个彻底的悲剧,但在这里面没有让人感到特别的出路。而不像大卫·里恩的《桂河桥》中,日本人代表一种不入道的东方文化,英国人在战争中大讲人道,而里边的美国人则要游刃有余得多,代表光明吧。——所以也可以说,你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姜:《桂河桥》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带着一种对和平的崇拜,认为和平无所不能,这是错的。时至今日,本世纪末,世界上所有事又重新翻腾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和平是很脆弱的,“和平是两次战争中的休战”。而且从美国人的角度他愿意这么理解问题,他是战争的胜利者,得意者。他会掩盖很多在成为得意者、胜利者的过程中的一些手段。但是作为另外一个民族,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能比他更有机会,更有勇气来谈一些问题。后半个世纪证明《桂河桥》那种想法是太理想化了。你看黑泽明的《保镖》,三船敏郎要不是有一个替天行道的冠冕堂皇的帽子,他就是个坏人,他是在以恶制恶,比恶还恶。其实这话中国也有,“比狐狸还狡猾的猎人”,但我们没有做到这点。我们一旦比狐狸狡猾了,就不对狐狸了,就对猫了,就对家禽了。这是个问题。此外,在这部影片里中日之间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因为他们都还属于东方。
记:它也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战争的影片,尽管它与以往的战争片有很大不同。
姜:我们首先要把战争中的双方都当做人来拍。我们相信他是一个人,但他做的是野兽的事,你能把握到他的脉搏,他的变化。其实这部影片里反映出的日本人的残暴要超过以往任何影片。但它是人的残暴,人在战争中的变异,而不是野兽。
记:如果说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那么在这部影片里被打碎的,是中国的某种传统文化?
姜:在影片中,中国村民表现出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善良、很美好的,是一种境界。有好的东西被撕坏了——我们的散漫、无主题、无逻辑,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融在大自然当中的。但为什么在影片中它引出一个悲剧呢?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反思呢?我觉得是人们进入了现代文明,需要有钢铁,需要有高科技。
现代文明也是一个过程。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有不足和值得考虑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把目标看得太清楚了,我们想直接要结果,忽视了过程。我们忽视了在高境界之前可能会有的一个非人性的过程。现在也一样,我们看西方自由,但它有严格的法律界限,过了一点就没有自由了,
通过这部影片我也在想人类的一个悲剧:你想达到最高境界,你能否不要过程?过程是否舒服?没有这个过程,是不是就会栽倒?人无法摆脱的一点是,你要进步,但进步本身的意义在哪儿?有的时候它会扭曲和摧毁人性。你要追求人性,有时就会和进步冲突。
尽管故事发生在40年代,但我们每个人仍然会面临剧中人所面临的问题
记:可能带给我压抑感的是影片里面有很多悖论的东西,像编剧述平说的,很宿命的东西:一群农民介入了残酷的战争,他们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你在那样一个情境,你没辙,你只能那样走。
姜: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所有好的作品,你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现代人,或者自以为聪明的一个角色去代替其中的人物。我们无论是谁,我们去当一下马大三(影片主角),或者遇到类似他的境况,我们都不能比他更高明,就像我们不能比哈姆莱特想到更好的办法。那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这是挂甲台(剧中村名)种地的哈姆莱特,他们的问题是一样的。涉及到生存还是毁灭这种最根本的问题时,你就不能比他更高明。你注意到有一些作品,你是可以比剧中人更高明,你只不过是看着两个蝈蝈儿在那儿现掐,你有点儿幸灾乐祸,我觉得那个不叫作品,那只是个娱乐。我不排斥作品里头有娱乐性,但仅有娱乐它不是作品。你称为压抑的东西,你不能比他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这并不能使你绝望,这正是“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面对问题,想办法,去找到哪怕是一个方向。我们不急于找到一个答案。
记:人们总要试图为自己不懂、不明白的事情建造出一个体系,给它一个上下文关系。但你想通过一部影片打破这种上下文关系?
姜:我没想解决什么,但我觉得应该提出问题。这部影片不是表现扭曲、阴暗的东西,而是表现尴尬。这部戏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尴尬的位置上,每一个人都是别扭着,每一个人遇到的事都大大超出他的能力。——扭曲和阴暗的东西都加上了太多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这部影片最终不给人压抑感,而是使人们有一种净化感,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脑子里的东西,这是悲剧带来的有益的东西,而不是让你看完了难受,没法儿活,绝望。我们追求光明。
对于我们这个环境来说,我认为最大的灾难是我们经常误以为我们有了答案,或者我们被强制性地接受了一种答案,或者强制性地给别人一个答案,俗称结论。这个不是艺术,也不是对生活或者对艺术的态度。古希腊人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问题,那是因为它触及到问题的根儿。可能得一代一代推下去。我们也是接受了上一代人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在作品里存在会使它成为一个作品。可能我这话说得有点傲慢,我就是觉得我们以往的作品里边真正的问题太少,或者不存在,或者没到根儿。
我们这个民族上百年的灾难,不是简单的技术比人落后,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们不太重视学问。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是可怕的。为什么很多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之后——你看看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有很多令人失望的东西,就是因为,读书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对书、对知识的崇拜,对知识的兴趣,这点是我们落后的根本。我们可以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努力读书,比任何一个民族读书的成绩都高,但他不是兴趣使然,他的目的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记:你提到现代文明也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对于技术、自由与进步你能否再稍谈谈你的看法?
姜:有个故事,清未有个搞洋务的大官,搞身儿西装穿着出去,很有勇气,自己也很神气。他回来跟自己老婆说,这西装真不舒服,你看这肩给窝的。脱下来看,那衣架还在上面。他不知道那衣架是应该拿下来的。把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当做了不起的东西来炫耀。其实现在数字化的东西,都跟那衣袈一样,那是个工具,说白了就是锄头、镐、镰刀。我说这IBM它就是个锄头,就是个镐、粪叉子。它在生活中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怎么能去迷恋它呢?你迷恋的应该是五谷丰登以后,秋后,歇着那段儿,赏赏月,吃口儿月饼,闻闻这个空气的味儿,烧荒草的味儿,这是人气儿。现在人都掉进这个粪叉子里去了,那哪儿行?但是你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使手去捡粪,显然不太舒坦;但是你有了你不能把供着。思想上去供着它那就更可怕了。怎么对待我们在生存当中的遇到的选择——这不是马大三一个人的事儿。
电影业的问题,对于一个艺术家,心灵的表达是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一个境界。成功也好,票房也好,名气也好,那都是粪叉子的事儿。真正重要的是你心灵表达的一刻,赏赏月,五谷丰登以后,跟老少爷们坐着,扯扯淡,这是境界。别的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艺术观:姜文认为,让人兴奋与让人思考,这是好作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但我们太多的影片,或者是把兴奋点理解成娱乐点,为取悦他人而创作;或者是,想让观众思考,却忘记了作品首先要让人兴奋,结果把深入浅出弄成了浅入深出
记:对电影形态你也有一些探索,比如前半部分大家是笑着过来的,但它同时又像个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片。
姜:样式上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怎么在紧张的时候还经常有笑声,笑得你头皮发麻,不笑还不行——人们就是在矛盾中生活。我觉得无论让人紧张,让人恐惧,让人思考,还是让人快乐,总之是先让人兴奋。我自己能在剪辑房一坐半年,是因为兴奋。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前提。
我们的文艺习惯常常是取悦。但我个人的艺术观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绝对的沟通是做不到的,但通过作品是可以互相拨动一下心弦的。取悦仅仅是要那一笑。我们看到西施会让我们赏心悦目,并不是西施要取悦我们,而西施本身具有那些东西。可是后来大家都去模仿西施具有的那种效果。艺术也是这样。你觉得这部片压抑是因为我们以往的喜剧也好,悲剧也好都有很强的取悦性,也就是缺乏一种往心灵深处去的严肃性。某些东西停留在某种感官上,不太入心。
记:就是说,不能把兴奋点和娱乐点混同,一说要观众就以为是要娱乐观众了。
姜:对啊,现在不是电影市场不好了,是坏电影的市场不好了。那么说好电影就是《泰坦尼克》,这又错了。所有上座影片的根儿,都是一部经典影片。好莱坞最早受一些好的戏剧影响,但它在二战后到60年代,本国电影少于进口电影。美国国产影片快死了,大家都慌了神儿了。接下来出来的是好莱坞小子:科波拉、斯科塞斯、卢卡斯、斯皮尔伯格这些人。他们在形式上弄得惊天动地,但科波拉自己就说过,他们受的影响是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还有黑泽明。这些在今天似乎令人望而生畏的影片,当时给他们吹去的是一种新鲜空气,他们弄出来的是《教父》、《出租车司机》、《毕业生》、《愤怒的公牛》这些比较大众化的影片。从他们那儿再派生出一大堆所谓有可看性的商业片。这就像一尊维纳斯,整体挺好,有人就弄维纳斯的一个头,维纳斯的一个胳膊,一个乳房。这些有商业性,但没有维纳斯,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记:在戈达尔、安东尼奥尼和黑泽明他们那里是兴奋点,移植到美国变成了娱乐点,再到我们这儿,就又变成了一种东西。或者说,中国如果没有出几部讨论问题的影片,没有出几部给人兴奋点的经典影片,是不会出真正让人娱乐的影片的。
姜:对。我们不能舍本求末。还有一个危险是,如果我们急功近利地这样做,我们还是从经典影片中学不到东西。我们缺乏对经典影片的尊重、追求和研究。我们只是像大三儿一样想看到结果,挣多少钱?票房多少?多少年来我们犯的就是同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必须承认“过程”,我们必须为结果付出这个过程的代价。
好作品应该有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
记:影片前半部分一个大的悬念是,不能让日本人发现这两个俘虏,由此引出了好几场戏:比如日本兵抓鸡,比如俘虏教小孩学日本话,这些是不是有些相像,还是为了积累,以证明他们都疲了,农民和俘虏都疲了,最后才不得不达成那样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协议?
姜:我不是在制造悬念,所以我也不怕它相像。我是说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有多少种可能能够摆脱困境,而又摆脱不了,有多少条出路是出不去的。我要追求悬念那它又成一个工艺品了。我觉得达成那个协议并不是因为他们疲了。就像我们看那些贪污犯,他们并不是因为没钱花,而是因为欲望,欲望难以填补。比如做这个片子,我感觉到我作为人的可怕性。我当时能把剧本写好,就是我的最高理想;我写好了我就想拍好;我拍好我就想把它剪好;我剪好我就会想把它混录好;混录好我就想把它卖好,成为最了不起的作品。我去掉了原小说里面的因为饥饿而达成那个协议,因为饥饿就没意思了,而是因为欲望,就像有魂在勾引着他们。他们按照欲望去设计他们可能发生的走向,可是事实与他们的设计不同。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这部片子,我都认为一个作品应该有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太多的格式化会使作品缺少人气儿。我觉得这儿应该这样,过瘾,那就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大部分都是不应该那样,却那样了。真正的好作品,出人意料的作品,往往它是非格式化的,可能由于它会带来一个新的格式,又被大家给炒滥了。
记:《红高粱》有这个意思。
姜:对。当时《红高粱》出来时,有人说这个幼稚,这个剧本有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个片子的优点也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片子了不起就在于它生猛,我就这个。那时候张艺谋也恰恰不太会写剧本。
记:你有没有觉得影片节奏太紧?如果它不是那么紧张、刺激、好笑,让人一刻不得安宁,会不会更易让观众认同,比如把马大三与自己联系在一起?
姜:我追求这个。我们的电影在世界上,没有哪部片子是因为节奏太紧而著名的。相反是普遍的拖沓,我去过很多电影节,我们的片子真让人睡着了,不好意思。我即使把它做得过分,也到不了太快的程度。我的两部片子在洗印厂混录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接触到的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最复杂的。我不迷恋技术和手段。摄影机架在架子上,能不能跟上人(演员)?跟不上,搁轨上;轨上能不能跟上?跟不上,拆下来,扛上。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设计,哪儿是扛?哪儿是摇?但是我们排练,我是学舞台的,我会充分利用这些空间,把它调度起来,而且也符合人性。我的目的是要表达人的内心。一切以内在的内容为核心。所以无论是调度还是镜头的运用,还是剪接和声音的运用,全是符合这个。我认为它是内容的要求才形成现在的影片。
为问题而拍摄
记:你说影片中的疯七爷是唯一的英雄(我倒觉得马大三也是英雄,因为他代替我们在面对许多难题,并试图解决它们),但疯七爷始终只有一句台词: “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他们(日本兵)”,与其他人物相比是不是显得概念化?像鲁迅小说里,总在喊“吹了那个长明灯”的疯子?
姜:不是概念化。我想让他多说啊,我想让他多有点作为啊,但我并不想让观众在影片里把这口气给出了。我满足你你就不想了。我想把这个愿望告诉你,让你有这个愿望——疯七爷能不能再多点儿什么?我们常认为艺术品要有一定的剧场效果,要在剧场里面观赏的同时就得到满足,这个贬低了艺术作品的作用。小时候看电影唯一让我受刺激的是《甲午风云》,这口气儿到现在我出不了——咱失败了,是不是?这事儿咱没办成是不是?想撞没撞成——咕咚——咱掉沟里了。我很多求知欲望是从《甲午风云》开始的——我不明白了,我糊涂,我懵了。
记:你喜欢鲁迅?
姜:我喜欢,但是我没什么研究,这个我不敢这么说。我们中学课本就有,但说实在话,不是很懂。在我剪片子的时候,偶尔把《阿Q正传》看了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懂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更不敢妄自去读了。我们中国有些伟人,我们没有去认真研究,我们在能够拉近的时候,尽量把他往下拽,这是心理上的事儿。毛泽东被拽成他们家邻居了,鲁迅被拽成他们家后院了,平衡了,舒坦了。一旦这个事情做不成,我就往相反的方向走,给你推成神,于是我也就更平衡了。他不是神吗?他跟咱们不一样。这两点都挺可怕。他还又不是神,又不是跟你一样的人。你能不能变成跟他那样了不起的人?你是有可能的,但你主动不要这个机会。这(部影片)里边的老百姓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是带着很强烈的爱来写的,你不会恨他们,你甚至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可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毁灭?我演着演着就觉得我一点也不比大三儿高明。
我们一直强调作品要有社会责任感,但我们谁愿下功夫呢?我们的剧本弄了几年,就开始有人耻笑了,“几年弄一个剧本啊?俩月就能弄一个,怎么那么笨!”我宁可这么笨。“片子剪半天,剪七八个月,出事儿了吧?”我宁可出事儿了,我宁可是一个笨蛋,我需要这个。其实一个故事酝酿那么五六年算短了,你怎么就把事儿全给琢磨透了?功利心太强是不能做艺术的。
记:你感到这部影片与中国以前的影片相比,最大的不同的是什么?
姜:我们有问题。我们不是为拍而拍。
记:你在构思《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问题?
姜:人不断地充满激情,但激情这么容易逝去。激情与理想能否带来美好的现实?如果没有美好的现实,我们是不是因此否定激情?我们是不是因此否定理想?那样我们是不是太功利了?就像拜菩萨,怎么不灵啊,我他妈把你砸了。再比如,值得人们怀念的东西是不是有价值的东西?那没价值的是不是就不值得怀念?现实存在的观念与人的真实反应是否一致?——因为我们常常用观念来压制我们的真实反应。
记:你曾说拍这两部电影都像是拍回忆录,你的意思是说,这两部电影凝聚了你一直以来的思考?
姜:《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告别青春的一个作品,那些问题使我不拍不快。拍完了就想锁到哪儿去——“为了忘却的纪念”。《鬼子来了》——由于要拍出时代的真实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至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像个30年代过来的老人一样,那些事是我原先看到的或者经历过的;但根源还是我36年的人生感受,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撞击而出,我觉得是这种回忆录的感觉。
记:在《鬼子来了》整个创作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到很娱乐化的东西?
姜: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很娱乐化。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玩具,是一个大玩具。因为我崇拜艺术,我能够驾驶着电影这辆车通向我的理想。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愉悦的。整个拍摄过程就像坐在一艘船上,那些现实就像水边的山影飘过,我觉得一切的困难、问题都像拍击船体的浪声一样,是一种节奏。